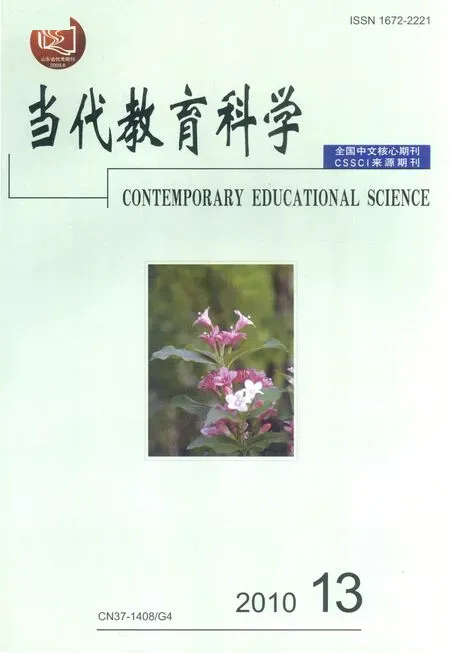论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现象
——兼论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真独立”
● 范涌峰 刘 梅
论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现象
——兼论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真独立”
● 范涌峰 刘 梅
从元教育理论研究对于本土教育理论发展的贡献这个角度来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元教育理论研究是“无效”的。“无效”之因在于元教育理论自身的缺陷、教育学者的学养缺失和制度的规约,而其根本则在于教育学与教育学人缺失其本应具有的“真独立”的生命灵魂和价值品质,为此,追寻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真独立”是制度规约下元教育理论和教育理论发展之必须。
元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学;学科自觉
一、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
中国元教育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进行这方面探索的是雷尧珠的《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1995年,在瞿葆奎教授的倡导下,华东师大学报 (教育科学版)首开“元教育学讨论”专栏,引起了人们对元教育学问题的广泛关注。此后,关于元教育理论研究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陈桂生教授的《“教育学”辩》(1997)、叶澜教授主编的“教育学科元研究丛书”(1999)、周作宇教授的《问题之源与方法之镜》(2000)、唐莹教授的《元教育学》(2002)等等。此伏彼起的元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者们对教育学科的“自觉”,对教育学发展问题尤其是教育学“学科危机”的普遍认识,在教育学研究领域,钱钟书先生和华勒斯坦(Waller-stein,I.)对于教育学的描述近乎人人皆知,成为教育学人心中难以抹去的“伤痕”,许多教育学人的“学科自卑”情结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于是,怀着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切之情和奉献之心,学者们化“危机”与“伤痛”为动力,开始梳理中西教育学的发展历史,追源教育学发展中的问题,谋求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新路子。然而,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元教育理论研究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有心的学者已经可以去构思研究“中国元教育学研究史”了。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元教育理论研究对于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之贡献是十分微弱的,我们甚或可以说,元教育理论研究是“无效”的。
我们缘何说元教育理论研究是“无效”的?又凭什么说元教育理论研究“无效”?这里所言的“无效”,意在指出近30年来我国的元教育研究之于教育理论的发展是“无效”或者收效甚微的,而不是说元教育理论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同时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元教育理论研究指的是广义意义上的元教育理论研究,即对教育理论的反思、批判与重构性质的研究,这也是本文用“元教育理论研究”而不用“元教育学”研究作为题名的主要原因,因为元教育学研究有元教育学学科建设之意,而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指称范围则要更广得多,也更有意义得多。叶澜教授曾指出三个“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政治、意识形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1]教育学者们的元教育理论研究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的。概言之,近些年来元教育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关照教育理论的发展:一是教育学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主要包括教育学学科属性、学科内涵、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方法论等方面反思与探索;二是对本土教育学发展之路的探索。这一研究维度是基于学者们对中国教育学“西化”现象的反思;三是对政治、意识形态与教育学关系的反思,主要体现在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关系问题的探讨上;四是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反思,只要是针对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而提出的。这四个向度上问题的解决是元教育理论研究孜孜以求的目标,也的确是教育理论发展必然要跨过的“障碍”,因而可以说,元教育理论的发展“抓住”了教育理论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然而,抓住或者研究了问题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
从教育学自身问题探讨这个维度来说,关于教育学学科属性和内涵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普遍的取向是人们将教育学从“科学化”的歧途引向“文化性”的轨道,并强调教育学的人文意蕴,[2]然而,对于“文化性”的错误理解却使“文化性”成为许多教育研究者摆脱教育实践的“借口”,“文化性”成为“书斋式”研究的最好辩护,教育理论的“价值关怀”往往成为脱离实践的“无根”的“价值关怀”;教育学学科体系一直是中国教育学者们的努力方向,尽管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教育学所陷入的误区从表现形式上看,乃是对体系的偏好和追求。”[3],然而,如果仅仅从元教育理论的初衷之一——构建完善的教育学体系来说,中国教育学体系的建构无疑是失败的,教育学成为其它学科和西方话语的“领地”的现象依旧,我们仍然不能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较为完善体系的“中国教育学”;从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来说,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争辩持续至今,并有学者提出科学的人文主义路向,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学的路向,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有人种质研究、叙事研究等,[4]然而,教育研究领域真正意义上具有教育学特色或者合乎教育理论研究的“教育学研究范式”似乎依然没有发展起来。
从对“本土教育学”发展来说,中国教育学者们太渴望本土教育学的发展和完善了,然而,西方话语仍然充斥着中国教育学领地,西方教育话语的权威性显然远远胜于本土教育话语,对于西方教育话语的掌握依然是教育学者们获取学术权力的重要能源,似乎教育学已然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学智慧,打开教育研究的论著,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海德格尔、胡塞尔、哈贝马斯等西方思想家的身影,难道西方教育学的研究也言必称孔孟吗?文化、思想的相互交流、吸收、利用是应该的,但是在中国教育研究的领地上却很难找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本土教育话语,这的确是件值得反思的事情。
从政治、意识形态与教育学的关系来说,这一关系最直接地反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的关系上,当前,“教育理论研究对于教育政策的依赖度似乎要远远大于政府在做教育决策时对教育理论的依赖度和咨询度”,[5]当新的教育政策或者其它政策出台时,教育学者们争相解释相关的教育政策或者做相关政策运用于教育实践的研究,而对于新的教育政策,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理论在教育政策中的话语权十分有限,这与当前我国庞大的教育理论研究学术队伍的现实是不相称的。因而,从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这一维度来看,教育理论中有太多的“应景”之作,教育理论成为教育政策的解释工具,而缺少批判精神、实质性的贡献与话语权。
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反思恐怕是近些年元教育理论研究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学者们从实践哲学等多角度解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企图调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增强教育理论的实践意义。然而,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教育理论实践意义的重要性,也无论我们提出多少调和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方法,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更有甚者,随着近些年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教育理论中的兴起和对教育学的文化性与人文意蕴的普遍认同,许多学者将此作为自己脱离实践的“辩护词”,许多所谓对教育实践的“价值关涉”仅仅成为没有实践也没有价值的关涉,那些不过是纯粹的“书斋研究”的产物。与此相应的仍旧是教育实践一线以及社会对教育理论的实践价值的普遍质疑,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也因此而依旧式微。
杜威坚持认为,最好的理论就是最有用的理论。尽管对于教育理论之“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从上述四个维度上的“依旧”来看,教育理论并没有因为元教育理论的发展而有多大程度的发展,因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元教育理论研究是“无效”或者至少是低效的。元教育理论研究的声音反映的是教育研究者的学科自觉和学术责任的唤起,然而,遗憾的是,元教育理论研究没有多大成效,教育学者们的一片“赤诚之心”只能被安放在尘封的角落。
二、元教育理论研究何以“无效”
对于教育学科的一片赤诚居然是“无效”的?这是许多教育学者所无法接受的。元教育理论研究何以“无效”?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对于元教育理论和教育理论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人们对于一个事物“无效”之缘的追问往往从三个方面进行:事物本身、事物的作用对象和作用的过程(主体、客体、过程),元教育理论的直接作用对象在于教育理论或者更直接地是教育研究者,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可以从元教育理论自身、教育研究者、影响元教育理论作用力的外部因素三个方面找寻“失效”之因;我们也可以单从元教育理论的直接受力点教育研究者出发来找寻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所谓的“失效”的缘由可以分为教育研究者“想不想落实”元理论与“能不能”落实元理论两个方面的原因,最终我们发现,无论从哪条分析路径出发,我们都可以一致地得出元教育理论研究“无效”的三方面主要原因。
(一)元教育理论的自身缺陷
元教育理论的发展之初主要走的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路线,试图检验教育理论的逻辑规则,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认为,元教育理论研究无法找到共同言说的 “元基础”,“元教育学的语言分析仅仅以自己的视角在教育学的共同体内指出理论的缺陷,进行思想的澄明,而不能形成教育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6]之后,元教育理论研究的功能扩展为批判与反思教育理论(我们现在通常指称的元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广义意义上的元研究),然而,元理论的发展依然存在这一问题,能不能找到“元基础”、该不该找“元基础”,尽管当前人们受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更多地倾向于认为元教育理论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必要找到反思教育研究的“元基础”,然而,我们发现,缺乏共同言说的基础和相互对话,元教育理论的研究是十分混乱的,每个研究者都从自身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兴趣出发来言说教育理论的“应然”。这时的教育研究者面临着教育实践工作者面对他们制造的教育理论时同样的尴尬境地,面对各种堆积如山混杂的元理论,他们无所适从。另一方面,许多元教育理论研究仅仅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所论说的元理论不过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至于元理论对于教育研究的作用以及能否产生作用,则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有的教育研究者论说的元理论本身是反对教育学的“西化”现象的,却以西方话语作为言说的理论基础,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学却引用政策文件中的话语以增强论说的权威性和话语权,这样的教育学者所得出的元理论不仅是不足信的,而且还会干扰教育研究者的视线。
(二)元教育理论的直接行动主体——教育学者的学养缺失
教育理论有三个主体:教育理论主体、教育政策主体和教育实践主体,而对于元教育理论而言,教育理论主体无疑是直接的受力主体,而其他二者则为间接的受力主体。因而元教育理论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教育理论主体即教育研究者,如果没有教育研究者发挥主体作用,所谓的元教育理论只能是一纸空谈,元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走入“无效”的尴尬境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找不到落实元理论的主体。我们认为,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首先在于教育研究者缺乏相互间的对话与协作。教育研究者们从各自的的立场出发对教育研究进行批判和建构,而缺乏相互间的对话,元教育理论仅仅停留在纯粹的元教育理论研究上,而远离了元教育理论的功能和目的,同时,由于缺乏相互间的协作,没有形成合力,单一的研究主体的元理论声音是十分微弱的,难以使某一元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当然,元理论研究作为一种以批判精神为本质精神的学术活动,相互间的真诚对话与协作是需要教育理论主体具有基本的学术宽容精神和批判精神的,而这种精神的普遍缺乏恐怕也是元教育理论“失效”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元教育理论的自身缺陷和“无效”也反应出教育研究者缺乏真正的教育情怀,缺乏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的关切。元教育理论研究往往蕴含的是研究者对教育研究的某些方面的“应然”之思,这样的“应然”应该是虔诚和发自肺腑的,然而,许多元教育理论也仅仅是一些教育学者赚取“学术资本”的工具,他们反对教育研究中的“西化”现象,却又乐此不彼地追逐西方教育理论,他们主张教育研究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却又毫无批判地对教育政策“俯首帖耳”。这也使理论停留于理论,元教育理论研究只不过成为教育学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真正认真分析各家之言,致力于推动学术协作与共同体的形成,进而推动教育理论实质性进步的教育研究者少之又少。
(三)制度的规约
在元教育理论作用于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制度因素也是制约元教育理论产生实效的重要阻碍。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的保证,即便元教育理论的实施主体教育研究者努力而为,许多具有较大价值的元理论也只能止步而无法对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作用。首先,高校和科研机构刚性的学术评价机制制约了教育理论的进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评价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束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于研究者学术水平的高低主要是通过其主持课题的多少、著作的多少、论文的多少来衡量,这种单一的、量化的评价机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教育学术研究的繁荣和活跃,研究者争相申请国家课题、争相发表著作和论文,否则在当前实行科层制管理的高校,他们将面临着降级的危险,同时,教育学科的课题研究期限和经费都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学研究者们很容易屈从于制度的要求,在制度的要挟中放弃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责任。同时,这也在客观上容易刺激教育学者急功近利的追求。再如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我们希冀通过叙事研究等方式让更多的实践主体参与到教育理论研究中来,以此作为调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路径之一,但是在当前的科研体制和学术氛围中,教育实践人员表达自己教育观点的可能机会和平台恐怕还是少了些;其次,缺乏开放民主的理论环境。实际上,教育活动作为社会活动,是无法离开政治的,教育理论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唱“独角戏”,但是,如果理论环境过于封闭、保守,那么教育理论只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成为教育政策的注脚,失去理性批判精神的教育理论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再者,对于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政策三者之间的对话与协作缺乏制度规范与保障。教育政策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教育理论要真正产生广泛影响必须要有政策的支持,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协作机制保障,每个理论主体都遵循各自的“游戏规则”,那么,一方面,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在教育政策中的话语权永远是微弱的,另一方面,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也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三、追寻教育学与教育学者的“真独立”
如前所述,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始于教育研究者、元理论自身和制度的屏障,而为何(元)教育理论存在如此多的缺陷?为何教育学者会屈服于制度的要挟?依循这样一个分析理路,我们发现,问题的源头又指向了教育学和教育学者本身,如此看来,所谓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和教育理论发展失落原因的关键以及出路还在于教育学者自身,那就是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缺乏或是丢失了某种谋求其发展本应具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就是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 “独立”精神,这是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生命灵魂和价值品质所在,在当前教育学发展状况和制度背景下,为着具有独立个性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发展,我们理应追寻教育学和教育学人所缺失的这种生命灵魂和价值品质,这是他们学术生活中的本然身份与追求,也是元教育理论与教育研究的发展之必须,教育学的发展太需要教育学科和教育学者的“独立”精神了。找回教育学与教育学人应有的“真独立”或许比提出所谓具体的出路有意义得多,也是任何措施意义生成的根基和前提。何为“真”?真为本真,真为无蔽之真、原初之真。追寻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真独立”意在追寻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独立”精神内涵之“应然”,教育研究的学术生活需要教育学者理性地行此“应然”之路。
(一)教育学的“真独立”
教育学的发展不可能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任何教育实践都是政治性活动,任何教育理论都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态度或价值取向,教育理论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西方教育理论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独居于学术生活的“世外桃源”,因为思想的交流是促进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却不能让教育理论与实践成为政治生活、西方教育理论或是其它学科的附庸或附属品。为此,关键在于我们找寻到教育学的独特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是教育学应该牢牢坚守的“堡垒”。我们仍然坚持认为,文化性是教育学的学科秉性,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又内在地包含教育学的实践精神,因为任何教育都是一定文化历史时空中的教育,教育学是充满文化符号的价值学科,而任何文化又一定是实践时空中的文化,即文化是实践中的文化,实践是文化性的实践。实践是文化生成的土壤,因而更是教育理论的生成土壤,教育理论是教育实践土壤中生成的教育智慧,是对教育实践的价值关照和文化审思,只有植根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教育理论才是有价值的教育理论。而对于价值的关照需要教育学具有理性批判精神,批判是教育理论关照实践的基本方式,也是教育理论应该具有的基本功能和理论品质。以实践为土壤,以价值为旨趣,以理性批判精神为精神内涵,在实践中生成价值,在批判中建构价值,这是教育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学术轨迹,文化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是教育学应该具有的精神品质,它既规定了教育学学术生活的时空,也规定了教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因而坚守这一内在的精神品质也就意味着教育学学术实践的独特性,意味着与政治生活的相对独立,意味着与西方思想和其它学科之间保持合理的距离和张力。因此,教育学的独立不仅仅在于建立教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坚守这一内在的精神品质才能实现教育学的“真独立”。
(二)教育学者的“真独立”
金生鈜教授认为,我们缺乏真诚的、纯粹的教育学人,并提出向教育理论领域的庸俗专家宣战。[7]的确,我们的教育研究队伍中太缺乏真诚的、纯粹的教育学人,部分教育研究者缺乏起码的学术良知,成为了功利的“俘虏”,为了获取学术资本,他们追捧西方话语,毫不负责地屈从于意识形态话语,在功利和世俗面前缺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起码的学术人格和批判精神,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扰乱了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和秩序。因而,我们主张教育学者应该具备真正的“独立”精神,教育学者的“独立”不仅仅在于其所在学科的独立,不仅仅在于具有独立的言说平台、独立的功利获取渠道和学术能量,教育学者的“真独立”在于具有高尚独立的学术人格,教育者应该具有真正的教育情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树立为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服务和为人类增添新知识的崇高学术理想,将其视为自己的学术信仰,并使之成为学术研究动力和自我审思的重要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不迷失自己的学术方向、不为西方教育话语所俘虏,才能在当前浮躁和功利的学术环境中不为制度所屈服,不为利益所驱使,不扭曲自己的学术人格。“独立”的精神还需要教育学者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和学术宽容精神,允许对自己理论的不同声音,也敢于对主流与权威话语发出自己的 “不同的声音”;此外,“独立”精神还在于对学科独立尊严的维护,为此,应该在提升自身学养的同时,致力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推动学术的对话和互动,增强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的学术话语的影响力,致力于教育学学术标准和话语秩序的建立,最终推动本土教育理论的实质性进步。
当然,教育学与教育学者的“独立”还依赖于教育政策主体提供的外部制度环境支持,为着“真、善、美”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政策主体应该真正致力于为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民主、开放的学术环境,促进弹性、宽松的教育科研体制的形成,促进教育理论、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三主体的协作机制或联合体的生成,只有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使“真、善、美”的教育智慧和教育生活成为可能。
此外,我们说元教育理论研究是“无效”的,是否意味着元教育理论研究应该终结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指明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意在唤起教育学者真正的学科自觉和学术责任感。元教育理论研究就是具有“真独立”精神的教育学人以“真独立”的教育学作为价值引导和方向引领,不断地对教育理论研究提出理性的批判和审思,这也是教育研究者理应为创建具有独立个性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践履的历史使命,教育研究的发展需要元研究的冷峻而理性的审思。元教育理论研究之路不会终结也不应该终结,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走,是否真诚地在走。
[1]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思[J].教育研究,2004,(7).
[2]刘铁芳.教育研究中的人文意蕴[J].教育研究,2008,(11).
[3]周作宇.问题之源与方法之镜-元教育理论探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06.
[4]周勇.论教育研究的文化学路向[J].教育研究,2000,(8).
[5]范涌峰.论学院派教育研究者的生存困境与出路[J].当代教育科学,2008,(15).
[6]金生鈜.教育学的合法性和价值关涉-对元教育学的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4).
[7]金生鈜.向教育理论领域的庸俗专家宣战 [EB/OL].http://old.blog.edu.cn /user3/jinshenghong /archives/2007 /1673861.shtml(金生 鈜博客),2007-3-26.
范涌峰/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 刘 梅/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丙元)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