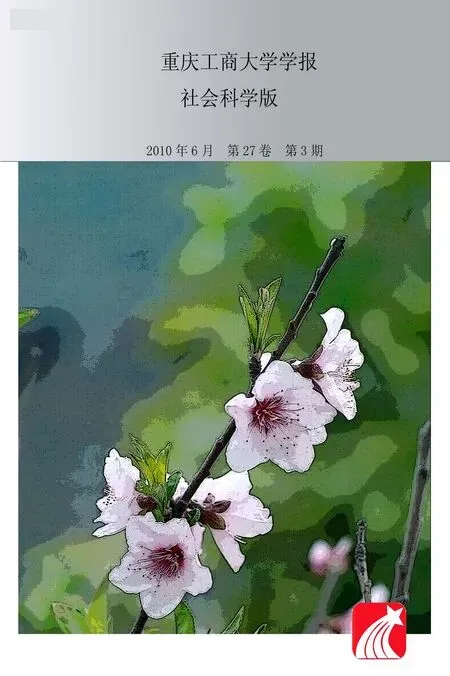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孙立春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一、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五个阶段及两个高潮
日本近现代小说指的是从明治维新到现在的小说,而开启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正是梁启超1898年翻译的《佳人奇遇》,可见这段翻译史主要集中于20世纪。因此笔者将以20世纪为中心来研究这段翻译史,21世纪最初7年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也略有涉及。关于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的分期,王向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中分为五个阶段,即清末民初(1898—1919),二三十年代(1920—1936),战争时期(1937—1949),建国头三十年(1949—1978),改革开放以后(1979—2000)。另外,谭汝谦在《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把300年的中日翻译史分为五个时期,即萌芽期(1660—1895),第一过渡期(1896—1911),发展前期(1912—1937),第二过渡期(1938—1945),发展后期(1946—1978)。相比之下,王向远的分期更符合20世纪日本文学翻译史的实际。因此,笔者参照王向远的分期,并结合谭汝谦归纳的各阶段译书分类明细表,简单地回顾了20世纪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
通过梳理这100多年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其中有两个高潮:一个是第二阶段,即五四运动至抗战爆发;另一个是第五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余年。这两个高潮期的共同点是译者人数多,译作数量大,影响面广。不同点在于前者偏重于引进日本的近代小说,以对抗中国的旧文学,促使中国文学发生质的变化;而后者重在全方位地介绍日本小说,以填充“文革”后的文学空白期,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体现出中国文学已经成熟,译介过来的日本近现代小说不再是文学革命的武器,而是中国文学的有效补充。也就是说,译介过来的日本近现代小说在这两个高潮中的作用不同,而且译介的范围也不一样。从这100多年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是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载体,翻译是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进行深入研究,以找出这繁荣现象下的深层次规律。
二、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总体特征
近现代的中日文学交流是一千多年的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最辉煌的一章,而日本近现代小说的翻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梳理丰富多彩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我们发现这段翻译史有四个鲜明特征。笔者试述如下:
第一,随中日关系而变化。近现代的中日关系史是错综复杂而变化多端的,既有和平友好的时期,也有战争动荡的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日关系走上了不正常的轨道。后来日本在中国又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事件、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等,第一、第二阶段的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但由于中国非常需要日本政治变革和文学变革的经验,以及鲁迅等大批留日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所以第一、第二阶段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并逐步走向第一个高潮。“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争阻碍了正常的文学交流,也使日本文学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原来译介日本近现代小说的知识分子只能放下译笔,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抗战中去,因此日本近现代小说的翻译骤然减少,所译介的少数小说也是为了配合抗战。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又陷入内战,译者们也无心译介日本近现代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所以这一时期译介的日本近现代小说也不多,而且局限于左翼文学和反战文学,忽视了战后日本文坛的发展。1972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中日关系也开始迈向正常化的轨道。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种良好的中日关系也带动了中日文学交流和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的繁荣,并形成了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上的第二个高潮。
第二,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译者的选题和翻译策略。第三、第四阶段尤其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第三阶段,国共两党都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确保中华民族的独立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所以他们为了配合抗战,译介了一些揭露日本侵略者凶残本质的侵华文学和在华流亡日本人的反战文学。而在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当权者为了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和侵华的合理性,译介了一些纯文学和侵华文学作品。第四阶段,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偏左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作品的思想内容是选题的首要依据,艺术价值是第二位的标准,所以只有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日本左翼文学和反战文学才得到我国译者的重视,其他小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排斥或轻视。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左翼小说自然不会受到青睐。除了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也存在有一定独立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某些内化在译者脑海中的思想意识也会在无意中影响译者的选题。例如在第一阶段时,清王朝日益衰落,梁启超等维新派对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不满,所以为了开启民智、实现变法维新,他们译介了日本的一些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
第三,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并重。在第一阶段时,译者的文学本位意识薄弱,他们译介的目的在于输入文明和借鉴日本近现代小说的思想意义,而不是看重其文学价值,所以他们译介的大多是二三流的通俗作品,而不是文学名著。例如他们几乎没有翻译二叶亭四迷、幸田露伴、樋口一叶、森鸥外、夏目漱石等名家的小说,尾崎红叶的小说虽然翻译了两种(吴梼所译的《侠黑奴》和《寒牡丹》),但不是尾崎红叶的代表作。而他们对二三流作家如押川春浪、菊池幽芳、樱井颜一郎、黑岩泪香等人的作品却翻译了很多,同时大量翻译的政治小说艺术价值也不高。第二阶段,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开启了研究日本文学的风气,所以这一时期的译者在选题时少了随意性和盲目性,开始把小说的艺术价值作为选题标准,译介了大量优秀作品。第五阶段,翻译家已经成熟,他们认识到了日本近现代小说的价值,因而全面翻译了属于纯文学的小说,而且有的小说有多种译本。同时为了满足普通读者的娱乐需要和猎奇心理,他们也翻译了大量可读性强的社会小说、家庭小说以及趣味性强的推理小说。王向远经过统计和比较,指出这一时期推理小说的译本约有270种左右(含复译本),占100年来日本文学译本总量的七八分之一,约占这一时期日本文学译本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森村诚一是20世纪中译本最多的日本小说家。[1]纯文学译介与通俗文学译介的共同繁荣是这一时期日本近现代小说译介的最显著特点。
第四,译者个人因素突出。相对于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而言,译者选择译本的自由是有限的,但这并不等于译者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译者虽然受意识形态等因素制约,但他们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翻译主体,可以在可供选择的材料中,选择契合自己价值观、兴趣爱好、翻译目的的作品,对于其他作品可以视而不见,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决定译本的具体形式。除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第三、第四阶段,其余阶段都明显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和个人风格。在这些阶段中,译者可以选择某一流派、题材类型的小说,也可以拒绝某一流派、题材类型的小说;可以用这种语言风格去表达原作,也可以用那种语言风格去表达原作;可以用直译的翻译策略,也可以用意译的翻译策略。正因为译者在对原作的选择、理解、表达中发挥了不同的主体性,所以不同流派、类型的小说在20世纪的中国才有了或被重视或被忽视的不同境遇,而且有的小说也有了不同风格的译本。译者的个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本世界的面貌。
三、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大大开拓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王向远所说:“一百年来,我国共翻译出版日本文学译本两千多种。日本翻译文学对我国的近代文学、五四新文学、三十年代文学以及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文学,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中国读者从这些数量庞大、类型各异的日本近现代小说译本中,不仅了解到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在思想上受到了启示,而且也从这些译本中学到了一些艺术技巧,从而为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转变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概而言之,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词汇上。实藤惠秀曾经考察过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两种辞典(《新名词辞典》和《新知识词典》,各收新名词6000多条),发现其中的日语词汇和与日语词汇结合的词汇占了大半。[3]高名凯、刘正淡合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和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也陈述了这一事实。例如高名凯和刘正淡指出:“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言的词都是通过日语转移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4]日语词汇进入现代汉语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留日学生的广泛应用,二是翻译的日本书籍的流行,可见日本近现代小说的翻译对输入日语词汇也是有功的。融入现代汉语的这些日语词汇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量,带来了许多新观念、新思想,而且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复音化和现代化,使现代汉语表达更加精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丰富也必然会带来文学表现方式的多样化,所以随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而来的日语词汇,首先在语言层面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第二,观念上。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处于末流,为中国传统文人所轻视。梁启超通过提倡翻译日本等国的政治小说,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文学观,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五四运动”以后,周氏兄弟对白桦派小说的译介,使中国作家发现了白桦派主张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些思想的合理内核。20世纪20年代末,后期创造社对日本左翼文学的译介,促使中国左翼作家在“阶级意识”上觉醒,并使他们把这种意识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由此可见,日本近现代小说的译介不仅对扭转中国文人轻视小说的观念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也在文学思想上给中国近现代文学以新的启迪,同时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轻视日本文学的观念,从而能在平等的条件下开展中日文学交流。
第三,形式上。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曾经借用了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的倒叙手法。除了倒叙,梁启超的“新文体”也来自于政治小说的翻译实践。在《佳人奇遇》中,他把原文的汉文调文体直译为中文,结果形成了一种半文半白的翻译文体,并受到学者文人的欢迎。日本近现代小说译介对中国小说形式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人称叙事、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等方面。中国古典小说一般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在翻译过来的日本等外国小说的影响下,中国小说家也开始用第一人称叙事,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例如,从赤裸裸地告白“我”的性欲的《沉沦》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第一人称叙事的魅力,也能看出郁达夫对日本私小说叙事模式的借鉴。另外,中国古典小说不太注重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很少用大段文字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描绘自然景物,而且在早期的外国小说翻译中,这些文字也经常被整段删去。随着日本等外国小说译介的增多,中国小说家开始适应这些描写技巧,并逐步加以模仿,所以中国的近现代小说才逐渐有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丰富的景物描写,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第四,题材上。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指出,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未涉及的题材类型,这4种题材都是从外国小说借鉴来的。[5]其实,这4种题材中,最早的政治小说和教育小说都译自日本,它们分别是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山上上泉的《苦学生》,而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中也有不少是直接译自日本或从日文转译的。例如直接译自日本的侦探小说有黑岩泪香的《离魂病》和江见水荫的《女海贼》《地中秘》等,从日文转译的侦探小说有加博里奥的《夺嫡奇冤》(转译自黑岩泪香的日译本)等。科学小说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来自日本,影响最大的科学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大部分中译本都是从日译本转译的。例如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依据的是森田思轩的译本。鲁迅译的《月界旅行》,依据的是井上勤的译本,而且鲁迅在这个译本的《辨言》中写道:“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6]由此可见,鲁迅当时的小说观也受到梁启超功利主义小说观的影响。除此之外,押川春浪创作的五六部科学小说也被翻译过来,如包天笑译的《千年后之世界》,徐念慈译的《新舞台》等。不仅如此,“20世纪初中国‘新小说’的主要的小说题材分类概念,几乎全都沿用了日本文坛在翻译西洋有关小说题材类型时所创制的汉字概念”,而且“对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这三种题材的优先提倡,同时也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启发。”[7]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对引进新的题材类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整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其中的四个鲜明特征,了解到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8],从而为我们从文化角度研究日本近现代小说在中国的翻译情况,提供了宏观背景和选题依据。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并深化日本现代小说翻译研究。
[参考文献]
[1] [2]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82-383.
[3]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310-311.
[4] 高名凯,刘正淡.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158.
[5]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97-501.
[6]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2.
[7] 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225-226.
[8] 范荣.林杼小说翻译策略的读者视野关照[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