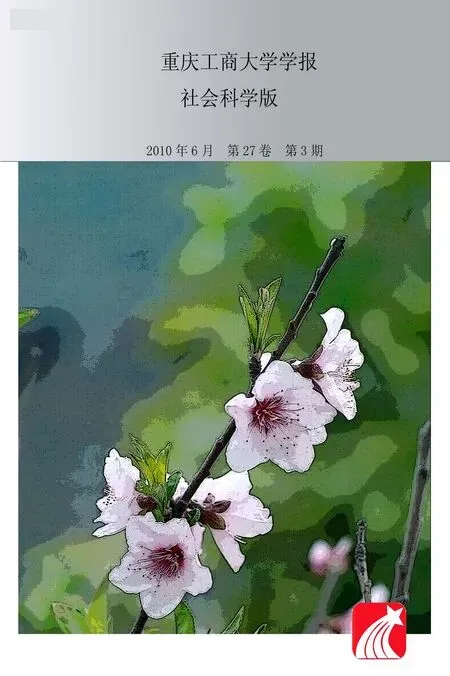配角与主角
——关于《又来了,爱情》的文化诗学
薛小玲
(福州大学 阳光学院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015 )
一、文献综述
多丽丝·莱辛(1919— )是英国久负盛名的女作家,她的创作生涯横跨大半个世纪。作品题材涉猎广泛,关注的视角涵盖政治、种族、女性、环保、宗教、历史、神秘主义等诸多方面,其创作风格求新求变。在莱辛的20多部的小说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她最早的作品《野草在歌唱》和最具有实验性的作品《金色笔记》。国外的评论界对于莱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研究、对作品中女性形象、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解读、观念阐释、相关作家(群)比较研究、文化研究、东方文化传统对莱辛的影响等。而在文化研究方面,主要是运用精神分析、社会学、音乐、意识形态、社会性别等领域的知识。国内对她的作品的评论多集中在主题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宗教哲学批评和形式研究批评等。但是,国内评论界对于《又来了,爱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正如这部小说中译者翟世镜所说,在“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今,这部书“让我们不要忘记老年人不但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感情需求,他们也盼望‘共享’爱和被爱的基本权利”[1]14。实际上《又来了,爱情》在回归现实主义时,虽然没有像《金色笔记》那样的标新立异,但它在朴实中无不体现了作者对于边缘女性在社会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注。本文将通过对边缘女性的对于爱情的追求的探讨:莱辛对于边缘女性和像她自己一样的老年妇女的感情关注,来引起整个社会对边缘人群的关注。美国作家罗伯特·斯特恩曾在他的《创造历史的爱情》(Lover Affairs That Have Made History)中写到“爱情婚姻是人类自然的欲求,是人类生产力的机制。[2]1”这位作家用了“创造历史”一词,且认为爱情是一种生产力机制。可见爱情在社会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的重要。保加利亚的学者瓦西列夫在其《情爱论》中说: “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连接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方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体。[2]4”
对于社会边缘人群的关注是新历史主义的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新历史主义不再只是把社会历史当作文学文本的背景,而是认为历史本身就是文本。历史只是众多“话语”中的一种,所以文学文本不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历史的主角。新历史主义将形式与历史的母体加以重新整合,从而将艺术价值与批评标志、方法论上的共时性与历史态、文学特性与史学意义等新母题显豁出来,使当代批评家开始告别解构的游戏,而向新的历史意识回归,实现了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型。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把文学文本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的范型。作为边缘批评,新历史主义直面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强调性别、种族、阶级、心理方面存在的对立和冲突,从历史的对抗中把握文化精神。新历史主义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将轶事趣闻纳入“权力”和“权威”的历史关系中,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在文本和语境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最终文本历史化变为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变为批评的政治。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1943—)以研究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为出发点,认为在文艺复兴不但产生了自我(selves),而且这种自我是能够塑造成型的意识。在格林布拉特那里,“自我”通常指“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是在生命活动中力图塑造自我而实现真正的善,自我意识将自身和一定欲望相统一,就产生了行为的动机,而“动机是行为中的意志”。人之所以具有意志,就是因为人不满足现状,力图通过自我塑造而趋向善。格林布拉特对自我提出定义:自我是有关个人存在的感受,是个人藉此向世界言说的独特方式,是个人欲望被加以约束的一种结构,是对个性形成与表达发挥塑造作用的因素。
二、朱莉·伟龙的自我塑造
莱辛说过:“出版一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用自己的个性和信仰去影响他人的尝试。” 1996年多丽丝莱辛发表了《又来了,爱情》。在小说中,莱辛采用了历时与共时并置的手法——“两个平行的世界”[1]65。作者打破了历时性叙事模式,解构了历史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同时作者也采用了历史和真实杂糅的手法,在小说中,朱莉·伟龙与拿破仑的情妇约瑟芬并行,八百年前的迪耶伯爵夫人的悲叹和朱莉的音乐并唱,朱莉与她三个情人的爱、斯蒂芬对朱莉的爱、斯蒂芬与萨拉之间的暧昧、萨拉与演员和导演的爱共存。小说的目的性就很强,作者想再一次借用小说来引起人们对于处于爱情荒漠地带的人群的关注,想要人们能够看到各个人群对于情感的需要。莱辛在自己的自传《影中漫步》中提到:这部小说中关于男人与女人以及小说中的老年人的爱情是显而易见的[3]309。要注意的是她所关注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们(年轻人)的爱情,她关注的是被遗忘的人们的爱情。萨拉是小说的主心骨,她把所有的人物和情节联系起来,但同时她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她是一个已过花甲的老年妇女)。
朱莉·伟龙和拿破仑的约瑟芬·德·博阿尔内两者都来自西印度的马提尼克岛,两个人的最终命运都是遭到了抛弃。虽然朱莉和约瑟芬是一样地不甘命运的摆布,但是历史决定她们的悲剧,所不同的是人们对约瑟芬的评价永远地停留在了不能为拿破仑传宗接代而被休的命运。而《又来了,爱情》中的小人物朱莉,却在死后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写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改写了社会的历史,不仅让自己的作品流芳百世,也让自己的爱情传唱至今。
从母系社会瓦解,妇女遭受历史性惨败之后,女性的奴隶时代恰好与男性中心文明同时存在。未来社会,女性将会从整体转败为胜,成为与男性互补的世界的主体与创造者[4]156。朱莉是一位黑白混血女人的女儿,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位白人种植园主少爷的情妇。朱莉的出生——性别、血统就注定了她一生的命运。也就是说朱莉的历史不是她自己能够书写的,而是已经书写好的,所以作者特别强调了朱莉生活的时代。所谓的正统历史已经决定了她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无论是保罗、雷米、菲利普还是史蒂芬,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地与朱莉修成正果:保罗是不成熟的爱人,雷米是迫于社会的压力,菲利普也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史蒂芬更加是不可能穿越时空和阶级。这一切都是爱情与权力之争,而爱情在权力面前往往都被动的,受压制的。女性的压抑和她们的真正权利之间的紧张,根源于事实上女性所掌握的典雅之爱,这一反映中世纪贵族政治的“实际权力”,但这个爱作为融通调节的理想被功能化了,就掩盖了“它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的紧张”,诸如父权制婚姻[5]74。
“她的确大部分时间都在恋爱,但这不是她的任务。我们不能演出这样一出戏,说一个女人被两个情人抛弃后自杀了,我们不能塑造这么一个罗曼蒂克的女主角。[1]47” “她的故事应该有个诠释,她自己的诠释。[1]48”这是当代排演者对朱莉·伟龙的故事的理解,也是朱莉对自己以及对社会历史的书写。这位奇女子出名不仅因为她与贵族男子的“禁”爱和热恋,还有她的诗歌,日记,画以及她的音乐。她是一个具有伟大智慧的女性,她通过自立,热恋等方式来反抗所谓的传统。典雅之爱的性别特征……代表了一种(封建女性的)性别的和感情上权利的意识形态上的解放,而必须有一些社会参考。至于这种爱情关系实际上是否存在或者加入他们有自由的习俗,这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关于意识形态真正的课题是,更准确地,什么类型的社会能够假定婚姻之外的爱情关系为一种社会理想?什么是哺育特定社会习俗而不是哺育更多众所周知的女性贞洁或女性依赖的一种社会状况[1]26?权力在社会上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某种被一个精英集团所占有和控制的,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它更像一张被磨损的美元账单无始无终地从一个缀着钻石的钱夹通过一个磨破的口袋,并再次回来[5]14。也就是说你是否拥有权力,你什么时候拥有权力,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你是否是主角,你什么时候成为主角,这就像一张流通的纸币一样,主角是不停在转变中的,你可能成为一时的主角但是你最终都是配角。在这个表象的世界中,没有人能永远是权力的拥有方也没有人永远是被压抑的配角。朱莉就是一个不甘受到历史摆布的女子:她的书架上的藏书显示出一种更加平衡的倾向。蒙田的散文与罗兰夫人的著作并列……而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和左拉没有理由不和伏尔泰分享空间[1]22。最终朱莉成了“我们(贝尔河镇)的朱莉”,而贝尔河镇和成了“朱莉的贝尔河镇”,那儿有三个旅馆都是以朱莉的名字命名的。保罗的家庭和雷米的家庭都乐意为朱莉·伟龙节作贡献,因为这将给这个小镇增添光彩[1]58。朱莉在死后成了贝尔河的缪斯女神,而在生前她是杀死自己婴儿的女巫。朱莉在以自己的方式向世人言说自己,同时她也塑造了一个镇的人民的信仰。权力在这里瓦解,个人在创造新的历史。而在爱情中,女性往往是男性爱情的注脚,莱辛的《又来了,爱情》从女性的角度来关注爱情,可以说是改变了女性这个注脚的角色。她关注的是女性的爱情体验并且对她们在爱情中的感受进行聚焦,而不仅仅是在男性恋爱中来增加一个情人。虽然在《朱莉·伟龙》这幕剧中萨拉不得不使用这样三幕:第一幕:乔治;第二幕;雷米;第三幕菲利普。但是萨拉·德拉姆事实上已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自由女骑士”的形象。朱莉已经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的注脚,而事实上这三位男性只能是朱莉的三个过往的情人而已,是朱莉选择了他们,或者说是莱辛写作的需要选择了他们。他们并不能在朱莉或萨拉的生活中扮演任何主要的角色。作者复原一位像朱莉·伟龙这样女性的描摹只是为了使她成为另类历史具有象征意义的主角。朱莉是因为是受到了历史的质疑后又恢复名誉的配角所以受到特别的青睐。这给人们对于当时历史的理解提供了另一种不容忽视的视角。
三、萨拉的自我重塑
朱莉·伟龙不仅吸引了一群人,而且完全的改变了他们。而这出戏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她改变了一个守寡多年的人——萨拉。萨拉在戏里戏外,展现了她的魅力,同时也使她陷入了爱情——这一她已遗忘的生命力和生产力。
在1982年,联合国大会签署了《国际老龄关注行动计划》。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对老年人在政策上给予重视。它的目的是使社会和政府更加有效的处理老年人口和老年需要的问题。情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它对于男女老幼是同等的重要。但是老年妇女的爱却总是在不知不觉间被剥夺了。女性主义理论家Simone de Beauvoir在《老年》中认为,老年人不能被当作是一种东西或者机器,在他们年老对社会没有贡献时就弃之不顾[7]156。
莱辛通过描述萨拉对于Bill的欲望,对Henry的爱情以及与Stephen 的友情来关注老年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们该如何改写甚至创造自己的历史。萨拉在65岁时,重新感悟了人生:爱情、亲情、友情。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感情生活其实是重于物质生活的。莱辛曾经说过:关于老年问题。我想表明一个观点,有的人决定变老,至于为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很多人坐在那儿等着变老。事实上,我认为不变老是很容易的,虽然要保持年轻不容易。很显然莱辛说的是心态问题,而不是健康问题。当莱辛在谈到创作《又来了,爱情》时,她说:“陷入爱情,我是说情欲,令我着迷。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不知道它的用处。但是它来的时候很强烈,猛烈,具有破坏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又来了,爱情》。”当莱辛自己在65岁又陷入爱情时,她感到了爱情的猛烈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悲伤,但陷入爱情的人的所具有的活力使她重新焕发出青春:她步履轻快,思维敏捷,“那位妇女正精神饱满地忙碌着……精力充沛的动作时,很容易把她想象为年轻人”[1]1。
《又来了,爱情》写于莱辛76岁之际,当时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社会问题。当人们关注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之际,往往会忽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老年人这个边缘群体的感情需要。当代关于爱情的小说可谓数不胜数,但是年长女性和年少男性的爱情还是禁忌,这就和社会的男性主体和历史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社会中,当恋爱的双方中,女性比男性年长时,社会对于这种“爱情”还是有保留的态度的。小说在浪漫(朱莉和萨拉的爱情)与理性(朱莉和萨拉清醒地意识到和分析她们的问题),在幻想(朱莉的故事)和现实(各个扮演角色在现实中的复杂丰富的生活)之间对照。《又来了,爱情》唤起了社会的禁忌,追寻的是人类的爱情的根。这样的禁忌之爱我们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时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间的仇恨家族之间的爱情,我们可以在劳伦斯的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找到相似的描绘:这些都是禁忌之爱的传统。《又来了,爱情》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罗曼史,它透过爱情这个古老的母体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人们和社会契约之间的那种遵循又反抗,被约束又改造的矛盾统一,这部小说以边缘人的爱情颠覆了传统历史中的爱情母题。
由于当代社会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社会乃至全球性的问题,莱辛对于老年人的(特别是老年妇女的)爱情需求的问题的提出和关注使小说本身更具有时代的意义。同时作者莱辛又把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设定在戏剧的场景中,这更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她能自由穿梭于“戏里戏外”。正如《又来了,爱情》中所说的 “在最后……那些主要角色并非毫无陪衬地在一个又一个场景之中登场对抗,在大多数场合,是一对一对地出场,实际上主要角色是被合并到一组次要角色之中。在最初……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配角,现在却显示出他们对主人公命运具有多么巨大的决定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1]129”在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生活的主角总是年轻人,老年人只能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的配角,无论是在生活的任何场景中,即使是在爱情上也是如此。但是“她曾经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牺牲品,现在她应该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力。[1]15”
四、结语
历史学家明显需要强调会超过其他历史角色的一定的历史角色, 但正如福柯所说“权利不是一个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被赋予的一定的勇气,它是人归因于在特定社会中的一种复杂的战略境况的名字。[8]93”权利无处不在,但是它也可以是像货币一样的流通的。新历史主义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是文化的制成品。[10]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莱辛注重的是社会的配角们在怎样的进行自我的塑造,即社会的权力和历史是怎样在流通中不断被取代和改写的。莱辛是一位有着社会担当的作家。她说过,个人不可能脱离她所处的那个时代, “一个作家应该代表她所归属的,所负责的,本人又无法言说的人们去说话。”显然莱辛是用小说这种文本在言说一群人的历史,表达一种人性。
[参考文献]
[1] 多丽丝·莱辛. 又来了,爱情 [M]. 瞿世镜,杨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 金永华,金铮琦.影响世界的爱情[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1,4.
[3] Lessing, Doris. Walking in the Shade [M]. Great Britai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7: 309.
[4] Gilligan, Carol. 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56.
[5] 诺曼·J·威尔逊. 历史角色——理性、性别、阶级和话语结构[C]//红苇,译. 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 吴士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51-74.
[6] Joan Kelly (U.S.A). Female, History and Theor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26.
[7] Beuvoir, Dimone (France). The Coming of Age[M]. Trans. Patrick O ’Brien. New York: Warner Books,1972:156.
[8] 福柯.性史 (第一卷):一个导言[M].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3.
[9]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93-413.
[10] 王业昭.女性主题的延续与升华——释读多丽丝·莱辛的《善良的恐怖分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