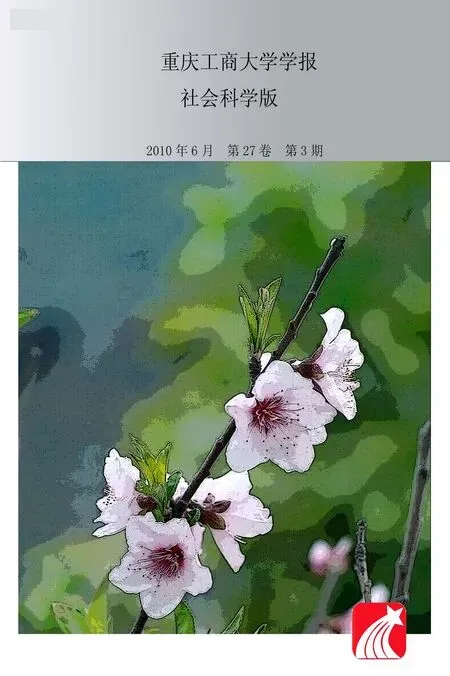论世情小说名著《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体例的生命承传
张鹏飞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蒙城 233500)
一、《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范式的文化承继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思想始终崇奉着“男尊女卑”的道德理念,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存在而丝毫不享有人生的自由权利且在婚姻问题上主要是承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凄惨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譬如说,《水浒传》作为一部收集前人资料整理演义而成的小说名著却深受儒家文化“三纲五常”道德规范的影响而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女子婚嫁观的审美烙印。比如段三娘曾与王庆交手又主动托媒求亲。但《水浒传》作为忠实维护传统妇女婚嫁观的文学典籍却这样评价不守“闺训”段三娘:“从小不循闺训,自家择配,做下弥天大罪,如今身首异处,又连累了若干眷属”。[2]强调女子自家择婿的正当举动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同时论述:“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是打死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了他的权力罢了”。[3]由此,封建贞节观其实是男权意识对女性的一种行为规范以及身心自由上的道德限制。可见,古代社会要求女性贞节可以说是个颇具世界性的普适问题,但在封建宗法制森严的中国,也许更为突出,并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基本纽带之一。[4]然则《金瓶梅》人物刻画中业已了无传统文化思想规范的约束功效,而是体认着芸芸众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封建礼制及程朱理学的嘲弄、亵渎与叛逆以及传统价值观念在市井平民社会阶层中的贬值乏味和对人生在世的享乐生活的孜孜不倦地渴望吟诵。即社会转型期带给世人的唯有道德的迷失、行为的失控、野性的张扬、神圣的荡涤,伦纲的不复、佛道的疑惑和信仰的动摇。自此,中国文学演绎开始拓进到礼教人伦的封建禁区并突显着小说艺术苑囿的新境界。
《金瓶梅》虽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演绎的长篇小说名著,但其叙事体例却多半是依托于《水浒传》而加以演化生成。比如说,《金瓶梅》第九十二回“陈经济被陷严州府,吴月娘大闹授官厅”的回首诗“暑往寒来春复秋”源自于《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叹曰“事遇机关须进步,人逢得意早回头”。感喟时光短暂且富贵在命不由人的劝诫意图。《金瓶梅》第九十七回“经济守御府用事,薛嫂卖花说姻亲”的回首诗出自《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宣讲着贫富由命、穷通在天的宿命论。《金瓶梅》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张胜忿杀陈经济”的“一切诸烦恼”发自于《水浒传》第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之回首诗等。[5]皆表征着作者创作思想义理与立身处世思辨的心有灵犀的契合融汇。故而张竹坡品评:“《金瓶》内之西门,不是《水浒》之西门。且将半日叙金莲之笔,武大、武二之笔。皆放入客位内,依旧现出西门庆是正经香火,不是《水浒》中为武松写出金莲。为金莲写出西门。却明明是为西门方写金莲。为金莲方写武松”。[6]即言兰陵笑笑生演艺故事虽有模仿之处但却是顺着西门庆一支线索自然而然、有条不紊、栩栩如生地加以铺陈叙述。
《金瓶梅》虽说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型作品”或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拟话本长篇小说”。[7]然则黄霖曾在《<忠义水游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统计了《金瓶梅》中盖有27个人物与《水浒传》源出同名。又将《金瓶梅词话》和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加以对勘就找出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描述12处,《金瓶梅》模仿《水浒传》的韵文54处,认为《金瓶梅》承续的是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而刘世德先生通过对《金瓶梅》与《水浒传》比勘则认为:“《金瓶梅》作者袭用《水浒传》文字时。既参考了天本(天都外臣序本)又参考了容本(容与堂本)”。[8]像欣赏者在文本对读中皆可发现《水浒传》与《金瓶梅》有相当程度的融通之嫌。譬如,《金瓶梅》第二十回“盂玉楼义劝吴月娘,西门庆大闹丽春院”的回首诗“在世为人保七旬”所表达的即是听天由命、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就源自于《水浒传》第七回“郓哥帮捉骂王婆,淫妇药鸩武大郎”的回首诗“参透风流二字禅”的莫计得失、安贫守拙的生命理念。
《水浒传》故事的成书可谓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历程。它产生于北宋且酝酿、丰富、流传于宋、金、元并一直延续到明初的多事之秋。加之施耐庵《水浒传》的叙写始终认为汉家一统的难以为继切实表征着忠义不在朝廷。故而另辟蹊径地借助民间广为流传的宋江故事来振呼忠义报国。李卓吾则主张:“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那些“有忠有义”的“大力大贤”之人不愿“束手就缚而不辞”就聚集水浒之地。“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9]然则《金瓶梅》小说故事的产生却有着迥异的历史文化渊源。兰陵笑笑生所面临的是一种近乎粉饰太平表象下的盛世繁华。再者,程朱理学扼杀人性的本质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及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的质疑和颠覆。故此“物极必反”的事物运动规律又导致了明代中叶以后人欲的泛滥与肆虐的矫枉过正的现实生存窘境。
二、《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样式的艺术嬗变
《水浒传》小说叙事中包括西门庆与潘金莲等主要人物在内的诸多形象或姓名却承续在《金瓶梅》叙述中反复出现。然其故事显然经过了程度不等的改写编撰。诸如《金瓶梅》关乎世俗人情的叙事是注重以小说得名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主要女性形象加以描摹。虽说人物出身、性格和遭遇皆有差别,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却有着一种共同的超乎寻常的对于情欲、物欲和肉欲的渴求或是对赤裸裸的人性的自然欲望的求索。而潘金莲可谓是淫荡、狠毒、欲望的鬼魅化身。即所谓“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10]但毋庸讳言,《金瓶梅》中的确尚有一些地方过多沿袭着《水浒传》中的大片整段的文字叙写和诗词韵文。张竹坡评介:“《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竞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无论”。[11]可以说,《水浒传》与《金瓶梅》是明代两部承续关联契合的小说典籍。袁中道指出:“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12]从小说发展的角度观之,自《水浒传》到《金瓶梅》可谓是体认着小说叙事范式由历史传奇向世俗人情叙事转化的演进轨迹。因此,沈德符评曰:“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13]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14]可以说,《金瓶梅》着力展现了晚明时期平民百姓所信奉的离神、解咒、祛魅的现实境遇,世人不再以传统的宗教伦理思辨来束缚性灵,也不愿将人生幸福寄托于来世托生而去忍受现世的诸种苦难磨砺却尊崇当下肉体的快乐欢娱以及奉行着“快活了一日是一日”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阳沟沟里就是棺材”的人生哲学。因此,中国传统佛教文化中的“因果报应”观念作为一种信仰虽说可给民众提供一种敬畏崇奉和形而上的生命关怀,然则吴月娘就始终认为潘金莲“原不是那听佛法的人”。如同马尔库塞所指出:人可以根据充分发展的知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重新提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的问题。[15]即寓意着潘金莲对佛教的来世愉悦的说教不感兴趣而常常毁僧谤佛且变得无所畏惧的去追求当下的生命体验并干尽了毒杀武大、害死官哥,陷害来旺、逼绝惠莲等彰显着道德虚无主义生存理念的恶劣行径。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所充满的动荡和变革的转型体征就突出地的表现在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文化变迁。概因明中叶以来的城市全面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壮大、政治斗争尖锐、王朝更替频繁的诸多社会大动乱,导致了理学信仰的危机和异端思想的抬头,加之雅俗文化的日益对流与中西学术的初次碰撞以及处此复杂多变环境里的士人骚客心态的无助、狂放、抑郁、渺茫的矛盾汇集情愫。凡此种种,社会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心理因素的整合贯通致使晚明社会日趋推崇个性宣泄的文艺思潮的诞生。正如沟口雄三评介:晚明思想界的变化是经济与社会深刻巨变的伴生物;这其中,对“欲”的肯定和对“私”的主张,是儒学思想史上一个根本的变化。[16]可以说,《金瓶梅》小说叙事中两性关系的露骨化描写孕涵着对封建等级秩序的公然蔑视和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叫嚣宣战,它突显了世人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和个性本体的张扬以及渗透着人的本能解放与社会创造及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譬如说,西门庆针对吴月娘要其“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却不攒下些阴功”的善意规劝却在《金瓶梅》第五十七回公开宣称:“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17]李卓吾评曰:“成佛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18]体认着“三教合一”下的晚明社会境况和泰州学派的阳明心学观照下的审美取向并预示着传统伦理道德之下的世人心灵的躁动和对人性肆意发泄的希冀。
从接受美学观之,《水浒传》叙事中潘金莲是个“淫妇”欲女而西门庆是富而好淫。然涉及《金瓶梅》的相关情节的两个人物的基本风貌仍然未有迥异质变。即言兰陵笑笑生所接受的不仅是潘金莲、西门庆的名字而主要的却是接受了人物形象的生命体征。换句话说,西门庆和潘金莲惟有在《水浒传》现有“基本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和演绎,否则将背离读者欣赏的期待视野。即《金瓶梅》的叙事情结不能完全摆脱《水浒传》的“阴影”或偶尔必须牵涉关情到《水浒传》,可以戏说是“《金瓶梅》中的水浒”。同样,人类喜欢猎艳趋奇又是其天性本真使然,而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有趣、诱人则是古今中外小说家从事创作时所偏爱的审美效应。像《金瓶梅》在被翻译到西方出版发行时就在书名问题上煞费苦心而绞尽脑汁地突出其故事性、媚俗性、趣味性和煽情性。诸如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巴赞所译的《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1927年纽约出版的《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1930年出版弗朗茨·库恩翻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他的六妻妾之艳史》、巴黎出版公司1949年出版的让·皮埃尔·波雷编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妻妾奇情史》等就是颇含意味的典型范例。[19]可以说,《金瓶梅》借用一部小说去接受另一部小说的特殊接受方式又与小说叙事范式中的续书演绎有所差异,但《金瓶梅》中诸多人物显然被作者加以“改造”深化。像武松在《金瓶梅》中就完全变异,“这位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一落到人间就成了芸芸众生。西门庆才是‘虎’,是‘英雄好汉’,是强者;在西门庆面前,武松变成了‘羊’,是凡夫俗子,是弱者。《水浒》中杀嫂祭兄、仗义自首的慷慨悲歌的场面不见了,光明磊落、义薄云天的英雄,变了卑微琐小、凡夫俗子”。[20]即小说叙事模式可谓是由作者的自由思维所建构。《金瓶梅》诞生之前的长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承受史传文学思维的百般观照而大多展现神秘虚幻的非现实生存空间且构成了叙事情节的离奇怪诞、跌宕起伏和生动传神。然则《金瓶梅》故事情节的叙述空间却洗涤了神仙佛教所赋予世人的神秘观感且聚焦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幻化梦境。
《金瓶梅》小说叙事中却张扬着作者的人性关怀和哲学幽思并试图寻觅到生命的信仰而重建世人的精神家园。它强调着尘世万物的幻化、痛苦和空虚,意在唤醒读者对生命本身的反省抗争。恰如作者在卷首词所吟:“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旨在唤醒读者对生命本体的自觉感悟并以此奠定全书的审美基调。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所言:“我从超越的存在中能了解到的是,我们所寻求的行为是一个纯粹的虚构”。[21]坦言人生的欢乐、痛苦、欲望皆为生命幻影,所谓弹指间去来今,显示着无法救赎欲望而慰藉众生的悲凉、怜悯和哀叹。故而清代张潮在《幽梦影》评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张坡竹亦主张《金瓶梅》是一部“炎凉书”。[22]比如说,《金瓶梅》小说演义中的潘金莲就是一个对传统婚嫁观最具挑战性的世俗女子形象。她虽遭际命运的不幸坎坷但却对人生表现着强烈的愤懑抗争。当张大户将之许配给“身不满尺的丁树”般的武大郎时就突显其面对强迫的不合理的“婚姻”的强烈哀怨。盖因武大郎“生的身不满三尺,为人儒弱,又头脑浊蠢可笑”。清河县人见其“模样猥衰”。起了他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23]故而叹息身世:“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嘛酒。着紧处,却是锥扎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24]于是乎整日“打扮油样,沾风惹草”而变得更加轻浮、招摇和淫荡,看似“春心”骚动的青年女子的正常心理追求即是对男性压抑的某种报复以及对封建礼教与伦理道德的一种控诉且富含追求自由幸福、性灵张扬和个性解放的生命情韵。它体现出作者对遭受传统婚姻制度戕害毁灭的妇女的深切同情以及对造成女性身心痛苦的婚姻制度的强烈不满,也是《金瓶梅》在妇女自由婚姻理念上对《水浒传》传统婚姻观的超越升华。
综上所述,《金瓶梅》可谓是一部出现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摹写市情世相的写实主义经典小说,它是对当时的现实社会、人生百态、世俗民事的真实、生动、自然的高度贴近化的叙述描写。然则《金瓶梅》叙事情结可谓彻底涤除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水浒传》等由市井弹词到文人写定的近乎道德评判的文化心态,而是以冷静、客观、宽容的叙事摹写对诸多人物形象的行为举止加以真实的披露刻画且认同着某种菩萨般的慈悲心肠并传达出哲人思辨的悲哀怜悯,从而彰显着意味隽永的生命情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
[2] 施耐庵.水浒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1:169.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2.
[4] 李新灿.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5.
[5] 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87.
[6]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7:62.
[7] 周钧韬.《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J].社会科学辑刊,1991(6):26.
[8] 刘世德.《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5):22.
[9] 李贽.焚书续[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9.
[10] 侯忠义.张竹坡评点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8:66.
[11] 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C]//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589.
[12] 袁中道.游居柿录[C]//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229.
[1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C]//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230.
[14]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71.
[15]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6.
[16]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1997:27.
[17]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76.
[18] 李卓吾.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
[19] 胡文彬.金瓶梅书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9.
[20] 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8.
[21] 耿春红.庸众的沉沦和哲人的悲哀[J].明清小说研究,2005(3):75.
[22] 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444.
[23]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一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8.
[24]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香港:明亮书局,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