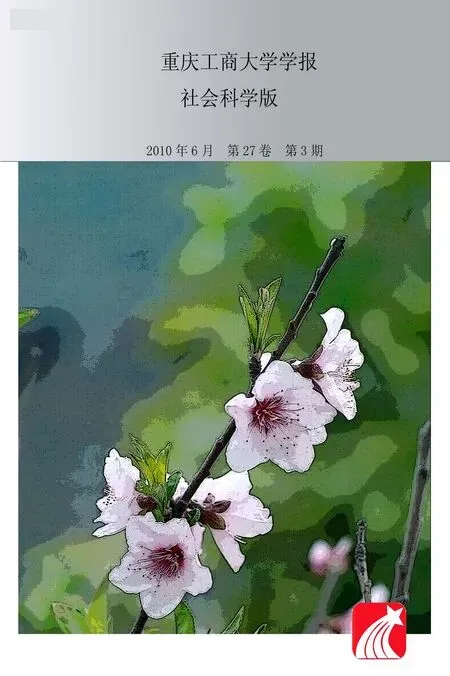文学研究的宏观视野与理性阐释
——评《迟到集:学术思辨与艺文随笔》
张中宇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4)
胡明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作家与流派研究,集中于中国古典文学,从魏晋到明清,有相当广阔的视野,而不止于某一断代之文学。第二是文学的宏观考察,包括文学基本理论,重要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及相关问题的思考,这一部分融通古今,但更多以当代文学作为切入点与着眼点。第三是文学与文化的综合研究,这部分是近20年的主要工作。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分上下两册、近80万字的胡适研究[1],其后有21世纪初的陈独秀研究[2],及最近的瞿秋白研究。胡适、陈独秀、瞿秋白既是20世纪前期中国新文化运动或政治运动领袖,在文学方面亦多建树,如胡适新诗,陈独秀旧体诗,瞿秋白散文随笔等,或开一代风气,或领一代风骚。这一部分研究也集中在文学与文化思想的交融、互动。在部分的研究中,文化思想发展轨迹的阐释实际上是一时代文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与潜隐动力;在另一部分的研究中,对思想文化的探讨更为幽微深致,有更多对中国现代社会及未来方向的凝重思考。
新出版的《迟到集:学术思辨与艺文随笔》(辽海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以下凡标明页码处均出自该著)分为五部分。一、二两部分依“序”中说,是以风格的不同安排,都是关于文学的宏观考察。第三部分为文学与文化的综合研究,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思想都有典型的选择。第四部分序跋和书评,大致属于文学或文化的宏观思考。第五部分则是作家与流派研究。《迟到集》各部分正好构成胡明先生学术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及其基本风格。
关于作家与流派的研究多在学术生涯的前期,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较少看见。家乡徽州深厚文化积蕴的浸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环境及惊人的勤奋,胡明先生对古今中外典籍有相当广泛的关注,这些分布于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及流派研究——从魏晋到明清,从三曹到《红楼梦》,构筑了他对文学宏观脉动极为厚实的全景考察与准确把握。进入90年代,从研究胡适开始,在宏阔的背景中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展开系统绵密的阐释。
这部新著醒目地放在一、二两部分的,是关于文学宏观问题的考察与研究。《70年文学谈》是一篇近2万字的论文,最初载于《文艺争鸣》1989年第4期,全景式地回顾了新文学70余年(1919—1989)的重大事件及重要进程。要阐释这一跨越大半个世纪、头绪极为纷繁、争议颇多的新文学从发生到壮大的历程并不容易。胡明先生抓住新文化发展的主线,相当清晰地勾画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宏观轨迹、五四前后的文学发展,二三十年代文学,抗战文学的特质,解放区文学气象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整风,“文化大革命”,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与复苏等,纵横捭阖,澎湃激扬。《70年文艺谈》相当清晰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重要现象、文学运动及其发展的深刻动因,为新文艺发展留下颇多启迪。
从社会文化的宏阔视角来考察文学现象的生成、运动乃至相互影响,以及文学的特性、价值等宏观问题,善于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寻捕内在的精神实质,是胡明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这从早期的作家、流派研究——这些大致属于文学的个案研究,就可窥出端倪。正是着眼于宏观的习惯,他的思考往往直逼文艺的重大及实质性问题。这部新著中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责任》《贯通古今寻索真知》《历史·历史观·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文艺学的前沿、热点与高层》《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伦理与逻辑起点》《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现代性——兼谈人的精神家园看守问题》等,均就文学领域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他对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尤为关注:
当前的文学研究各学科大体来说,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头工作是从史料的整理走向史料的解释,在已经差不多做完的文献整理工程的基础上搜寻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为3 000年一部古典文学史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判断,为各种各样悬而未断的“问题”拟出学术结论。现当代文学的工作重心恰好相反,从大量现成的历史结论与定性标签走向艰苦、繁琐的史料的发现、整理与分析,改写结论与撤换标签常常是更为迫切的常规功课,显然过去的史料解释工作和定论定性工作做得太匆忙、太草率、太简单片面了,而指导和规范上面两大板块操作运动的又正是文艺学理论研究的时新成果。(《文艺学的前沿、热点与高层》,第40-41页)
这篇最初发表于2005年的论文敏锐地观察到文学研究两大领域开始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值得注意的在于,这里提出的是两大基础学科领域需要发生的良性变化。中国古典文学较长一段时期以来以搜寻、整理文献为己任,但当然不应止于文献整理,忽视文学规律的研究,古典文学研究也不能仅仅成为“古典文献学研究”。“差不多做完的文献整理工程”固然有对多年来文献整理的充分肯定,恐怕更多则是对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强烈期盼。“如果说‘以汉还汉’、‘以唐还唐’的史料整理为的是‘不诬古人’,那么科学正确的史料解释工作以及理论规律的寻索则是为了‘不误今人’——它的‘现代责任’与‘现代价值’无疑更重大。史料的解释基于高度学术理性与纯粹学术智慧,这一份认识判断的工作本身就是十分艰难的,而理论抽绎与规律探索更是深化史料解释的题中应有之义……做学术研究重在出思想,出见解,出断制,史料的解释是学术发展、文明进步的主要表现和核心内容,即史料的‘整理’只是为‘解释’服务的。”(第28-29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责任》最初发表于2003年,比《文艺学的前沿、热点与高层》还要早两年,这些思考不但前后一致,而且恐怕在两大学科领域发生变化之前,作者就预见到或者说期待着这种变化的发生。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研究往往急于给出某种阐释甚至急于下结论,却忽视了材料的充分采集,原始证据的全面寻索,只有回补这一部分的工作,现当代文学研究才能在更厚实的基础上前行。《贯通古今寻索真知》从另一个角度探索两大学科的关系:
中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条块分割、人为断裂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尴尬与混乱,在知识论的传播与应用上更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与陷阱。我们的两个二级学科: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在一个历史临界点断裂,互相之间筑起了高墙深堑,生发了深厚的隔膜……这种二元分立研究格局至少使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过程得不到清晰合理的阐释与发明,她的细微而真实的发展逻辑的层次感、内容隐显和聚散离合的信息也得不到深细而完整的描述。……中国文学研究的纵深推进与质的飞跃更失去了必要的依托。……要改变这种雍滞堵断的学术局面,只有提倡古今演变的贯通研究一途。(第90-91页)
另一篇《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伦理与逻辑起点》也是对学科建设的思考:“大约在人们想到中西医结合的十多年或二十年后,也忽然想到中西文论(古今文论)学理上的结合。主导舆论立即形成三个时序的要求:先是共存互补,再是转化转换,最后是融会贯通。为了这三个要求的实践,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界忙乎了近十年。但成绩不大,问题不少。”(第51页)实现古今、中外的融通,关联着中国文学研究质的提升与长足进步。大概受徽州老乡胡适(或许还有陈独秀)影响极深,胡适从古今演变、中西比较来观察、评价中国文化与文艺,判断中国的未来走向,胡明先生选择的基本上也是这样一条路经。他发现,由于已经习惯于“分割”“断裂”的体制,要真正有效打破“分割”的研究方式,尤其是改变“断裂”的思维方式,并非易事。
胡明先生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富于激情的阐释方式。激情来自于对学科的强烈兴趣,它促使研究者处于高度兴奋及活跃状态,往往可以激发科学的灵感,推动科学的发现与创新,或许还需要指出的是极深厚的文学修养。我们不要忘了以胡明先生为主翻译的120万字的《狄公案》。翻译固不同于创作,但文学的翻译往往具有相当的再创作成分。傅东华译《Gone with the Wind》,把一本美国的通俗小说演绎成一部文学经典,若没有翻译者的文学才华与生花妙笔,尤其是文学思维的创造性发挥,恐怕是难以做到的。[注]傅东华译本有部分删节,人名、地名等的译法也存在一些争论,但仍不失为早期的代表性译本。《狄公案》译本“用仿古白话译出,做到面貌神似,灵魂嵌入,语言精彩,文化到位”,“改善高氏的原文中国气味不足”(第324页),我们不难体会其中的文学创造。译本出来引起期刊、出版社争相刊载、出版,继而电影、电视的改编播演,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狄公案”高热未减,其中也颇多无视译者辛劳的侵权困扰,都从一个侧面证明翻译的成功创造与巨大影响。若不是人的精力有限和学术研究的巨大消耗,我猜想胡明先生大可创作出自己的韵味十足的文学作品。顺便说,开启一时代风气乃是极为重要的标志。除了掀起持续数十年的“狄公热”,他的胡适、陈独秀研究在海内外也极有代表性,在某种意义上开启或引领了这些领域的当代研究。这些特点使他在阐述学理的时候不但着眼于宏观与幽微,而且文情并茂,妙趣横生。兹迻录数例:
文艺学自身的格局建制与历史要求恰恰在这个关键时段有点脱了节,有点慌了神。文艺学的理论探索与学科规范被社会经济全球化“举世滔滔”裹挟而行,不免步履踉跄,力不从心。抬望眼,西风渐紧,语境丕变,“眼见长江趋大海,青天却似向西飞”。不免又心眼失衡,视野模糊。近些年来,我们的文艺学“热点”一个紧挨一个,“前沿”不断前移,为了追上层出不穷的理论新思维与变幻万千的学术新语码,我们亦步亦趋,换了一茬又一茬关键词,……等我们再站立定学术视窗前,文艺学的图景已经大变了,“理论”的航船已驰到了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前沿”,“审美”重心已经移出了“文学”的边界,在“文化”玄妙吊诡的波涛里打转。(《文艺学的前沿、热点与高层》,第41页)
这些论述或惟妙惟肖,或语带锋毫:“50年代初的文化政策基本上是解放区的有关文件扩大发放范围,正如当时具体领导文艺工作的周扬所说:‘我们今天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基本上就是明天要在全国实行的’(《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在实际完成了解放区文艺模式改造的第一步后,清算个性解放与人的自由主题的文化任务便提到了日程上。在‘文艺整风’中,凡是从解放区走进北京的作家们已经获得了某种有限度的免疫,国统区过来的进步或非进步作家是主要的教育对象。”(第81页)究其原因,文学本来就是有血有肉的精灵,而非死板的岩石样本,文学评论就有了通灵活泼的特质:
“秦学”与其说是一种红学研究成果,毋宁说更像一部作家杜撰的小说。这种新文体的小说比旧式的索隐探佚更有趣,更曲折,更有情调,作者也需更多的才情与智力。“秦可卿”的小说,大抵也可自圆其局,因为有许多假设,有许多猜测,无需认真解答;有许多情节设计与小说的构思布局一样,可以草蛇灰线,逻辑暗连。有人作案,就有作者来最后破案,有人设谜,就有作者来最后解谜。这样一座空中楼阁,这样一镜水底明月,无疑更有文化审美的意境。即便有过度诠释、深文周纳之嫌,作为创作的文化作品毕竟还有设计精巧、灵气透彻的一面。这是作家的优势,当然有可读性,有收视率,有观众,有读者,有粉丝,俘虏了一大批人心,也为盛世的文化事业增添了一道胜景。(《红学的颜色革命与学术狂欢》,第24页)
在神州红学界对刘心武“秦学”一片挞伐中,只有从新的角度思考,才能对文学领域的新问题进行有效诠释。一部《红楼梦》绝非只能从学术角度进行解读,更不是只有一个红学评判中心。兰陵笑笑生可以从《水浒》横生出一部《金瓶梅》,刘心武当然也可以从《红楼梦》演绎一部“秦学”新传奇,这并不需要“红学”发放许可证。刘心武本为小说家,即便他假借“学术”的方式——就像古典小说假借“历史”的方式。不少人却忘了从小说角度去看“秦学”,去发现“有许多情节设计与小说的构思布局一样”,去鉴赏“设计精巧、灵气透彻”,反以“学术”而且还是很死板的“学术”去苛求“新文体的小说”。
我不禁想起一段经历。数年前正集中力量作《白居易〈长恨歌〉研究》,苦于争论之烈,分歧之巨,我到了陕西周至县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仙游寺。仙游寺处终南山麓,黑水之畔,碧波清澈,幽竹环绕,但我当时只想寻得些许材料与白居易创作的心情动机,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弥合学术界巨大分歧的新方案,因而全无心于此,大好河山形同虚设。后来小著完成,蒙胡明先生赐序,序文有曰:“站在仙游寺外俯瞰仙游寺原址的低矮山包,黑水委婉,波光粼粼。终南山迤逦横绝,白云青霭,秋光浩荡;中峰众壑间,红树点点,林表淡出,颇有点缥缈的感觉。八百里秦川太阳下无边亮丽。”(第345页)寥寥数笔勾画出三秦故地胜景,令我大为惊异,也可为胡先生深厚文学修养的旁证。序文中还有一段:“听仙游寺的僧人说,从长安来仙游寺,有一条骑马行的山间便道,这就是著名的‘终南捷径’了。当年白居易往来长安、周至间,走的便是那条‘终南捷径’。”(第345页)以前读教科书,所谓“终南捷径”只说明谋求功名官职的引申义,序文信笔所至,或寻出原始意义。《迟到集》序中说:“所谓‘随笔’,大抵又如汪士慎说的‘胸中原有烟云气,挥洒全无八法工’——与书法绘画一样,随心用笔,自出机杼。”这种用笔的灵活,目的在于追求“自出机杼”——新的发现,别出心裁的创见,也包括独特的阐释方式。
整体而言,胡明先生更多以宏观的考察和深度的思想见长,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寻求“思想的价值”,“即理性思辨上或价值判断上有些长处,可以启发人的思考,有补于我们生存着的时代思维结构的前行,有补于我们生存着的时代价值观念和判断力的进步”,“在龙蛇郁盘、元气淋漓的审美外壳下散布出一种骨立嶙峋、思想挺拔的气象,传播一种健康的文化心理,力图代表前进的思想界的言论姿态”。(《迟到集·序》)这是他的学术宗旨、治学追求,也反映了他的主要特点及风格——当然也是这部《迟到集》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 胡明.胡适传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