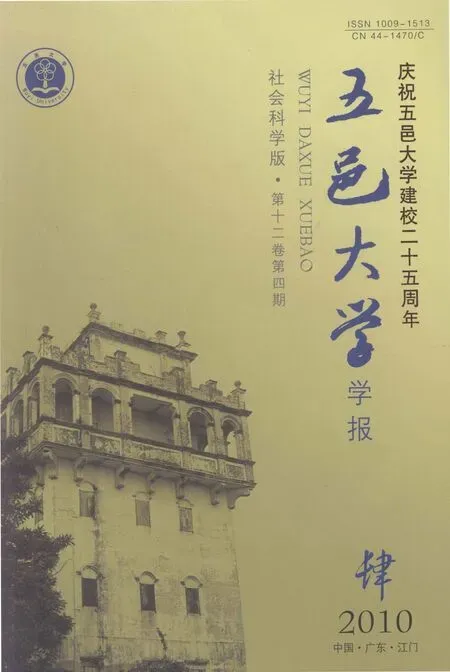从内在理路谈明清至“五四”的“文化下移”
闫 宁,苏 科
(1.昆明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云南 昆明 250100; 2.山东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从内在理路谈明清至“五四”的“文化下移”
闫 宁1,苏 科2
(1.昆明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云南 昆明 250100; 2.山东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0世纪80年代,海外学者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明清至“五四”才被看作一个联系的文化整体。以内在理路考察明清至“五四”的文化发展,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重心由雅文学向俗文学下移,其背后的根本推动力不在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是在激烈社会文化震荡中中国知识分子自身言说的需要。
内在理路;文化下移;文化焦虑;俗文化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雅、俗文学之别,这是封建等级观念在文化领域的反映。雅文学代表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取向,以文言为语言形式,以诗文为主要载体。俗文学源于民间生活,是对下层民众普通生活和情感思想的反映,以白话为语言形式,以民歌、小说为主要文体。明清之后,俗文学逐渐发达兴盛起来,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彻底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明清至“五四”的文学发展预示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开始,那么,明清至“五四”发生的文化下移趋势的内在动因如何?这种文化下移趋势为何在五四时期才显现出实绩?这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以白话代替文言的白话文运动是实现中国文学向现代化迈进的第一步,也是“五四”新文学先驱们喊出的第一个口号。1917年1月1日发行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这片文章中提出了“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他在文章中指出白话胜于文言的两大优势:第一,白话较之文言具有较强的普及性和流传性,“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第二,白话文能够充分表达真思想和真感情,不像文言文“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而应该“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即是功夫”。正因为白话在文学表达上具有压倒文言的绝对优势,胡适大胆宣称:白话文当“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同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实现中国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城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是对胡适“八不主义”的回应,在反向的意义对照中明确指出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总体发展方向。胡适、陈独秀的文化主张共同表明“五四”新文化建设对俗文学的倚重和对雅文化的背离,文化建设的重心由社会的精英层向民间下移。
提到“五四”新文化人对俗文学的重视以及20世纪初新文学建设中俗文学的备受推崇、繁荣发展,大多数人就会从知识分子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或无产阶级成为历史主人公、应该创造为他们服务的文化等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寻找缘由。事实上,“五四”新文化倡导者重视、发展俗文学有启蒙大众和服务社会的考虑,但若将二者视为其决定因素,笔者却不能苟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在事物的发展中起辅助作用,而内因才是最终影响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那种“社会政治外援决定论”显然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精神,是建国以来文化研究中极“左”思维惯性的遗留。余英时在梳理清代学术脉络时提出“内在理路”的文化研究思路,这是唯物主义“内因决定论”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灵活运用。他认为:“思想史本是看做有生命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1]因为在同样的经济繁荣程度、政治压迫环境和社会生活背景下,不同的思想史、文化史会发生不同的反应,选择不同的发展路线,一种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应该从文化内部挖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化启蒙为缘起的新文化建设,倡导者立意通过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种文化创作符号的根本转变,实现民主思想和现代文化在大众中的传播和普及。文化的形式和表达从精英向平民移位,建设的目标也由精英向平民下移,而这种文化建设的平民意识和平等态度,在很大程度显现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针对这种由于文化下移所带给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895年:“恐怕整个‘五四’的新文学脉络要重新整理,不能够相信任何人的话,包括胡适的话。我想提出这么几点:第一,绝对不能认为新文学是从‘五四’开始的,一定要从晚清开始。”[2]王德威则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3]
在探求中国新文学的起源上,李欧梵主张文化研究的整体观,反对任何将某段文化史从整体中抽取出来进行孤立研究的做法,而应该在文化史的整体梳理中探询一种文化现象或思潮产生的源头和起点,这与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思路不谋而合。随着中国内地思想解放的深入,大陆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从政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来治文化史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尊重文学本体的前提下,他们将“五四”新文化置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整体中重新探讨其现代性根源,发现中国文学对俗文化的提倡并非自“五四”始,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出现文人对俗文化的艺术加工和对白话文的倡导。
二
建国初的几十年里,文化界一直将明清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割裂开来,片面强调两者社会属性的不同,而未注意到两者在“文化下移”趋势上的潜在贯通。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的行动主体,处于文化发展的最前沿,能够最先敏锐地感知文化衰败的信号,他们面对文化困境所作的思考和选择最终决定中国文化未来要走的路。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和《误读之图》中提出,伟大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着要摆脱前代诗人的影响、到达自己诗歌创造新境地的内在文化焦虑,这被称作“影响的焦虑”。也就是说,当某种文化极度发达后,其文化机制内的知识分子内心就会产生摆脱前人文化影响的焦虑,推动文化主体不断思考、不断选择,开拓出文化发展的新历程,推动文化延绵不断地前进和完善。[4]
从封建士大夫家庭走出的鲁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对“影响的焦虑”体验最深切的一位。他常常剖开心灵深处,直视传统士大夫文化带给自己思想和文化创造上的双重文化焦虑。当有人以他为例,说明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道理时,鲁迅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并进一步谈及古书对自己创作和心灵的影响:“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很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5]“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都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识大家,虽然他们没有像鲁迅一样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文化焦虑进行有意识的反思,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却是他们无可摆脱的共同心理体验。
“五四”白话文运动中,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正是这种共同心理体验的外在行动表现。他们的言论不约而同地倡导“说自己的话”、“作自己的文章”。胡适后来直接将“八不主义”概括为:“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6]鲁迅在谈及五四文学革命的目标时,将其总结为“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7];钱玄同则直接向年轻一代号召:“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8]“五四”文化人对文言文的大举讨伐、对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刨祖挖坟最终取得成功,并非只是“五四”文化人内心焦虑能量的作用,而是明清以来知识分子文化焦虑郁积的总爆发,是历代文化主体心理机制中心理焦虑不断积累、瓜熟蒂落的最终结果。
文化焦虑是促使知识分子展开文化行动、推动文化向新阶段迈进的内在动力。它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公共文化情绪,是知识分子对文化衰败迹象的心理机制反映。它从产生直至成长为共同的文化价值驱动力,需要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文人在文化探索道路上的共同情绪积累和情绪传导。中国文化史上,文言作为一种为文工具已经存在发展了几千年,经过唐诗宋词的极度灿烂后,明清时代的文人越来越感受到文言对创造者思想和情感自由表达的束缚。在封建社会,文言作为书面用语是儒家文化的承载体,被文化特权阶层所垄断,平民布衣无缘亦无权使用文言。“经”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文言为文讲究引经据典、皓首穷经,讲求无一字不无出处,这种毫无创新的为文规则严重束缚了文学思想和真挚情感的自由表达和抒写。张载《张子语录》中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是中国文人自觉的文化使命和追求。一部分文人仕子感知到以文言代表的士大夫文化的衰落,纷纷各尽其智,采取行动企图挽救或扭转文言文化的衰败趋势。明代以来诗文流派纷呈,“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等先后涌现,都试图在“拟古”、“仿古”的文学复古运动中振兴文人诗文,不过最终都回天乏力。
而另一部分文人却选择了一条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晚明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市民阶层的产生和日益壮大,促使符合市民审美、表现市民生活的俗文学繁荣发展,文学的功能开始由“载道”与“言志”向“娱乐”与“说教”过渡。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代表士大夫情趣的雅文学和反映市民心态的俗文学,本是壁垒分明、不相交融。自晚明以来,文学的个性化表达日趋强烈,与文言的官方体制化发生龌龊,部分文人为了自由表达真我性情,开始关注俗文学的价值。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之路,主张文学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看到了俗文学的文学价值,大力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袁宏道指出文言表达的局限性并质疑文言文:“今之诗文不传久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夫人孺子所谓《辟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是可喜也。”(《锦帆集·小修诗序》)晚明的冯梦龙是一名积极倡导俗文化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他搜集民歌、笑话,编撰白话小说,是俗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极力推崇民歌对个人思想情感真挚、自由的表达,把桂枝儿、山歌看作天地间之至文,看作国风遗响。他说:“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明清民歌时调集·叙山歌》)这些于文学复古思潮肆虐年代产生的对文言的质疑,是一些文人感应到文言诗文的衰落后其心理机制中潜在的“影响的焦虑”对现实文化的最初回应。在晚明文坛,这种发展俗文学的声音和动力还处于发蒙状态,只存在于少数文人的意识中,其影响力也只限于文学。
三
文化和文学终究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如果一种文化形态臻于成熟,一定会和现实社会发生互动;而如果文化或文学所存身的社会不具备促其发展外在的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形态亦不可能仅凭自身的发展动力驱向成熟。明清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延缓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文言所标榜的雍容持重的审美意向符合整个帝国“天朝上国”的文化定位以及缓慢的生活节奏和封闭的文化环境。鸦片战争之前,文人仕子为通俗文学的发展辛勤耕耘,《聊斋志异》、《红楼梦》、“四大谴责小说”等文学经典先后出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但白话却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代替文言的绝对话语权。鸦片战争爆发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碎,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国门大开,被迫走向世界,中国文化亦走出封闭的环境,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开始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近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弥漫着浓重的文化焦虑情绪。这种文化焦虑不仅是指“影响的焦虑”——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倍感封建旧文化的腐败、落后,要求摆脱旧文化的束缚,寻找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还包括“言说的焦虑”。
这种“言说的焦虑”对外表现为被西方文化霸权定义的焦虑。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拥有者,鸦片战争后,中国以半殖民地的身份走入世界文化之林,文化的话语权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剥夺,成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强权下的“他者”。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是“一个自指涉的系统,它制造了一个西方之东方,这个东方是具有某种怪异性的、一成不变的、低劣的、被动的文化他者,它的意义是解释西方或认同西方”[9]。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中国的世界文化形象是一个被西方文化霸权恶意歪曲了的劣等民族脸谱。
“言说的焦虑”对内则表现为新的文化语境下自我表述的焦虑。西方武力的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一切使得士大夫文化为代表的文学在话语涵括纬度和文体审美取向上,无法适应中国人逐渐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和内心情感。特别是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山河碎的外敌入侵局面,无法再用极度雍容华贵的雅士情调附庸风雅、点缀太平,他们急需一种简洁、明快的语言工具发泄“护国保种”的文化焦虑情绪。
世纪末的文化焦虑情绪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共同价值的认知凝聚在一点:在中西文化的对流中,大力发展中国俗文化。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船坚炮利”方案的提出,从改良派的“托故改制”与顽固派的“中体西用”到“五四”文化先驱的“科学、民主”与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近代知识分子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来探讨醒世救民、富国强民的现代途径。他们在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认识到,单纯地依靠西方的技术和思想来振兴中国是行不通的,一个民族要伫立于世界文化之林需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一个民族要想被世界接纳,就必须具有自己的文化行囊”[10],一味模仿西方,否定自我只会让中华民族沦为文化乞丐,又有何资格与世界文化接轨?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封建正统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前者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早已和它所附属的社会走向衰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映衬下更是处处显现出遮掩不住的“垂死之相”;而俗文化自晚明之后,经过几代文人的努力扶植和培养,在近代中国文化画卷中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中国整体文化结构中,俗文化处于最基层、最根本的部分,它具有最普泛的代表性和最本质的民族性。19世纪末,知识分子在文化焦虑情绪的内外交困中,寻找一种既能凸显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又能适应中国人当下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交流的新表达方式,无疑,以白话为主的俗文化是他们最佳的选择。
[1]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1993:470.
[2]栾梅健.纯与俗的变奏[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45.
[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4]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15.
[5]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85.
[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8,4(4).
[7]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5.
[8]钱玄同.随感录[J].新青年,1918,5(1).
[9]朱水涌.叙事与对话——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10]杨国.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
[责任编辑 文 俊]
I206.6
:A
:1009-1513(2010)04-0071-04
2010-06-08
闫 宁(1980—),女,山东烟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