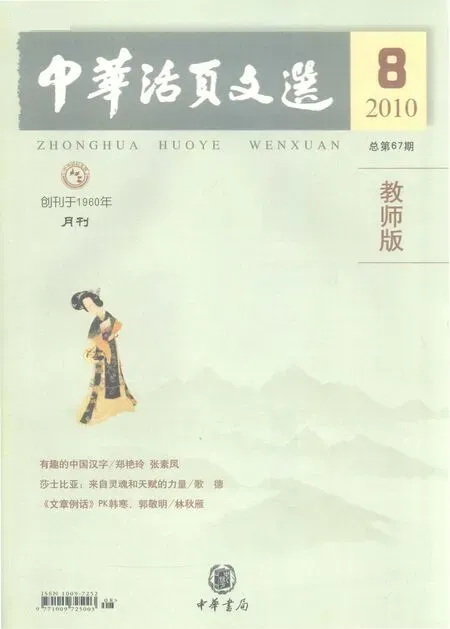一缕春风拂过三尺讲台……
黄志雄(广东省英德市一中)
一缕春风拂过三尺讲台……
黄志雄(广东省英德市一中)
又到了高考填报志愿之际,不少学生会问我做老师好不好,问我为什么要做老师。每当为学生解答完,我自己亦久久不能平静,其实有些事情我没跟学生讲,今天让我成为一名老师的“宿命”,或许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因”。
那还是在20个世纪80年代初期,所有的学校都差不多,设备简陋,“三尺讲台”只会少于“三尺”不会有多,讲台其实就是一张小木桌,上面也只摆放有一块破布作粉笔擦,没有粉笔,因为一盒粉笔值一块多钱呢,彩色的更贵,当时稀罕得很,粉笔都放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呢。父亲是一所小学的老师,那时的我经常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不少只剩一丁点的粉笔头——我曾经瞒着父亲拿了一支新的,发现后被揍了一顿,从此不敢再拿——但一小截的粉笔足以让我成为小伙伴中最“富有”的一个了,那一小截的粉笔也为我换得了不少小伙伴手中的一片番薯干或是一只比较能斗的蟋蟀,彩色的能换得更多。
我刚上小学那会儿,教室里的黑板是用木板刷上黑漆,用两根棍子架起来靠在墙上的,用得久了,板子上到处是坑坑洼洼,剥离的漆成了一个个小白点。有一次考试,老师把数学题目抄在黑板上,我误把“1”看成了“10”,结果做错了,一道题好多分呢,委屈得我当时大哭。
过了好几年,学校的讲台换了,类似大的书桌,粉笔擦也是特别制成的,因为那时候黑板已改成水泥的墙壁黑板。我再也不用担心把“1”看成“10”了,不过新的烦恼又来了,那时候粉笔已经不那么珍贵得连粉笔头都不能丢,这就成了好些老师的“武器”,不知怎么地,他们就练就了一手出神入化的指上功夫,谁要是上课走神,老师那么轻轻一弹,不偏不倚,保准正中走神的人的额头,他还能不耽误讲课,走神的人也立刻回过神来继续听课。我曾经无数次在想着超人和机器猫的时候饱尝这种“流星丸”的滋味。让我纳闷的是,为什么老师准确地“一击即中”时,都是在超人快打败坏人的紧要关头,这令我懊恼过无数次。但爱幻想是小孩子的天性,即使是在课堂,即使无数次地“中招”,仍然乐此不疲。
渐渐地走过了疯玩、爱幻想的童年,在初中的某一年夏天,我们的课室换上了新的讲台,除了伴我走过童年的粉笔和粉笔擦,它还摆放了很大的圆规、三角尺、地球仪等。不过我们那时看上去挺和蔼的数学老师,好像不太用圆规,遇到要画圆的,他拿起粉笔,在新装的磨砂玻璃黑板上先磨两下,然后再找块干净的地儿,手腕一转,一个漂亮的圆出现了,画完他自己会露出一副满意的神情,看我们一眼,继续讲课。我们曾在课后特意跑去量过那圆,跟圆规画的还真差不了多少,莫名地我就越来越喜欢上他的课了。我们也常学他在黑板上画圆,或是列出某道题的解题过程,进行讨论。偶尔还会有一些对话或涂鸦,互相开个玩笑,当然在老师上课之前,这些幼稚的对话或涂鸦都会成为“粉笔灰”。
讲台最令我惊奇的变化是在高中的时候,当老师打开幻灯机,白色的屏幕缓缓降下的时候,我们这帮平时不安静的毛头小伙竟然个个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那份好奇现在想起都激动。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胖得非常可爱的语文老师最喜欢用幻灯机给我们上课了,有一次她正眉飞色舞地讲着一篇课文,我用手支着下巴看着大屏幕,她换了一张幻灯片,我忽然想笑,憋住了,全身一哆嗦,不知是因为角度问题,还是老师写的字确实有点揉在了一块,我楞是把“令人向往的白银子”看成了“令人向往的白娘子”,正纳闷着呢,语文老师一脸无辜地问我:“哪儿讲得不对吗?”……
后来到了高三,已经是进入了21世纪,在这个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时代,发生任何事情可以不用再去大惊小怪了。我们平时只在家里用的电视,学校把它搬进了课室,我们有些课程就是通过它来完成的,老师在一个视频室里讲课,有需要的班级打开电视就可以听课了。不过习惯了在教室的老师,在视频镜头中好像还些不太适应,他会习惯地问一句:是不是啊?总会有同学抢着回答,其他同学就笑了起来,电视中的老师也意识到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家就更乐了。这种时空相隔制造的欢乐笑声,在紧张单调的高三生活,总算让我们轻松快乐了不少。
再后来,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成了英德市一中的一名语文老师。在大学里学到的多媒体教学,我已经可以非常娴熟地操作了。形象生动的演示,美不胜收的图片,悦耳动听的配乐,一节课已经可以生动得让你仿佛置身电影院。
讲台下学生在打闹着,讨论着,小声地说笑着,一如当年的我;那一张张青春的笑脸,慢慢地,慢慢地模糊了。我又看到了那粉笔头换番薯干的童年……
一缕风,轻轻地,拂过了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