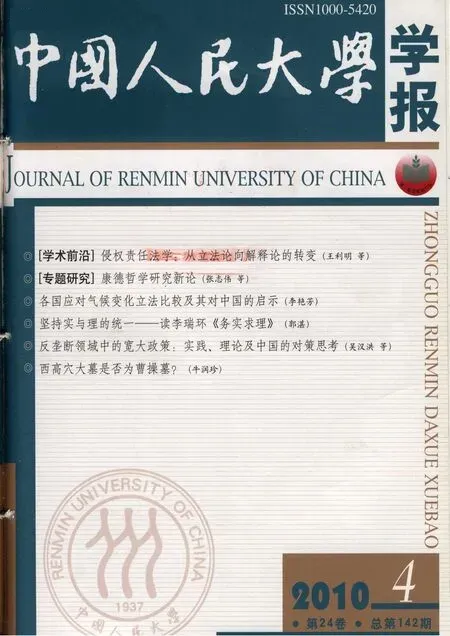正统理学的终结者:阳明心学发微
宋志明
青年时代的王阳明笃信朱子理学,格竹子事件以后,他转向了陆九渊心学。不过,他并非师承陆九渊,而是自悟所得。正德元年(1506 年),他受到刘瑾的迫害,被贬到偏远的贵州龙场作驿丞,堕入人生的低谷。可是,他竟然在逆境中有了学问上的大收获,这就是龙场悟道。《王阳明全集·年谱》记载了他悟道的情形:“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亿说》。”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开始构建心学体系,并创办龙冈书院,讲学授徒。他曾在文明书院等多所书院讲学,晚年又创办稽山书院,从学弟子众多,不乏杰出者,如徐爱、邹守益、钱德洪、王畿、王艮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是王艮,他在下层民众中间传播王阳明心学,创立了王门中最有特色的一个分支——泰州学派。后世学者把陆学和王学合称为“陆王心学”,其实,集大成者当数王阳明。在王学问世以前,陆学处在边缘,并不能与程朱理学抗衡;王学问世以后,陆王心学才取得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地位。
准确地说,王阳明既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整个正统理学的终结者。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属于正统理学的范围。他们的共同理论诉求,乃是把儒学从政治哲学讲到人生哲学。可是,大多数理学家仍旧抱有较强的政治哲学情结,努力为三纲作论证;直到王学的问世,才在人生哲学方面把正统理学讲到位。王阳明的政治哲学情结不像其他理学家那么强,他很少提及三纲。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全集》卷四)“破山中贼”属于政治哲学话语,“破心中贼”则属于人生哲学话语,他显然把理论重心放在了后者,而不是前者。程朱理学把儒家世界观讲到位了,讲出了明明白白做人的道理,可是没有把儒家人生观讲到位。程朱理学得到历代皇帝的扶植,通过科举取士的途径得以推广,变成了一种官方哲学。用官方哲学话语不可能把儒家人生观讲透彻。鉴于这种情形,王阳明只能选择心学的理路,选择民间哲学的理路。同程朱理学相比,王学带有较强的草根性,没有成为科举取士的文本依据,没有皇权可以傍依,因而只能靠自身的理论魅力得以传世。正因为出现了王学,才会有“宋明理学”的称谓,否则只能称为“宋理学”了。在最著名的理学家当中,除了王阳明之外,其余都是宋代人。本文从“正统理学终结者”的视角,对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重新加以梳理,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良知本体论
在本体论方面,王阳明接着陆九渊的心学学脉讲,也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基本思想大体相似。不过,他并不照着陆九渊的讲法讲,而是找到了一种新的讲法。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以《孟子》为主要文本依据,但选择的核心理念有所不同。陆九渊选择的是“本心”,王阳明选择的是“良知”。为了突出王学的学术特色,本文把王阳明的本体论学说称为良知本体论。
在西方哲学中,“本体”是解释存在的哲学范畴,指世界赖以存在的最终实体,指世界存在不可再追溯的终极依据。在中国哲学中,“本体”观念具有两重意思:既是存在的终极依据,又是价值的终极依据。中国哲学所说的本体,没有“实体”的意思,主要是指本然状态或本真状态。陆九渊突破了朱熹以存在论为主的本体论理路,转到以价值论为主的理路,但并没有做到位,仍旧保留着脱胎于存在论的痕迹,甚至把价值论和存在论混为一谈。例如,他的“宇宙即是吾心”的说法,既可以理解为价值论的命题,也可以理解为存在论的命题。他的“本心”观念,是从“天理”观念中嬗变出来的,没有明确的价值规定性。到了王阳明这里,才清除掉存在论的痕迹,把价值本体论讲到位了。王阳明拒绝从存在论的视角探询本体,只从价值论的视角探询本体。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王阳明并不否认宇宙万物的客观实在性。《传习录》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有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有些研究者根据这段材料给王阳明带上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论”的帽子,并不合适。王阳明在这里讲的,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存在论话题,而是关于人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的价值论话题。按照王阳明的这种说法,倘若没有人,世界本身当然存在,不过,无人存在的世界处在“寂”的状态。“寂”并非意味不存在,只意味着对于人来说没有意义。无人的世界既然对于人来说没有意义,就不必当作哲学话题,完全可以悬置起来,存而不论。无人观看的花,当然存在,但此花没有审美价值;只有被人观看的花,才“一时明白起来”,被人赋予审美价值。当人没有看到花的时候,花在人的意义世界之外,处于“寂”的状态,而不是“无”的状态。他并没有否认花的存在,只是说此花对于人没有意义。有些论者常常把王阳明的花树之喻等同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实则拟于不伦。贝克莱按照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强调主体的先在性,用主体规定客体,讲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心主义经验论;王阳明按照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强调内在性原则,讲的是价值意义上的本体论。王阳明把无人的、无价值的世界搁置起来,只关注有人的、有价值的世界。他认为,在人天一体的、有价值的世界中,人是有能动性的、有灵明的主体,用他的话说,人就是“天地的心”。《传习录》下记载了这样一段他与弟子的对话: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之心?”
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
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塞天地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
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的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在这里,王阳明对“天地鬼神”做了价值化的解释:天的“高”、地的“深”、鬼神的“灵”,其实都是人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并不是事实判断。在他看来,有价值的世界是人的精神创造,倘若离开了人的精神(灵明),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传习录》下)他把人和宇宙看成一个整体,而把人心看成这一整体的“发窍之最精处”。王阳明十分重视主体性原则,但有别于贝克莱所说的那种认知意义上的经验主体,而是价值意义上的评判主体。
王阳明沿着“整体——主体——本体”的本体论理路,第一步是把人与宇宙万物看做价值意义上的整体,第二步是把这一整体归结为价值评判的主体——人,第三步则从对人的考量中提升出价值本体——良知。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所同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在孟子哲学中,良知指先验的道德观念;而在王阳明哲学中,则是本体论范畴。良知的本体论意涵如下:
第一,良知为心的本体。王阳明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并且为“人人所同具者也”(《答陆原静书》)。他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传习录》中)对于任何人来说,人既是一种肉体(身)的存在,又是一种精神(心)的存在。在这两种意义的存在中,心为主宰者,身从属于心,心为体,身为用。那么,心又以何为体呢?心必须以良知为体。良知是对每个人所具之心的超越,具有不可追溯的终极意义,故只有良知才可以称为本体。良知是一切价值的源头,具有普适性,每个人都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良知自觉的体现者。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由于受到物欲的牵扯,往往造成对于良知的遮蔽。每个人可以通过心性修养的途径,使良知呈现出来,从而实现人的价值。
第二,良知把人同宇宙万物整合为一体。在具有价值意义的天人统一体中,天地万物不再被王阳明视为自然之物,而视为体现良知的价值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是造化之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下)在他看来,良知不仅为人所本有,也为一切无情之物所本有。“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同上)按照王阳明的看法,天地万物皆在“良知”所及的范围之内,是“良知”的“发用流行”,这就叫做即体即用,体用一源。王阳明用这种说法,为儒家追求的“天人物我一体”的境界提供理论支撑。王阳明的良知说与天台宗湛然的“无情有性”说、禅宗的“心生万法”说、华严宗的“理事无碍”说意思相近,但突显了儒家的特色。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学说的特色,在于突出的是一个“良”字。“良”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良”而言,用以表示儒者应当追求的、合理想的价值目标。由此来看,良知本体论可以称为价值本体论。我们不能将其归结为西方哲学中那种唯我论。在西方哲学中,唯我论是一种关于存在和知识的本体论学说,即试图从主体中演绎出宇宙,从认知主体中演绎出认识对象。王阳明没有采取这样的思路,他无意从主体中演绎出宇宙万物,也无意从主体中演绎出认识对象,只是把客体的价值性归结于价值主体。在价值评判中,强调主体的重要性,乃是一种无可厚非的选择。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倘若离开了价值判断的主体,价值何从谈起?因此,只能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寻找价值判断的终极依据,不可能完全诉诸客体。“驴子宁要稻草,不要黄金。”驴子只需要稻草,不需要黄金。黄金对于人类有价值,而对于驴子却无价值。王阳明建构良知本体论,选择的正是从主体方面寻找人生价值的终极依据的思路。他并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认知主体上,而是超越了认知主体,找到了普适性的价值共识——良知。良知不是“小我”之知,而是“大我”之知。在王阳明看来,认知主体不仅不是本体,反而会遮蔽本体,只有超越了认知主体的良知,才可以称为本体。在这里,他表达了同以往儒家相一致的价值诉求:群体高于个体。
王阳明把儒学的价值本体论讲到了高峰,最终建构起牟宗三所说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按照他的本体论学说,良知就是一切正确的价值判断的终极依据,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对于任何人来说,凡是出于良知的行为,都是有价值的正确行为;凡是违背良知的行为,都是无价值的错误行为。他指出,做人的根本就在于“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祛除私欲的蒙蔽,恢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本然状态。因此,人的自我完善并不靠外在天理的他律,而应当靠内在良知的自律。
程朱从超越性的维度为儒家伦理寻找到“天理”这一本体论根据,王阳明则从内在性的维度,把天理落实到人心之中。他说:“良知即是天理”(《答欧阳崇一》),“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如孝、弟、忠等都是“天理”的“发见”(《答聂文蔚二》)。同时,他认为“良知”也是人固有的至善的“天地之性”。王阳明说:“至善者,心之本体也”(《传习录》下),“天命之性,纯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大学问》)。这种说法与朱熹的说法有所不同。朱熹主张“性即理”,即人性得之于外在的“天理”,仁义礼智等道德理念先天固有,人得之“天”而具于“心”,强调道德理念的先天性。王阳明则认为“天命之性”就是“吾心良知”,把人的“心”看成道德的终极根据,“理”不过是“心之条理”,强调道德理念的内在性。王阳明开出的这条思路,被其后学大加发挥,现代新儒学大讲特讲所谓“道德的形而上学”,仍旧沿袭着王阳明的思路。
二、知行合一论
陆九渊虽然实现了工夫论转向,但只讲到“知”的层面,未论及“行”的层面,没有提出系统的知行关系学说。王阳明比陆九渊迈进了一步,依据良知本体论提出了有特色的知行合一论。
知行关系问题是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在王阳明之前,二程提出知先行后说,朱熹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知轻行重说和知行相须说。王阳明站在心学的学术立场上,不认同程朱理学的本体论学说,也不认同程朱理学的知行关系学说。针对程朱理学的知行关系学说,他认为知行关系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轻重关系,而是“合一”关系。所谓知行合一,就是说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
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论,吸收了朱熹知行相须说的理论思维成果,但比知行相须说在学理上更为自洽。在他看来,尽管朱熹拉近了知与行之间的距离,仍旧把知行“分作两件”,仍旧存在着“析心与理为二”、“外心以求理”的问题。王阳明指出,如果把天理设置在心外,人永远不可能认知它,所以必须把它设置在人心之内。认识内心之中的天理,只有选择“求理于吾心”的路线,把知行内在地统一起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首先是一种关于如何建构哲学本体的学说。他所触及的深刻道理是:人们永远不能通过对象化认识的途径,得到关于世界总体的哲学本体论理念;人只能通过认识自身的途径,逐渐深化对于世界总体的认识。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论是有针对性的,故而自称为“补偏救弊之言”。他批评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今人却就将知行作两件事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却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传习录》上)在明代,程朱理学已经成为许多读书人猎取功名的工具,他们读圣贤的书,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并不想落实到行为实践中。王阳明试图扭转这种功利化的风气,故而强调知行合一。元代以后,程朱理学就开始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到王阳明时代,程朱理学进一步地官方化,变成读书人踏上仕途的敲门砖。真诚的儒者,已经不能在官方化、工具化的程朱理学中获得精神满足了。王阳明对儒学的这种现状感到担忧,故而大力倡导知行合一。他呼吁读书人做一个真诚的儒者,不要把儒学当成“为人之学”,而要当成“为己之学”,当成安身立命之地。他把知行合一论称为自己的“立言宗旨”,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对其做了充分的阐释。
第一,“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论,固然有针对时人把知行“分作两截”之弊而发的,但主要还是从学理上说的。他认为,仅从学理上看,知行就构成合一的关系。他说:“某今说个知行合—,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答友人》)为了论证“知行合一”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首先对“行”做了与通常意义不同的界定,强调“一念之发动处便是行”(《传习录下》)。他以“好好色”、“恶恶臭”为例子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所以,“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同上)。他强调,知行是同时发生的,在逻辑上不能分出先后来,“知”外无“行”,“行”外亦无“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在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答顾东桥书》)从体用的角度说,“知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行为“发用流行”。知行皆以良知为本体:知就是对于良知的自觉,行就是把这种自觉贯彻到生活实践中。
第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王阳明哲学中,知行都是动态的范畴,二者合一并进,没有先后之分。他强调,知行互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的这种看法,比朱熹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知与行的统一性,在儒家思想的范围内化解了先验论和经验论的紧张。他不再抽象地追问关于道德价值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只强调这种知识在实践层面的必要性、指导性和有效性。他也不再区分广义的知和狭义的知。在他的知行学说中,“知”通常是广义的,既指“天德良知”,也指“闻见之知”;“行”通常也是广义的,既指存心养性,也指经世致用。
他在《传习录》上写道:“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故,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人们在“行”之前,肯定已选择了计划、方案,故说“知是行的主意”;而“知”只有通过“行”才得以体现,故说“行是知的工夫”;当有了计划、方案时,“行”就已经开始,故“知是行之始”;而一旦把计划、方案付诸实行,就是“知”的完成,故“行是知之成”。以饮食为例,“夫人必有饮食之心,然后知食。饮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以走路为例,“必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其结论是:“则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同上)不过,他说“知已有行在”,“行已有知在”,存在着把知行混为一谈的问题。
第三,“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王阳明指出,从学理上讲,知行应该是合一,可是在事实上,人们并不能都贯彻知行合一的原则。例如,“今人尽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由于私欲作怪,致使知行分离。所以,王阳明说:“夫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传习录》上)他把知行合一论同“诚意”、“正心”、“去欲”等修身工夫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求人们在“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传习录》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行合一同朱熹说的“存理去欲”是一致的,都要求每个人不断克服影响良知呈现的私意妄念,树立起对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坚定信念。
总的来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贯彻了一条由心到物、由知到行的认识路线,不过,其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
其一,王阳明接触到了知行之间的统一性问题。王阳明已认识到,知离不开行。他指出,“不行不足谓之知”,行比知更为重要,没有行就没有真正的知。只有“行之明觉精察处”,“知”才能达到深入的程度。他也认识到行离不开知,需接受知的指导。如果离开“知”的指导,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那就是盲目的“冥行妄作”(《传习录》上)。只有“知之真切笃实处”,行才算名副其实。王阳明对知行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关系的揭示还是比较深刻的。王阳明还看到了在由知到行、由行到知的转化中,有一个亦知亦行、非知非行的过渡环节,这也是一种具有辩证法因素的见解。
其二,王阳明反对分“知行为二”,其中包含着倡导言行一致、反对知而不行的合理因素。王阳明认为“行即学”,强调“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传习录》中),“若离了事物为学,都是著空”(《传习录》下)。由此来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既有先验论的倾向,也有经验论的倾向,然而理论重心还是放在行这一方面。他在儒家思想的范围内化解了先验论和经验论之间的紧张。他十分看重行,主张“在事上磨炼”。王阳明对“行”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朱熹。朱熹基本上是一个学问家,虽做过几年地方官,但政绩平平;王阳明不但是一位学问家,而且是一位经邦治国的干才。
其三,王阳明把良知看成真理的标准,认定“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传习录》下)。这种“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态度,比较充分地伸张了儒家理性主义精神,甚至流露出对权威主义的轻慢,委婉地表达了摆脱程朱理学的教条束缚的合理要求。在这种说法中包含着思想解放的诉求。
知行合一说在强调知行统一性的同时,却对二者之间的差别性有所忽略。王阳明的“一念发动处便是行”的说法,显然不够妥当,确有混淆知行界限之嫌。此外,王阳明所说的“知”,主要还是指关于道德价值的认识,“行”也主要指道德的践履,二者都不是单纯的认识论范畴,而是认识论与本体论、价值论合一的范畴。关于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行关系问题,王阳明并没有展开论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于王门后学具有双重的影响。有些人发挥重行的一面,把知行合一理解为力行哲学,如黄宗羲等人;也有些人发挥重知的一面,只在心性上做文章,沉溺于空疏之学,如王畿等人。
三、致良知之教
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乃是王阳明哲学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他的理论诉求是“即本体即工夫”,把本体和工夫看做一档子事,强调二者不可分。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在他倡导的致良知之教中。王阳明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良知”说的是本体,致良知说的就是工夫,二者加在一起构成人生的全过程。致良知之教就是王阳明对儒家人生观的系统阐述。
王阳明指出,致良知所选择的路线不是外求,而是内省。所谓致良知,就是树立良知本体论信念,牢牢地把握住“心之体”,站稳安身立命之地。王阳明的弟子把致良知之教的要点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这四句话被人们称为王门四句教。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心之体”是道德价值判断的终极依据,同经验中的善恶判断不在一个层次,处在“未发之中”,“无前后内外,浑然一体”。对于“心之体”,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可以说是超善恶的,也可以说是至善的。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下)这就是说,作为心之体的良知,本身就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与经验中的善恶判断无关。第二句话讲到“已发”层面,才涉及经验中的善恶判断问题。人的行为体现良知为善,反之则为恶。第三句话侧重于“知”,强调良知为判断善恶的尺度。第四句话侧重于“行”,强调良知必须落实到行为层面。
致良知不是一个知识论的话题,而是一个人生观的话题。致良知所说的“知”并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人生信念或是非观念。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在这里,他一连用了四个“只”字,已经明确地把“良知”和“知识”区别开来了。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也与朱熹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物”的意思就是“事”。他所说的物不是客观之物,也不是作为认识对象之物,而是指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他说:“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传习录》上)“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大学问》)举例来说,“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答顾东桥书》)王阳明指出,在意义的世界中,心是唯一的本体,物从属于心,理也从属于心。不仅“无心外之物”,而且“无心外之理”。“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答顾东桥书》)在他看来,心、物、理分而为三,合而为一,实则是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就是“事”。
第二,“格”的意思就是“正”。他不同意朱熹把“格”训为“至”,改训为“正”。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大学问》)“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传习录》中)。
第三,“致”的意思就是“推”。他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答顾东桥书》)所谓“致”,既是内省意义上的“知”,又是道德实践意义上的“行”。王阳明指出,人人皆有良知,但并不是人人实际上做到了“致”。
王阳明指出,致良知的过程不是一种知识的形成过程,而是心性修养的过程,同“穷天理”是同一个意思。王阳明从良知本体论出发,论证“存天理灭人欲”的必要性。与朱熹不同的是,王阳明认为天理不在心外,所以,“存天理”也就是“存心之理”:“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需外面添一分。”(《传习录》下)他也认为理欲不容并立,主张“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同上)。陆王学派与程朱学派的论证方式不同,但结论和目的都是一致的。正如清初思想史家黄百家所说,他们都以“扶持纲常名教”为职志。王阳明把致良知之教称为“拔本塞源”之论,自叹:“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传习录》上)他所说的致良知,就是以儒家的方式搭建精神世界、意义的世界或价值的世界,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地。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教,根本目的是解决如何把人造就为圣贤的问题。儒学既是一种政治哲学,也是一种人生哲学。不过,在王阳明之前,讲儒学的重点,显然被放在政治哲学方面,而不是放在人生哲学方面。自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教以后,讲儒学的重点则从政治哲学转到了人生哲学。王阳明修正了儒家的圣人观念,把儒家人生观讲到了高峰。关于圣人,孟子的说法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的说法是“途之人可以为禹舜”,都是把“圣人”同“王”联系在一起,不是指普通人。准确地说,他们眼中的圣人,其实就是“圣王”。儒者即便做不成“圣王”,至少也做个“圣官”。他们都有鼓励人们“到朝廷里去做官”的意向。诚然,孟子倡导“大丈夫”人格没有把普通人排除在外,但主要还是对文化精英讲的,也有浓重的政治哲学意味,并没有把儒家人生观讲到位。到王阳明这里,才把圣人讲到“人”的层面,把儒家的人生观讲透了。
在他的致良知之教中,圣人的观念已经泛化了,从狭小的庙堂扩展到广袤的民间,使平头百姓都有了成为圣人的可能。他切断了圣人与官位之间的联系,对圣人做了平民化的解释,甚至以为“满街都是圣人”,强调在成就圣人的可能性上,大家机会平等。按照王阳明的圣人理念,圣人就是自觉致良知的人,就是问心无愧的人,就是清清白白的人,就是有价值感、使命感、责任感的人,就是与万物同体的人。一个人能否成为这样的圣人,同他充当的社会角色没有必然联系。达官显贵可以成为圣人,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读书人可以成为圣人,不识字的劳动者也可以成为圣人,同样可以拥有圣人的尊严。朱熹是规范伦理学的倡导者,以天理的观念约束人,主张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王阳明是德性伦理学的倡导者,以良知的观念鼓励人,主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为了把圣人平民化,王阳明也切断了内圣与外王的联系,切断了德与才之间的联系。他把人的德性比作金子的成色,把才能比作金子的分量。认为做人如同炼金子:纯金讲究的是成色,而不是分量;做人讲究的是内圣,而不是外王。“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传习录》上)圣人的可贵之处,就体现在人的德行上,同才能的大小没有关系。这意味着,圣人未必就能成就外王,因为内圣只是成就外王的充分条件,并不是必要条件。能否成就外王,还需以应有的才干为必要条件。王阳明的这种看法并不是排斥才干,只是强调德比才更重要、更根本。在明代,研习朱学的读书人,大都抱有功利目的,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研习王学的人,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只是为了成就圣人。王阳明并不鼓励他的弟子到朝廷去做官,只是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修行,努力把自己造就成圣人。在他的从学弟子中,有相当多的人明确表示放弃科举考试。例如,王艮不仅自己不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希望自己的后代永远都不要选择科举之路。王学没有成为官学,没有被纳入科举的范围,没有得到官方的扶植,只以其理论魅力吸引受众。朱学的受众大概都是读书人,王学的受众更为广泛,不仅有读书人,也有不识字的人。他的从学弟子王畿说(王阳明)“以良知之说觉天下,天下靡然从之”(《重郭明明先维文录后语》),并非虚语。
在程朱理学日趋僵化的情况下,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并风靡一时,其积极理论意义,我们不可低估。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扬人的主体性。王阳明平生讲的“致良知”,旨在充分调动人主观精神的能动性,提高人自己把握自己、自己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内在潜能。他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的倾向,在把心与理、心与物合而为一的基础上,确立人在意义世界的中心位置。这种理论对“心”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予以充分的肯定。这对于长期处于精神枷锁束缚中的人来说,无疑会得到一种精神的慰藉。王阳明讲出了这样的道理:人要战胜环境,首先要战胜自己,充分调动人的主体精神和思维能力。王学之所以有这样的诉求,可能与明代已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关系。在明代,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重视人的价值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强调个性自觉的思想动向。王学可以说是这种潜在的思想动向在哲学上的折射。
第二,不迷信权威和经典。王阳明致力于打破官方化了的程朱理学的思想垄断,他在理学流行、圣人被神化的情况下,公然声称“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答罗整庵少宰书》),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他认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既不是那些权威,也不是“六经”典籍,而是自己心中的“良知”。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他不赞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迷信权威,也不迷信经典,倡导理性主义态度,客观上具有冲击旧权威、旧教条的积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王阳明虽然反对权威、反对教条,但他不反对“天理”,不反对儒家道德伦常,并且还自觉地为儒家道德伦常做哲学论证。
第三,强调道德自律和人性自觉。王阳明心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精神和道德自律的原则,赋予良知以“不假外求”的内在性,主张通过主体的自觉、自悟“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大学问》)。阳明心学简易直接,活泼开阔,故而能给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风气。
——围绕《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若干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