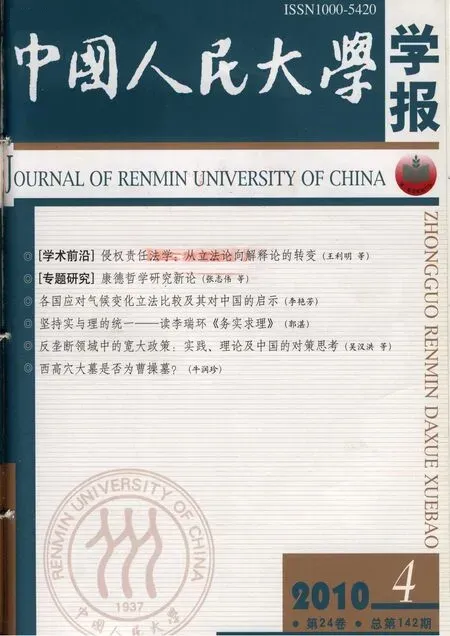论《纯粹理性批判》如何成为“基础形而上学”
黄裕生
(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100084)
一
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恰恰是为了把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来建立,而不是要放弃形而上学。
这里需要澄清,什么是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形而上学陷于毫无结果的长期论争,以致形而上学不得不一再走回头路?康德的回答是:“纯粹理性本身所不可避免的问题(Aufgabe )是上帝、自由和不朽。为解决(Aufloesung)这类问题所做的一切准备以及以解决这类问题为最终目的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它最初的方法程序(Verfahren)是独断式(dogmatisch)的,也即说,在没有对理性是否有能力承担起此伟大任务进行预先审察之前,就贸然行事。”(B7)
显然,在康德心目中,形而上学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构成形而上学最终目的的超越(transzendent )部分,这部分要对上帝、自由、不朽这类超越性事物作出思考和理解;另一部分是构成形而上学之准备性知识的超验(transzendental )部分,它将为确实可靠地思考超越性事物提供准备与前提。超越经验界限是形而上学的根本事务,它是人的理性之本性所在。
但是,形而上学却一直以独断的方法程序处理这一事务,这正是形而上学一直未能有所前进的根本原因。其独断方式就体现在它的方法程序(Verfahren)上:它在没有对理性本身是否有能力去认识经验之外的事物进行审察之前,就贸然去构造这类事物的知识体系。由于缺乏先行的批判考察,传统形而上学未能区分出理性本身的两种不同运用,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经验(理论)运用”与“实践运用”。
理性的这两种不同运用实质上就是理性的两种不同存在方式,或说是理性(人)的两种不同身份,这就是在理性经验运用中的“主体”角色与理性在实践运用中的“自由存在者”身份。理性的两种不同运用使人承担着不同角色,并开显出不同世界。
传统形而上学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混淆了这两种不同运用。这导致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结果:一个就是表面看似扩大了思辨理性或知性(Verstande )的认识领域,而实际上却缩小了理性的整个运用领域,因为它实际上以理性的理论运用排挤掉了理性的实践运用,从而取消了理性作为自在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但是,只有当理性自在地存在,它才是自由的,才是自由理性,也只是作为这种自由理性的存在者,人才是自由的,才保持为人。因此,当传统形而上学因混淆理性的两种运用而取消了理性的自在存在方式时,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失位的历史。形而上学误用理性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使形而上学在解决自己的基本问题时陷入了自相矛盾,从而影响了自己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二
形而上学的根本任务是超出经验之外,追问上帝(神)、自由和不朽这些根本问题。但是,如何超出经验之外?又如何去追问上帝、自由这些根本问题?显然不能通过把知性法则扩展到经验之外的领域来完成形而上学的任务。这种扩展使形而上学陷入的矛盾冲突表明,理性对知性法则的运用是有界限的,或者说,理性的经验运用是有界限的。因此,为了使形而上学摆脱长期陷入其中的那种自相矛盾,以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可靠的科学,必须首先澄清理性的经验运用的界限。而这也就是说,必须首先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考察。
因此,在康德这里,“纯粹理性批判”对理性所做的分析是形而上学本身的一项任务,它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准备性知识部分。也就是说,“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是要作为一门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任何形而上学,只要它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以“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为基础。
在康德心目中,“纯粹理性批判”是形而上学的“导论”(Prolegomena )。不过,我们并不能在著作的导论这种意义上去理解《纯粹理性批判》在形而上学中的导论地位。一本书的导论可以不是书的正文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在全书写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写。但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导论,“纯粹理性批判”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形而上学要作为科学出现必须首先完成的部分。所以,“纯粹理性批判”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准备性部分,但正是这个准备性部分保证了形而上学能够作为一门科学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准备性部分也就是它的基础部分。
所以,《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恰恰是为了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纯粹理性批判”当作“基础形而上学”,因为任何可能的形而上学都必须建立在这种理性批判之上。
三
如果我们的确可以把“纯粹理性批判”当作“基础形而上学”,那么,基础形而上学面临的任务首先就是回答“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因为“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就如“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和“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一样,它们的解决取决于“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换句话说,这一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对这三个问题的彻底解决。(B20)
“形而上学的成败,因而它的存在便完全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B19)不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形而上学来说,与对于自然科学和数学来说,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数学和自然科学并不存在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它们以其长足的进展直接表明了它们的事实存在。对于这种事实的存在,追问其如何可能,在根本上只是追问它们的起源(Ursprung)或根据(Grund)。但是,对于形而上学来说,“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解决并非仅仅具有奠定其基础的意义,而且关系到形而上学本身能不能存在。
按康德上面的说法,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要超出经验界限之外。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超出经验之外的科学是否可能?而这也是康德认为不能随便搪塞的一个问题:“是否有一种独立不依于经验,甚至独立不依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我们可以把这种知识称为先验知识(Erkenntnisse priori ),以区别于经验知识(Die empirische Erkenntnisse )——这种经验知识有其后验(a posteriori )的根据,即其根据在经验(Erfahrung)中。”(B2)
也就是说,形而上学能否作为一门科学取决于是否必然存在一种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先验知识。根据康德的划分,一切知识或判断可分为分析的和综合的。显然,先验分析知识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它们构成了逻辑学的对象。如果先验知识只是分析的知识,那么,也就无需形而上学这门学问。于是,从根本上说,“形而上学是否可能”最终取决于“先验综合知识(判断)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存在这一事实表明,的确存在着先验综合知识。正是这种先验知识一方面独立于一切经验,因而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一方面又对经验事物有所规定,因而是综合的。由于它能被运用于经验,所以才使以这种知识为原理和基础的数学或自然科学能够获得新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存在这一经验事实虽然表明了存在先验综合知识,却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先验综合知识的存在是必然的。在这里,先验综合知识本身是必然的,但是,是否存在这种知识却并非必然的。因此,如果我们停留在经验事实上去确认先验综合知识的存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然的理由去建立形而上学。因为既然先验综合知识的存在不是必然的,那么,以之为对象的形而上学当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然性。
要确定先验综合知识存在的必然性,显然只有通过追问“先验综合知识(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才能实现。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将确认先验综合知识的存在,而且将给出这种存在的必然性根据。因此,对于形而上学来说,“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只是具有奠定其基础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确立形而上学存在的必然性根据。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既是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也是确立其存在的必然性根据。
“纯粹理性批判”之所以是基础形而上学,从消极角度说,是因为这种批判澄清了理性能力的两种运用及其界限,从而使形而上学避免重蹈陷入自相矛盾的覆辙;从积极角度说,则是因为这种批判将提供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的先验综合知识(判断),并对这种知识的范围作出规定,从而为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提供必然性根据。当纯粹理性批判澄清了先验综合知识并规定了其范围时,它本身也就构成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一部分。
四
不过,把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确立下来,并非仅仅意味着从此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新的知识,因为“先验综合知识如何可能”首先并非只是一个知(认)识论(Erkenntnistheorie )的问题。
追问纯粹数学或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我们发现了它们的基础:先验综合知识。追问先验综合知识如何可能,我们发现了它们的超验(transzendental )根据:它们能够关联到经验事物,但它们本身却不来源于经验,而是来源于超验领域。也就是说,先验综合知识首先是人这种存在者的一种超验存在。因此,人之有这种知识,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对经验中的他物有所知,而且首先意味着人的一种存在:这种知(Wissen)是一种纯粹先验的“预知”或“前知”(Vor-wissen)——先于经验而知,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术语说,就是一种前理解或前领会(Vor-verstandes ),人向来是且不得不置身于这种前知或前领会当中,人存在于“前知”当中。
更进一步说,对于人来说,“前知”同时也是经验事物存在的方式。我们首先只有在时间与空间这两种超验的感性形式中,才能让现实(wirklich)事物显现-存在。但是,在康德这里,我们在时空中只显明有物存在,有物被给予,并不显明是什么东西被给予。要使事物作为本质事物存在,必须让这些现象事物与我们不得不置身其中的另类“前知”即质、量、关系等超验范畴(意识)发生关联,否则就只有感性现象,而没有本质事物。
这意味着先验综合知识并不只是众多知识中的一种,而首先是一种有超验根据的存在方式。因此,“先验综合知识(判断)如何可能”首先就不是一个认识论(Erkenntnistheorie )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存在论(Ontologie )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基础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批判”首先就不是一种认识论。海德格尔在阐释《纯粹理性批判》时断然地说:“纯粹理性批判与‘认识论’毫无关系。”[1](P17)斯言可信。
[1]《海德格尔全集》,第3 卷,法兰克福,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