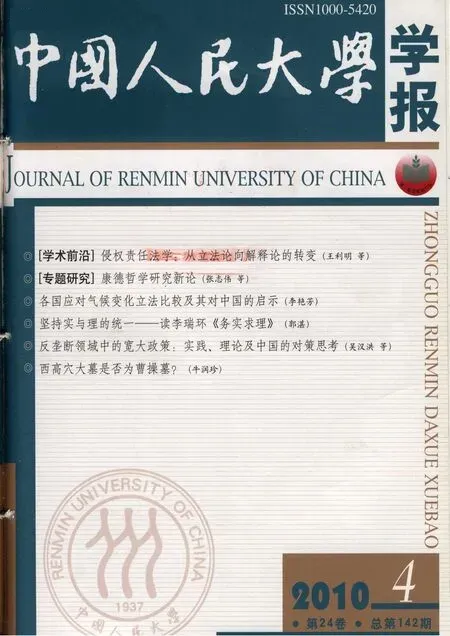从“方法论”看康德形而上学的架构与主旨
郭大为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长期以来,《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批判》)的“下半部”即“先验方法论”并不太为研究者们所重视,甚至被认为是在重复或总结“上半部”即“先验要素论”中的内容,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东西”,且“极端形式化”,表述上也“比较晦涩”。这些看法助长了对“方法论”的轻视和怠慢,由此引发了不明所以、望文生义的误读和讹传。
尽管按照当时逻辑学教本的通例,康德把他的《批判》划分为“要素论”和“方法论”两大部分,但《批判》中的“方法论”并不像传统逻辑学那样指向具体的应用,而是引向系统哲学的框架条件。只要将这里的“先验方法论”与《逻辑学讲义》中的“一般方法论”做简单的对比,人们就会发现,《批判》中的“方法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附件或可有可无的装饰:在《批判》中,“方法论”探讨的不再是单纯的定义、阐明、描述以及诸如“科学的与通俗的”、“系统的与零散的”、“分析的与综合的方法”,而是事关建造一座怎样的理性大厦以及如何建造这座大厦的“规划”(Plan)与“评估”(Anschlag)。在“要素论”中,康德勘测了建造理性大厦所要建基的基地,考察了可资利用的各种建筑材料(感性、知性和理性);“方法论”则需要根据以上勘测与考察的结果,规定正确利用基地与建材的操作守则,提出建设牢固可靠、适合人类居住的理性大厦的完整设计和实施方案。这样的方法论包括四个部分:(1)颁布了理性避免僭越或错误从而保证其正确运用的“戒律”;(2)在明确理性最高目的的前提下提出了建造纯粹理性体系所遵循的“法规”;(3)在此基础上勾画出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所必需的、内在有机的结构蓝图——“建筑术”;(4)通过对哲学的或“纯粹理性的历史”所做的系统的、“具有哲学意味的”的回顾与评判来确认所提规划的优越。这些内容与理性的两大立法即自然的立法与自由的立法直接相关,因而关系到对《批判》的根本任务乃至康德形而上学的构架与主旨的理解和把握。实际上,若不是为了回应各种抱怨、误解和攻击,康德在1787 年为第二版增写了著名的序言,读者只有到了《批判》的终曲处才能够真正认清康德哲学的“底牌”。
康德所说的“戒规”或“戒律”(Disziplin)是指“用来限制、最终根除偏离某些规则的经常倾向的那种强制”(A709/B737 )①引文出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下引只注第1 版(A版)、第2 版(B 版)页码。本文译文使用了邓晓芒和李秋零的译本,并根据语境做了少许改动。,它是在与“培养”(Kultur )即积极“技能”的获取相对照的意义上使用的,意指“管教”或“规戒”(Zucht ),本质上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虽然是否定性的立法”,以便建立起“一个谨慎和自我审核的体系”(A711/B739 )。由于理性在先验的使用中既无纯粹的直观,也无涉乎经验,因此,“它就十分需要一种戒律来约束它那把自己扩展到可能经验的狭窄界限之外,并阻止它放纵和失误,甚至纯粹理性的全部哲学都仅仅与这种否定性的效用相关”(A711/B739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类似的戒律已经存在于“要素论”对各种认识能力的有效范围与界限的考察中了,“戒律”不过是“辩证论”的翻版,只不过后者是“针对内容”的,而前者针对的则是方法或形式条件,因为不管内容如何,理性的运用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康德在这里针对纯粹理性的四种运用颁布了戒律:(1 )在独断运用中的戒律,主要是指哲学不能像数学那样仅仅出自概念来完成直接的先天综合,即实现所谓独断的使用;(2 )在争辩运用中的戒律,主要是指怀疑论只不过是颠倒的独断论,纯粹理性在单纯的思辨运用中并无真正的争辩;(3)在假设运用上的戒律,主要是指假设或猜想虽然在对自然研究中会起到促进作用,但一旦超出可能经验的条件独立运用时,它就完全丧失了合法性,从而沦落为单纯的意见或“思想游戏”;(4)在证明运用中的戒律,主要是指纯粹理性在其单纯思辨的运用中,不能像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借助于直观和经验而同时“先天地”和“综合地”获得知识,因而无法仅仅依靠概念自身证明其思维对象的现实性。
《批判》作为要完成一场思维方式变革的“关于方法的书”(BXXⅡ),在“方法论”中首先采取了一项令人惊异的措施:“为其他一切颁布戒律的理性本身还需要这样一种戒律”(A710/B738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理性能够颁布自我审核的戒律,虽然不能揭示真理,却可防范谬误;虽然只是消极的,却又是“纯粹理性的一切哲学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用处”(A795/B823 )。它限制将人的认识能力做超验的使用,从而有望终结形而上学混乱的争吵,这还构成了“这门科学的最根本的事务”(BXⅠX)。
如果说“纯粹理性的戒律”所探讨的内容还与“分析论”尤其是“辩证论”多有交错,那么“哥白尼式革命”的积极成果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才正式展现出来。康德把“法规”或“准则”(Kanon)“理解为某些一般认识能力的正确运用的先天原理的总和”(A796/B824)。康德认为,与“分析论”中所探讨的“纯粹知性的法规”(A796/B824 )不同,“纯粹理性的法规”只能是与理性在实践上的运用相关的。康德所说的实践是指“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A800/B828 ),而“纯粹理性的法规”所应用的范围正是“实践自由”所及的领域,而无需考虑在思辨运用中所涉及的“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A802/B830),它表明我们有一种能力,可以克服感性欲求方面的束缚,运用理性确立我们行为所追求的目的,这样一来,理性就成为自然的原因,即理性在对意志做规定时具有原因的性质。“所以理性也给出了一些规律,它们是一些命令,亦即客观的自由规律,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发生的。”(A802/B830)
从“法规”开始,《批判》不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内容上乃至风格上,都发生了一个从理论向实践的急剧转向,这一转向看似迫不得已和草率匆忙,但又具有充分的根据,因为这一转向关涉到理性的最高目的:“这些最高目的按照理性的本性又都必然具有统一性,以便联合起来去促进人类不再从属于任何更高旨趣的那种旨趣。”(A798/B826)康德将理性的全部旨趣概括为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2 )我应当做什么?(3 )我可以希望什么?理论理性回答的是第一个问题,这在《批判》(主要是“要素论”)中已经得到了详尽的探讨。第二个问题是单纯实践的,对它的专门阐述是在后来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 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 年)、《道德形而上学》(1797 年)等著述中完成的。在《批判》中,“法规”对第二个问题也作出了独特而恰如其分的回答:“去做那使你成为配得上是幸福的事情吧!”(A809/B837)之所以说这个回答是恰如其分的,是因为《批判》并不以系统探讨道德哲学为己任,“法规”中的这个回答是着眼于“纯粹理性最后目的”这一指导原则来给出的,它对于道德哲学的探讨是从配享幸福的角度加以表述的。由于第三个问题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它涉及自由与自然的统一,指向所有值得追求的东西的总和即至善。对于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人来说,单单具有德性或幸福都还不是完整的善,只有二者按照精确比例的合一才能达到至善。因此,人所应有的“合理的希望”也就在于:一个行为良善的人可以享有与之相称的幸福。在康德那里,道德神学以及目的论和宗教哲学问题都是遵循这些原则来加以解决的。
明确了理性的最高目的及其相关问题,“法规”的意义就在于划定由此获得的认识的等级,确定各自的价值。康德“在‘意见、知识和信念’这一杰出的匠心之作中,将他的希望认识理论置于一种系统、全面甚至是完备的认识论之中”[1](P299)。“法规”既然是针对实践理性的立法,其任务就在于给出正确理解和对待实践或道德信念的知识论原则。一方面,信念处于意见与知识的居间等级,诸如上帝或灵魂不朽这样的理性的理念虽具有上升到更高的统一性的调整性的功能,但它们并不是知识,不具有客观上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信念对于实践理性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理性的最高目的乃至整个批判体系的统一性,更与人的现实生活、与人的价值和尊严密切相关。为此,康德“不得不限制知识,以便为信念留出地盘”(BXXX)。
虽然康德所规划的狭义的形而上学体系依然保持着与传统形而上学相近的外观,但康德所力图建构的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材料和景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康德不是从经院或学院的立场出发来构建科学的体系,而是从人的、世俗的立场出发的。从哲学的“世俗概念”(Weltbegriff )来看,“哲学就是有关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之关系的科学,而哲学家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专门家,而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A839/B867)。“终极目的无非是人类的全部使命,而有关这种使命的哲学就是道德学。”(A840/B868)由此,康德第一次宣明:“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个对象,即自然和自由”(A840/B868)。前者针对的是实然之物,后者针对的是应然之物,实践理性占据着优先地位。
根据纯粹理性在思辨和实践上的两种不同应用,广义的形而上学就划分为自然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既是康德后来以“形而上学”之名发表著作的仅有的两个领域,也标志着“对人类理性的一切教养的完成”(A850/B878)。作为狭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形而上学具体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1)本体论;(2)理性自然学,包括理性物理学和理性心理学;(3 )理性宇宙论;(4)理性神学。纯粹理性的这一“建筑术”(Architektonik)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亦即狭义的形而上学来详细设计理性哲学的体系的,虽然这种自然的形而上学的主要功用不在于扩展知识,而是更多地被用于防止错误,但这并没有损害它的价值,反而促进了科学的共同事业的普遍秩序与和睦,从而与道德形而上学一道实现了康德所引“题词”中预设的目标:“为人类的一切福利和尊严奠定基础”。
总之,“方法论”虽然探讨的是完备的科学体系所需的形式条件,但由于涉及整个理性大厦的规模、结构与可靠性,因而它不但并不是“极端形式化的”,而是恰好相反,它第一次公开展现了康德所构想的科学形而上学体系的全部内涵。康德深信:《批判》并不仅仅为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是已经提供了体系本身。因此,《批判》中的“方法论”就像是指向通往科学形而上学的路标,我们在此首次总览了整个批判体系的蓝图,找到了进入康德思想秘库的门径。
[1]Otfried Höffe.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ie Grundlegung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Verlag C.H.Beck,Münche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