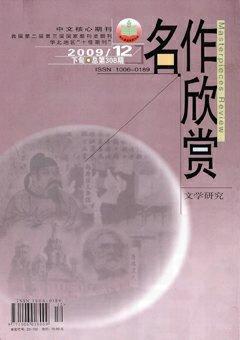膜拜·审美·消遣
关键词: 青年读者 阅读 膜拜 审美 消遣
摘 要: 青年读者作为受众在建国60年中的不同时期(即接受社会语境)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前30年(包括17年文学和“文革”)的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榜样化的社会语境时代,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实际上就是被教育者,他们进行的是顶礼膜拜式阅读;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中期的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经典化的社会语境时代,他们是与创作者进行交流的对话者,他们进行的是审美体验式阅读;90年代中期至今的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偶像化的社会语境时代,他们是盲从偶像的“上帝”,他们进行的是消遣娱乐式阅读。
新中国至今,中国文学走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60周年值得纪念和反思。国内著名学者杨义就曾指出:任何对文学研究之未来进行展望与规划,若与历史意识相融合,都必须立足于现实对文学学术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深度把握和认知上。{1}学界纵观60年的各类反思研究肯定会很多,角度也会不同,但从接受角度反思文学历程依旧是少,学界不应该忽略对建国后文学接受的考量,有必要审视反思建国60年来文学阅读的演变。文学阅读已走过60个年头,文学阅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青年受众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他们是被教育者?还是对话者?他们的阅读动机、阅读方式有什么改变?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事实上,围绕着文学阅读的研究,确有许多新旧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下文笔者就想从新中国60年文学阅读接受语境的演变、青年受众身份的变化及阅读方式的嬗变等问题做点初、浅的探讨。
一、榜样化时代中的膜拜化阅读
文学阅读是读者接受文学文本的活动,它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文学活动的最终目的。文学阅读按理说是一种个体性的自由活动,难以统一和规范,在文学阅读中,其外在的因素就是作为客体的文学文本和作为主体的读者;然而,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语境中,文学阅读未必如此。因为每个读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的,他们所从事的文学阅读必然会打上他所处的时代的印记,本是个体的“求导”阅读会变成“趋同”阅读,它受制于“社会”这一因素太重了。
新中国成立后,前30的文学是一个榜样化的阅读时代。说它是榜样化,主要是因为这时形成了一个思想和艺术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阅读局面,因为这时的“文学事实”——作家的身份,文学在社会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写作的性质和方式,出版流通的状况,读者的阅读心理,批评的性质、题材、主题、风格的特征等都实现了统一的“规范”。{2}这种统一的“规范”在笔者看来就是榜样化。首先表现在题材的集中,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几乎构成了这30年文学的大半江山;其次是主题的重大与鲜明,主要表现在阶级性;再次是人物形象的“高、大、全”(即英雄形象)。而这些无疑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所需求的真正的红色经典,我们可以从所谓的“三红一创、山青保林”和周扬1960年7月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提到的11部小说看出这一点:《三家巷》、《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黎明的河边》、《铁道游击队》、《草原烽火》、《战斗的幸福》几乎是清一色的革命题材。
文学历来就承载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使命,在建国初期,这种使命更甚。当时强调作家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担负起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任务,积极培养新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在这种统一的“规范”语境中,青年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教育的对象。浓厚的意识形态教化的意味几乎遮蔽了审美,读者的文学阅读自然就多了共性而少了个性。造就出这种榜样化的阅读时代,是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众所周知,那30年是特定的时代,文学艺术形式很不被重视。洪子诚先生就曾指出:“50年代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小说更加强化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同时,小说的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也总是被放置在首要位置上加以考虑。”{3}当时通行的文学观念对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二为”方向,此外,还有“内容决定形式”、“题材决定论”、“写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等风行一时,到文革时这种极左思潮则达到顶峰,就出现了所谓“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的局面。
榜样化的阅读时代也与社会的普遍期待视野有关。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正是以普遍的文学期待和阅读需求的形式对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起着制约和导向的作用。当时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主要就是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的讴歌。在文学意义上,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事件”,它的直接后果就造成了青年读者对“事件”膜拜式的关注与崇敬,这应该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特别发达的主要原因。这30年尤其是“十七年”之所以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阅读体验之所以是一种激情体验,应该都与这个“事件”密切相关。它们催生了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阅读期待,特别是没有经历过这一事件的青年读者便试图从文本中去体会革命的痛苦和欢欣。正是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左右着30年青年读者的阅读喜好、阅读动机和阅读目的,它改变了整整一代青年读者进人历史、阅读历史的方式。
也正是由于有着这种共同的阅读追求,有着对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历史巨变等的共同崇敬乃至膜拜。所以在它的作用下,社会产生出了一个强大的阅读心理场,社会群体中个体的感情、意志、动机统统臣服于主导历史巨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个体的阅读差异减少了,群体思想和观念的一致性、统摄力和凝聚力增加了。所有青年读者都希望从文学中寻求榜样和理想,随着一部部史诗式的表现革命战争和宏观展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长篇小说的相继问世,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和具有指导意义的性格形象,便成为青年读者们膜拜的对象,这是种顶礼膜拜式的阅读。这种阅读无疑包含了青年读者们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这时期革命文学、农村文学包括文革的样板文学之所以受到青年读者欢迎,艺术不是重要的,而主要是由于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导致的膜拜需求所造成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青年读者的政治热忱、价值取向和期待视野。当然,革命历史题材文学阅读的期待视界既不强调文化传统和语言方式的继承性,也不强调文学阅读的知识与经验储备。它是一种普遍的、由巨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全社会的心理预期,是对意识形态近乎宗教情绪的仰慕。{4}
革命文学以及随后的农村文学深入人心显然与当时青年读者们普遍的“趋同”阅读心理有关。在那个时代,文学被赋予一种神圣性,被国家机器加工后自然会受到青年读者们宗教般的顶礼膜拜。时至今日我们对这30年文学的阅读仍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束缚,近两年热捧的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就是例证。当然也不排除那时有一些青年在从事着个人的、分散的对现代文学文本及其他文本的阅读。
二、经典化时代中的审美化阅读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也吹绿了文学,社会语境的改变为这时期文学阅读提供了崭新的空间,伴随着历史脚步中国文学进入了建国后第二个阅读时代—— 一个经典化的阅读时代。所谓经典化的阅读时代就是人们重视文学,以为文学是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工具;人们重视作家,以为他们是社会文化的主宰者;但不再盲目崇拜,读者喜爱反复细读经典,以读懂经典为荣。文学的创作、文学的阅读和文学的创造者,都被神圣化了。从而形成了作家的写作、读者的阅读、文学史的纪录,都去追逐经典的总体情势。{5}
80年代就是个典型的经典化时代,中国的文学和青年读者们一样处于兴奋状态,这是创作的黄金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一波又一波;朦胧诗歌、先锋文学,一个又一个……同时,也是阅读的黄金时代,许多青年读者以亲近文学为荣,孜孜以求于文学。阅读是一种如饥似渴、大快朵颐的阅读,逮住就一拥而上。文学是人们生活的重心,几乎每一个识字的青年都在读小说读诗,他们对文学保持着一种崇敬,他们愿意从文学中寻找满足和寄托,有人称它为阅读的童年时代,一点也不为过。成为那时阅读时尚的书,除中国文学文本外还包括当时大量引进译介的西方大量经典文学名著和美学名著,如《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古典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受到许多读者尤其是大学生的青睐,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与文艺思想受到青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在这个时代,青年读者们在持续不断地享受着阅读与欣赏的快乐。不仅如此,对外来文本的阅读还造就了一批以马原、格非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是中国阅读界猛喝洋奶粉的年代。
按照德国阐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的理论,阅读是读者与文本间的对话,文学文本是一种吁请、呼唤,它渴求被理解,而读者则积极地应答,理解文本提出的问题,与文本之间进行交流。前一个时代受社会因素影响,青年读者是作为被教育者与文学发生着紧密关系;而在这个时代,青年读者与文学仍然发生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仍然在崇敬文学;但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崇敬,而是主动的阅读,首次以主体的身份与文学“对话”。这时少了政治功利性和直接目的性,青年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基本上是平等的、开放的,也给这时期的青年读者们以更多的主导与创造,同时也造成意义的多样、不定与模糊,文学开始走向了本体。
这种经典化的阅读时代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恰逢意识形态去政治化时代的心灵补偿以及随后的启蒙;二是由于当时文化资源的不足。按现代心理学的认识,寻求补偿是人的天然本性。文革结束后,长期的精神窒息、文化饥渴和人性压抑所积郁的巨大情感能量,迫切需要有一个释放或补偿的渠道,而由于文学的情感特征和理想品性,就使得文学阅读成为满足人们情感补偿的较为理想的方式,文学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重任,承担起了抚慰人心、填补沟壑、通顺人际的功能。这不仅是因为“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的文学具有启蒙性,还因为当时社会条件的落后,文化资源的稀缺,传媒方式的单一。在那个媒介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人们可供选择的审美方式不多,青年学子由于宿舍既无电视更无网络,就不得不从文学阅读中寻找智慧与快乐。像《班主任》、《伤痕》、《李顺大造屋》、《大墙下的白玉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在当时之所以会轰动以及“朦胧诗”、各种新潮小说的受宠,就是因为文学文本所营造的与青年读者所追求的具有某种同构性,那是一个全民读书热的时期。
由前所述,随着阅读语境的改变,青年读者的阅读动机和阅读方式也在改变,他们不再是被教育者所进行的顶礼膜拜式的阅读,而是作为与文学对话的“对话者”所进行的审美体验式的阅读。在文学阅读中,由于青年读者的整个身心都被调动起来去拥抱文本中的艺术世界,从而获得那种审美情感体验的真切性、亲切性和深切性。当他们读到心怡的语句时似乎就找到了自己感情的依托,找到了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等诗句就给了无数文学青年以鼓励与共鸣。当他们在现实生活遇挫时首先想到的是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抚慰。于是,路遥、张贤亮等人的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写作姿态的小说以其蕴含的情感体验赢得了当时的读者,尤其是文学青年的共鸣,而备受热捧,这些作品几乎就是当时许多热血文学青年的励志之作。这或许就是“审美性置换”吧。
三、偶像化时代中的消遣化阅读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步入了90年代中期,此时的青年读者面临的是建国后阅读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阶段,高科技迅猛发展、网络大量普及、现代传媒狂轰滥炸,很多青年严格地说已不再是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的读者,他们远离了文学,选择了更为直接刺激的图像和网络,对文学也不再抱有热切的期待,从作品中体验崇高、进行民族关怀已不再是此时青年读者的主要阅读动机和心理期待。大多数文学青年随个人的趣味似乎更愿意从文学中寻找日常与闲适,追寻时尚与流行,让缺失得到代偿、让伤痛得到抚慰,让感官得到刺激、让欲望得到释放。{6}
说第三个阶段是偶像化的语境时代,是因为文学作为商品与传媒的联姻,“偶像”字眼与青年读者如影随形,从网站写手的偶像化包装,到大小媒体的明星作家式运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现,时下青年读者正处于一个偶像化崇拜的接受语境。有些青年写手靠形式的绚美、青春偶像的装扮、青春叛逆的书写等来投合青年读者青春期“偶像崇拜”的心理。现代传媒则与之不谋而合,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大势能将他们包装成明星式的偶像。在时尚的包装下,青年读者一哄而起,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且庞大的“文学粉丝团”。其中又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三人的“粉丝”为最。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样的接受语境里创作数量、销售数量是巨大,精品却不多,热衷于崇拜且过度、不节制的青年读者不在少数,而真正进行文本阅读的理性青年读者却不多。
在这个时代,青年读者不再是俯首聆听作家教诲的被教育者,也不再是与文学进行心灵的沟通的对话者,而是作为文学市场的“上帝”,按着自己的个性、意愿,来进行选择、参与和盲目性崇拜,甚至背叛性阅读。他们拥有了更充分的自由与随意,他们不仅可以随意地阅读文学,甚至可以随意地进行“七嘴八舌”式的评论,比“我是流氓我怕谁”更甚。这些粉丝在现代传媒的鼓动下对明星作家、作品是率真而盲目的崇拜,在他们眼里偶像似乎永远是对的,偶像的作品永远是好的,谁说不中听的就群起而攻之(如著名的韩白之争事件)。由于有着便利的条件,他们不仅可以从多媒体的阅读(读书、读图、读屏)中享受快感,而且还获得了超文本的阅读空间,可以随意的“误读”。
之所以会这样,既是文学商品化的结果,也是科技发展的结果。
文学走向市场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期待,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媒体也要考虑自己的上帝,要制造上帝,让之消费。兴起于世纪之交网络在改变文学传媒的同时,也改变了读者接受文学的方式。接受的在线性可以让读者直接参与评论和互动,而网络的虚拟性又给了青年读者畅所欲言的机会,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看法。比如,当年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网上走红,引来无数网迷的跟帖,他们的讨论、建议甚至让慕容雪村改变了原来的情节设计。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可以亲自进行网络写作,成为网络写手,体会写作的快感,而这正是青年读者的喜好。难怪学者赵宪章说:“互联网的问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写作生态,改变了文学文本的存在形式,改变了文学传播,文学阅读以及文学批评的原有格局,而且对传统文学的发展与存在也产生了诸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7}正是网络的便捷、媒体的炒作与青年读者的热情造就了一大批过度、不节制的文学粉丝。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青年读者们阅读文学主要不在于认知、体验,而在于消遣娱乐,他们不会像第一阶段青年读者那样进行膜拜式阅读,也不会像第二阶段青年读者那样沉下心来进行审美化阅读,往往热衷于“文化快餐”,其阅读的兴奋点也早已不在那些具有深度的传统经典文学名著了,而那些迎合感官刺激、具有短小平乐和“心灵鸡汤”(如名刊《读者》)等特性的亚文学却很受欢迎。在印刷文本、视觉文本和网络文本三分天下的今天,大多数青年读者不会再从事真正的文学阅读,如果有文学阅读也充其量是消遣娱乐,这种阅读可以是“悦读”也可以是“速读”,还可以是“东北乱炖”式的“胡读”,却唯独不大可能是让人遐想、引人沉思的审美阅读。{8}
四、结 语
应该说,对文学文本的阅读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不需要由谁来指手画脚,但是,在某个特殊化的社会语境中,个体的阅读往往是受制于社会的,呈现出一种社会性行为。
由上所述,新中国60年中不同时期青年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是不同的,作为受众的他们在不同时代(即接受社会语境)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前30年(包括17年文学和文革)的青年读者处于一个榜样化的社会语境时代,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实际上就是被教育者,他们进行的是顶礼膜拜式阅读;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中期的青年读者处于一个经典化的社会语境时代,他们是与创作者进行交流的对话者,他们进行的是审美体验式阅读;90年代中期至今的青年读者处于一个偶像化的社会语境时代,他们是盲从偶像的“上帝”,他们进行的是消遣娱乐式阅读。从膜拜到审美再到消遣,青年读者们经历了一个从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再到主动参与的过程。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青年读者在阅读时整体呈现出的是政治化,第二阶段是审美化;那么,第三阶段则是时尚化、快餐化以及技术化的倾向。文学作为一种商品,尽管是特殊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读者的阅读。接受美学把读者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因此很多人认为读者的阅读需求对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其实,在笔者看来,60年中不同时期青年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历程未必如此,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文学阅读受制于社会的变化。
作者简介:石群山,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① 杨义.文学研究走近二十一世纪[J].文学评论,2000,(1):5.
② 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96,(2):60.
③ 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
④ 杜国景.论十七年文学的两种阅读期待[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5):40.
⑤ 黄浩.从“经典文学时代”到“后文学时代”——简论“后文学时代”的五大历史特征[J].文艺争鸣,2002,(6):44.
⑥ 姜桂华.从国族关怀到个人趣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接受心理变化的表现[J].渤海大学学报,2008,(3):37.
⑦ 赵宪章.新媒介·新机遇·新挑战[J].江西社会科学,2009,(2):7.
⑧ 赵勇.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9,(5):141.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