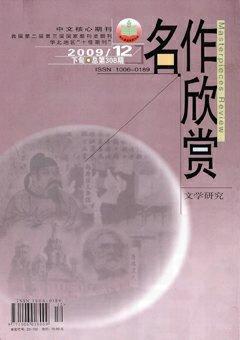现代繁华里的流放
回望故园的作品无疑是汪曾祺小说的群峰,他的小说成就自以写高邮的为翘楚,其中《鉴赏家》与其说是作家用诗的方法写小说,不如说他用小说的方法写诗。作品环绕季匋民的画作获赏果贩叶三而终生珍藏、至死不售的佳话,穿插当地风俗轶事、人情物理的诸多章节,以诗意写清愁,以繁华写寂寞,以平静写伤悼,一切如同亲历,娓娓道来,《鉴赏家》雄辩地成为汪曾祺文化小说的一处要塞。
一、民间奇迹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小说破题陡峭,出语惊人。季匋民虽与叶三身份迥异,但二人都品行高洁,且意趣相投。画家远离尘嚣,忘情于丹青;果贩留意人间幽微、草木细情,这成就了他在赏画时的洞见。这样的两个人是没有雅俗之别也不需要什么弥缝的,故事因之可信、动人。大凡汪曾祺泼墨浓重的人物都近义远利,见贤思齐,心中固有一种道德高标,时时自觉地进行反省、完善,对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有时人物本身就是古朴文化的持有者、代表者,叶三、季匋民都是直观的例证。
叶三是不一样的果贩。他不开铺,不摆摊,也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而是专给大宅门送货上门;他的果子总是得四时之先,市上还没有时他的篮子里已经有了,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叶三的果品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匀、香、甜,极是好看,统为“树熟”;他四乡八镇到处跑,经常外出到产地采办,出去买果子比他卖果子的时间要多得多,风里雨里,水路旱路,别的果贩都不肯下这样的工夫,他也因此比别人见多识广;他从不说价,买果子的人家也总不会亏待他,这不像交易更像一种人情往来;儿子孝顺、家境殷实、大可在家安心养老的他差不多是为季匋民一个人卖果子,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挣钱,给季匋民送是为爱他的画……
叶三更是不一样的鉴赏家。他是现实中的有心人,富于智慧,有偎近艺术的强烈愿望,更善于从实际经验出发得出关于画作的真知灼见,终于从一个单纯的欣赏者变成季匋民创作的参与者、评判者。
他给季匋民送果子,一来就是半天。他给季匋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绿、抻纸。季匋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意,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的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匋民的得意之笔。季匋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
汪曾祺直呼叶三为“鉴赏家”,也就是说作品的题目没用“果贩叶三”、“季匋民与叶三”或是“鉴赏者”,都是作家有意为之,这是汪曾祺由衷的结论,也是他向人物献上的一份敬意。能够对季匋民的画品精准点拨,对名家李复堂画迹的真赝识别一二的叶三,也确实当得起“鉴赏家”之名。汪曾祺说:“一个中国人,即便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是在文化传统里活着的……我写的人物身上有传统文化的印记。”{1}当然“鉴赏家”只是叶三一时一地的副身份,他的本职是果贩,但也就足够了;有了他本职的映衬,其副身份无疑多了一种弥足珍贵的、神性的光辉。
汪曾祺的视线几乎会习惯性地越过都市,作家在这篇小说里更是特意地、最大可能地安置了一个民间背景。季匋民不是世界、国家、省级画家,而只是一县之冠冕,是否真的有说服力?这与我们指认大家、名流的标准有太大的不同。其实这里也有一个汪氏的判断,他更信赖民间,认定奇人、奇事、奇迹往往就产在民间,有时甚至只产在民间。但季匋民不是作者的凭空想象,其原型曾任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主任及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兼上海《美术生活》特约编辑,得与徐悲鸿、黄宾虹等共事,39岁时辞去教务重返故里高邮。小说不写他这段世俗眼中更富华彩的人生段落,而写归隐的季匋民,写身在民间的季匋民,自是深味意长。
“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风格。”{2}用民间语说民间事也是这篇小说的一大奇观。只有“叶三”才能说出“紫藤里有风”、“这是一只小老鼠”之语。汪曾祺充分施展自己的摹态功夫,还原百姓日常用语,彻底放弃高谈阔论。要知道作家本人就是个著名的书画家、书画鉴赏家,他是有资格高谈阔论的。山东画报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图文并茂、读了养眼养心的《汪曾祺文与画》,书中除收了他106幅书画作品之外,更有十五六篇理论文章。据他的女儿汪朝回忆,汪曾祺对故宫博物院书画馆的藏品能够如数家珍。“高僧只说平常话”,汪曾祺借助白描语言的神力,让恬静淡泊的果贩与常常一语中的鉴赏家的形象精致地叠合在一起。
二、闹市之“士”
《鉴赏家》中的季匋民易于让人想起史上实有其人的大画家王陶民,后者汪曾祺曾在他的《看画》等多篇作品中提到过。王陶民(1894—1939),江苏高邮人,名珍,号陶民,以号行。擅花鸟、走兽,兼擅指画,并工诗及篆刻。其作画重师古而又重现实经验,他的艺术成就得到过吴昌硕、张大千等大师的激赏。返乡后,他以卖画为生,平民按润格付款,有求必应;对豪绅权贵多不理会,甚至以画相讽。1939年日军侵占高邮时卧病,后悲愤离世。如今我们仍能在许多场合看到他格调高雅、清水芙蓉般的画作。不论是真实的王陶民还是虚构的季匋民都会让人记起汉语中一个久违的命名“士”。
季匋民旷达超脱,他有一个率性的脾气,总是一边画画一边喝酒。他喝酒不就菜,只就水果。每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最佩服李复堂的季匋民最爱画荷花,且画的都是墨荷。他的画常是大写意,笔意俱到,笔致疏朗,善用空白。“他画的荷叶不勾筋,荷梗不点刺,且喜作长幅,荷梗甚长,一笔到底。”季匋民人在市井之中,心在市井之外,在物欲的漩涡里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他那些不染尘渣的画正是他高贵精神气质的外化。
季匋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因为季匋民是大画家,这些名士就特别爱在他面前评书论画,借以卖弄自己高雅博学。这种议论全都是道听途说,似通不通。季匋民听了,实在难受。
“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不但适用于先秦时代的儒家知识人,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后世各派的知识人。”{3}士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作用及内涵演变相当驳杂,但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核心任务。士是知识精英的别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音区。在现代社会,士要么已成为历史遗迹,要么被挤压在某个角落,但其依然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4}从某种意义上说,《鉴赏家》生动地展现了士被繁华、被世俗边缘化的艰难处境。
画家季匋民与果贩叶三在他们各自的生活圈里都举止超常,这样的画家与鉴赏家的奇妙组合也极超常,在人群中他们只对彼此“另眼相看”,何以会有这另一段高山流水的知音传奇?显然是因为士的血脉让他们不约而同地跳出商业重围,暂时避进传统文化艺术的幽静,尽量不受商业惊动。他们的相遇,他们的惺惺相惜,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心灵选择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这两个古朴的人物身上,汪曾祺寄寓着一种无比深厚的人文理想。而汪氏自己也一直效仿季氏的“荷梗甚长,一笔到底”,他画的花全是“杆子都这么老长”{5}。
季匋民送了叶三很多画,有的题了上款有的没题。叶三对季匋民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不卖。”《战国策·赵策》有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士为知己者死”,果贩叶三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到了。“季匋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匋民坟上供一供。”作为“士”,作为被现代繁荣放逐的“士”,季匋民和叶三并没有过“感士不遇”的大声鼓呼,而是在寻到知音甚至是唯一的知音时,沉潜于彼此倾力打造的心灵憩园,他们悄悄地苦守着自己的坚持,这样的沉默更具力量。
有评论家认为这篇小说应在“到季匋民坟上供一供”后即收尾,现在这个样子有些拖沓。这样的见解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的。“多出来”的300多字,大致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季匋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日本有人专门收藏他的画”;二是叶三手上的季画都是神品,他断然拒绝了迂听涛的高价求购;三是叶三如愿与画一同埋进棺材。汪曾祺曾说过:“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是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6}但是作家很难做到平静、释然,“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7}。我们看得出来,是这个结尾让情节越发伸向远方,一种力透纸背的苍凉,使作品的内容和主题都得到了大力的深化和提升,有了更上一叠的美学高度。
三、“最后一个”
与其说汪曾祺比许多作家有着更为突出的“最后一个”情结,不如说他对一些珍贵的流逝更为敏感。中国当代作家对“最后一个”是很有兴趣的,我们随便就可列举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凶奴》,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肖克凡的《最后一座工厂》,降边嘉措的《最后一个女土司》等等,这还不包括像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一大批题目未见但内容隐含着“最后一个”的小说。“最后一个”更是汪曾祺的一个挥之难去的心结,《徙》中的谈甓渔和高北溟,《故乡人》中的王淡人,《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喜神》中的管又萍,《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三姊妹出嫁》中的秦老吉,《故人往事》里的戴车匠,《茶干》里的连老大……他们适性随意,或是地方名流仁爱高尚,不同流于污浊世态;或是耿介刚直的一方隐士,急公好义;或是与世无争的寻常百姓,身怀绝技。这些人物都被“最后一个”轻轻着色,作家拼命地想抓到、挽留什么,却是无果,只能听任其凋零和远去。
《鉴赏家》写到了“最后一个”鉴赏家,还写到了“最后一个”画家。“果贩+鉴赏家”的奇异融合,应是绝无仅有了;像季匋民这样,用诗、书、画、人格一同诠释传统美德的画家也难得一见了,汪曾祺曾在追忆一位文化名人时慨叹“能题这样也深也浅,富于阅历的诗的画家似乎已经没有了”{8};对季匋民而言,叶三之外别无知音甚至别无可谈者,时代对他们的冷落与疏远让这些以心相交的人情美景已无以为继,恍若隔世;连同作品中的诗情画意,也极可能成为最后的生活、最后的景致: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
表面看来,作家是用疏朗的笔画、用各色水果勾勒出了一幅当地的四季风物图和一年的光景,其实这是写一种安静、适意的淳朴生活,须知“风俗即人”。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背后是作家爱怜、感慨的眼神,因为他深知“这种封闭的古铜色的生活是存留不住的”{9},一切都将改变。暖洋洋的抒情中深隐着汪曾祺的“人面不知何处去”的伤怀之思。
汪曾祺本人好像也是“最后一个”,他被人唤做“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可能这些说法未必合适,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点什么。包括汪曾祺在内那些深受中国古典文化濡染的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相近的思想履历,相近的文化心理结构,相近的随遇而安、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和相近的美学趣味,因此对古朴现实有着一种特别的热爱,所以一旦现代商业文明对这种生活造成破坏,他们就会陷入一种巨大的焦虑之中。他们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曲折前行、来之不易,深知它是我们这个民族非凡智慧和精神境界的杰出代表,他们更知道随意挥霍或是听任其渐行渐远我们损失的是什么。
“最后一个”带有“原型”意味,是一种益于心理聚焦、悲悯叙事的捷径。我们从汪曾祺的《鉴赏家》等作品中能够读到一种矢志不渝的努力,那就是最大可能地挽留传统文明。“汪曾祺在一次又一次的奔走呼号中不是一个落败者,但也肯定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胜利者。”{10}现代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除了带给我们一种又一种崭新的气象,一场又一场极大的欢喜,还会不可避免地带走一些东西,其中自然也包括曾经伴我们度过无数艰难时日的许多美好的东西。
《鉴赏家》逼真地记录了珍贵的古典文化被现代商业文明的一次流放,当然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我们还可以把它当做一篇特别的艺术批评来读。作品涉及了艺术家、作品与鉴赏家,艺术创作、生活实践与道德人格,艺术品、商品与时代潮流的繁复关系等诸多问题,并且作家也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这又一次明证大家之作往往是多声部的。
作者简介:林超然,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学报主编,燕山大学兼职教授。
{1}{7}{8} 《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第116页,第274页。
{2}{6}{9} 《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第198页,第130页。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页。
{4} 《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
{5} 《汪曾祺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10} 《二十世纪心灵的文学关怀——汪曾祺论》,林超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