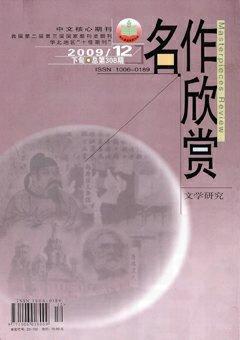烛照城市底层的温暖与尊严
袁 萍
关键词:王安忆 《骄傲的皮匠》 城市底层 温暖 尊严
摘 要:《骄傲的皮匠》讲述了一个底层的外来者在融入都市日常人生过程中如何获取安稳、守护尊严的生活故事。王安忆消解了以往有关城乡叙述中基于道德或文明视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一种温暖的笔调,营构出都市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空间。
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应该是2008年度最好的中篇小说了,在不久前由北京文学月刊社和中国小说学会组织的两次年度排行中都名列中篇小说的榜首。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流逝》到90年代的《长恨歌》,再到新世纪的《桃之夭夭》,王安忆一直留恋着她的上海故事,经营着她的弄堂人生,虽时遭诟病,仍乐此不疲。她说:“上海是我唯一的写作源泉,我只能尊重这个事实。如果只能写上海的话,就必须挖掘这个城市的资源,对于上海来说,小市民的生活是那么巨大的源泉和材料,你怎么能无视它的存在?所以,这个小市民的写作,以后还会继续的,不可能改变。”{1}《骄傲的皮匠》仍然是关于上海普通市民的弄堂人生,王安忆用一种温暖的笔调,营构出都市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空间。小说讲述了一个底层的外来者在融入都市日常人生过程中如何获取安稳、守护尊严的生活故事。
一、城市底层的温暖叙述
在王安忆以往的上海叙述中,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负载了都市沧桑的名媛佳丽,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文革轶事》中的胡迪菁、《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等,作者常常借人物命运的起伏演绎城市历史的变迁。《骄傲的皮匠》与王安忆以往的上海叙述不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再只是负载着都市沧桑的上海人,而是承袭了乡村记忆和城市变迁的外来客。这是一个叙述都市的新视角,王安忆消解了以往有关城乡叙述中基于道德或文明视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小皮匠根海的身份有着较为复杂的文化意味。一方面,他来自苏北农村,一家老小在乡下,与乡村有着血缘联系的他并没有完成精神上的迁徙,孝顺、纯朴、善良等乡土中国的传统道德操守仍然顽强地矗立在他的精神深处。另一方面,他住在上海,在城里谋生,与这座城市有着较为久远的渊源,他的皮匠家族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因而在他身上又显见许多现代城市文明的印痕。
张爱玲说,“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作为新一代的“海派传人”,王安忆深知“人生安稳的一面有着永恒的意味”。《骄傲的皮匠》用的是“人生安稳的一面”做底子,近乎琐屑的生活场景,随处可见的寻常人物,王安忆用“寻常人”的视角,携带一点怀旧的感伤,在市井人物的寻常生活中找寻一种温暖的诗意。皮匠街头做活的场景在平凡的世俗中蕴含着生活的魅力。王安忆用镜头式的语言描写了两代皮匠做活时的动人场景:“皮匠摊跟前的小马扎上,常常坐着一个女孩子,脱了鞋的脚踩在另一只脚的脚背上,等待皮匠做完她的活计,这情景看起来挺温馨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仍然是在这块“方寸之地”,当年的老皮匠换作了小皮匠,小女孩换作了老太太,作者又一次描绘了小皮匠与岳母街头静坐的场景:“岳母守在小皮匠身边,看着小皮匠接活做活”,“弄堂前马路上的景色,曾经在她男人眼睛里流连过,女婿手里的活计,就是她老头子的手艺,似乎觉着将来有靠头了一些”,“一老一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么缄默着”。皮匠摊前的“缄默”中流露出的不只是相互依赖的信任和亲情,更有动人的人性光辉和日常生活的诗意。小皮匠吃饭时的“家常一幕”更是溢满了安稳人生的温暖。当乡下亲戚到来的时候,“小皮匠家的饭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东西都是从乡下带出来的,草鸡炖汤,六月蟹拦腰一剁两半,拖了面糊炸,蝽子炒蛋,卤水点的老豆腐,过年的腊肉或者风鹅,还有酒。要是小皮匠的父亲在,就两个人对酌,单小皮匠自己,就是独饮。他喝一阵子,吃了一些菜,女人就给盛上满碗的饭,重新热了鸡汤。虽然是盛暑,可他们家乡的习惯,荤汤是要吃大滚的,吃出一身热汗,内里的湿热便发散出来。果然,风吹在身上,沁凉了许多。月亮也升起了”。为了在小皮匠的日常生活和城市栖居中烘染出诸多令人感动的温暖和诗意,王安忆不惜篇幅地絮叨着琐屑的生活。当然,这些温暖和诗意不只是来自小皮匠身后深厚绵远的乡土亲情,也有他日夜置身其中的城市友善。
小皮匠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异乡人或漂泊者,作者在一开始便交代了他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从城郊墓园到中心街区,从山东巡捕到浦东商人,从老皮匠到小皮匠,“倘若要说明这块方寸之地为什么属于小皮匠,大约就要涉及这近代城市的发展史了”。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在这里并没有按照她以往的惯常路数,不厌其烦地借弄堂旧识演绎都市沧桑,而是以亲切平淡的语调把小皮匠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娓娓叙出。小皮匠从他的皮匠家族那里继承了与这座城市先天的血脉亲缘。皮匠虽然来自乡村,漂泊在街头,“可总也漂泊不出这条街。他已经在这里做熟了,这里的人都是他的老主顾,他不能轻易放弃”。在这种底层生存中,皮匠安之若素,与城市形成了不离不弃的和谐,“皮匠摊设在台阶上退进去的地方,很妥帖也很谐调的样子”,“这条街上的人,也习惯了他的活计,有时候他回乡下去几天,人们就将活计留着,等他回来做,并不会去找隔街的那个皮匠”,“他又不碍事的,各部门对他的驱赶其实也不认真,渐渐地,就形成事实”。王安忆在温暖平淡的叙述中,消解了底层生存的艰辛和粗粝。这一叙述指向显然不是为了追忆这座近代城市的“逝去年华”,而是为了使她笔下人物获取在城市诗意栖居的合理身份,从而使得小说卸去了历史文化的厚重,而具有了日常生活的温暖。
二、都市边缘的尊严守护
乡下来的小皮匠不仅在这座倨傲虚荣的城市里获得了日常生活的温暖,而且还赢得了“尊严”。在日益物质化的城市四处潜伏着欲望的陷阱。生活在都市边缘和底层的小皮匠在欲望的嚣动中守护传统道德,努力保持内心的平静。
康德说:“道德和能够具有道德的人性是唯一具有尊严的。”{2}在他看来,财富、健康、机智等都不能体现人的尊严,因为这些外在的而具有价值的东西并不能把人置于不可替代的地位。小皮匠的尊严首先来自于他对道德的守护。他孝敬长辈,“为了表示赡养的决心”,他毅然把媳妇留在家中,“单身一人”在城市劳碌。他洁身自好,许多女顾客与他“很稔熟”,甚至“有些轻薄”,但是小皮匠则很持重,并不唆。他鄙视城市中的不洁欲望,为此宁可牺牲掉与河南房客那点“五湖四海的友情”。他宁可让他的女人在乡下“耳目闭塞”,也不让她到“大染缸”似的城市来接受“污染”。小皮匠时常站在道德的高处鄙弃城市的阴暗面,甚至对这个“什么都搅在一处,分也分不开”的城市产生“同情”,觉得它是一个“可怜的世界”。显然,小皮匠的精神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屹立在他身后的乡村传统。这在他对城市消费社会的批判中也可以得到确证。“即便是几千块钱的意大利皮鞋,小皮匠都能以平常心来对待”,虽然对名贵皮鞋有时“要格外小心一些”,但他“不是出于对昂贵价格的诚服”,而是出于职业上的“天生惜物”之心。“这种天价的名牌让他觉得造孽”,“他心里有一个底,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怎么说?鞋总归是鞋,总归是要吃力,所以,坚固总归是第一位的”。小皮匠对“名牌”的态度彰显出传统的实用主义心理和对消费社会的批判理性。
只有道德以及为理性所规定的意志才可体现的人类尊严,而意志只有在需要的冲突中才显示出道德性,才具有尊严。小皮匠也有单身的孤寂,“免不了会想起女人绵软的身体”,但他宁可在饮食的“盛宴”中挥霍欲望,也不愿到发廊和足浴房去发泄苦闷。然而,小皮匠还是在城市遭遇了世俗的爱情。他以自己的淳朴善良、知识见地和生命活力赢得了城市女性根娣的青睐。从衣食相帮,到情感相依,再到身体相拥,小皮匠与根娣的情爱在琐屑的日常来往中水到渠成。然而,当“这人生的际遇给了他们莫大的欢喜”时,根海最终用妻子和女儿重新召唤起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主动放弃了与根娣的情爱。小皮匠对城市情爱的回避再次彰显了道德的力量。
“腹有诗书气自华”,知识活动是人类最高尊严的存在。人们常常通过知识获取身份和敬重。小皮匠的尊严不仅来自他对道德的守护,同时还来自于他的知识见地。小皮匠很爱看书,而且“比较广泛”,包括《说岳全传》、《武松》、《资治通鉴》,还有一些《检察风云》、《读者》、《今古传奇》等杂志。虽然这些通俗书刊并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它们同样包含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朴素的人生道理。小皮匠对书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他把书分成古代和现代两种,他认为,“古书里面有很多大的小的道理,大道理是关于世道,小道理则关系做人”,现代的书“说当下的事,可以开眼界,不至于太蒙塞”。小皮匠不但“用心”读书,而且还善于从这些通俗书刊中汲取生活经验和处世道理,“他可以用现代书里的那些人和事来检验古书里的道理,反过来,古书里的道理又可用来解释现代的事情”。小皮匠的知识见地使得他在城里人面前“骄傲”起来。根娣对他的爱慕、小弟对他的佩服和叔爷对他的忌惮都源于此。小皮匠不但在手艺方面与时俱进,而且在精神气质上超越了他的皮匠家族。每一代皮匠身上都脱不了臭味混杂的皮革气味,然而小皮匠却与他的前辈们不同,他身上不但没有“这股皮匠行业的传统气味”,而且在仪表上非常讲究。上班前,他“像一个正规企业里的工人,要换上工作服”;下班后,他又像一个高档写字楼里的白领,穿上西装,戴上领带,用香皂洗了手脸再回家。虽然王安忆时常在城市过往的怀旧中流露出一种文化守成主义色彩,但是显而易见,在小皮匠的“骄傲”里既有来自他身后乡村传统支撑的道德品性,也有来自他面前城市文明陶冶的精神气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骄傲的皮匠》代表了一种新的高度。
三、弄堂人生的世俗拥抱
王安忆在一次讲演中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3}既然筑造小说世界的材料来自现实世界,那么《骄傲的皮匠》是由什么样的材料筑造的呢?
毋庸讳言,《骄傲的皮匠》的材料全部来自弄堂人物的世俗生活。弄堂“是个产生是非的地方”,是都市中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而只有这样的“民间世界”才充盈着丰富的细节和淋漓的生气。上世纪40年代它成就了张爱玲的“传奇”,半个多世纪后,王安忆仍然在这里演绎现代上海的风情。进城皮匠的做活、穿衣、吃饭,下岗女工的逛街、跳舞、打牌,皮匠摊前的风月,麻将桌上的流言,男人间的争斗,女人们的算计……王安忆不愧为编织细节和营构生气的高手,以小皮匠为中心,铺展出弄堂各色世态人情。
既然现实世界为心灵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那么小说家又是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材料,并以此建筑起属于她“个人的心灵世界”的呢?王安忆说:“从现实中汲取写作的材料,这抓住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要领,那就是世俗心。”{4}现实世界是世俗的生活,小说的材料来自现实世界。因而,写作者只有具有了世俗心才能融入世俗生活,才能从世俗生活中“汲取写作的材料”,才能运用这些材料筑造起“个人的心灵世界”。有人说,小说只有“从俗世中来的,才能到灵魂里去”{5}。这多少道出了小说的秘密,越是俗世的越具有真实感人的力量。正是因为王安忆所具有的世俗心,《骄傲的皮匠》才有了俯拾皆是的富有世俗气息的细节和场面,才有了真实生活的质感和触动心灵的感动。
“世俗心”是接近小说的关键,要真正进入小说还需要有“逻辑的力量”。王安忆在谈及福楼拜小说时说,“有时候小说真的很像钟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学,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6}。显然,王安忆在这里强调的是小说要有符合生活的“逻辑”。因为现实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材料通常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7},是无序的,没有逻辑的。这就需要作家根据生活的逻辑去组合和构筑一个“个人的心灵世界”。表面上看来,《骄傲的皮匠》充满了生活的细枝末节,作者的叙述似乎漫不经心,但实际上这些生活的细节都在作者严密逻辑的组织下不蔓不枝。譬如,小皮匠与城市的和谐相处,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必然;小皮匠赢得根娣的青睐,是小说顺理成章的发展;爷叔在金蓉那里遭遇挫折,也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安排。虽然小说是虚构和想像的世界,但是它的虚构与想像必须符合生活的逻辑,否则一切都将会遭到读者的拒绝。
王安忆曾经这样表述她的小说“理想”:“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特殊性。”{8}这一“理想”实际上是小说创作“返璞归真”的最高境界。当一名写作者不再为“某种潮流、某种旗号、某种社会需要而写作”,而把写作当成一种“心灵的需要”,“从内心出发”,为“自我”写作时,生活的“大地”将向他(她)无限敞开。《骄傲的皮匠》代表了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它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是王安忆小说理想的到来。琐屑中蕴涵着丰富,质朴里透露出成熟,作者不再追求叙事的技巧和语言的丰富,而是在平淡朴拙的叙述中从容地完成了语淡意远的风格转向。
作者简介:袁 萍,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 郑媛.借《启蒙时代》远离张爱玲,王安忆称80后都不好惹[N].北京青年报,2007-05-14.
{2}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443.
{3}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43.
{4} 王安忆.导修报告[J].小说界.2006(2).
{5} 谢有顺.小说的物质外壳[J].当代作家评论.2007(3).
{6}{7} 王安忆.小说的当下处境[J].大家.2005(6).
{8} 陈洁.访作家王安忆:写作只服从心灵的需要[N].光明日报.2003-10-11.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