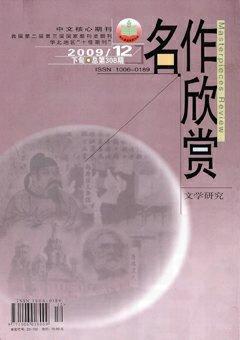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衰老
鲍尔吉·原野是一位蒙古族作家。他的新作《南西伯利亚故事》由一组精短的小说集纳而成,共有七篇。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都比较单纯,甚至有些似曾相识,当代喜弄新潮的作家已经不屑于讲述这样的故事了。不过,艺术的创造往往就是这样,在别人不屑一顾的地方觅得的东西,常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感受。只要能获得灵感的烛照,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衰老。
一、用简朴的故事触动深隐的灵魂
在这组作品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听二人转的狗》中那条小狗福贵的故事。这个故事由三个主要事件构成:第一,福贵是一条流落在国外的小狗,它是被到西伯利亚做工的张福田偷带出境的,“刚来时它小,塞一个地方就入境了。张福田提前回国,把它留这儿了”。第二,福贵曾在楼房失火时从烈焰中救出一个俄罗斯婴儿,并因此获得阿巴干市政厅颁发的奖章。这个事件让人想起中国文学史上诸多的“义犬”故事。跟那些故事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让福贵这次壮烈的义行占据作品的核心,从而避开了一个陈旧的思路。第三,福贵爱听二人转,渴望还乡。它对三个词最敏感:中国、扶余(它在中国的老家)、二人转。“月底我们回国,阿巴干九月份上冻。福贵就得扔这儿,海关不让带毛的玩意儿出境。”这个听到俄语就闹心、时时想着回归故乡的小狗福贵,是永远不可能回家的了。故事讲到这个地方,就打住了。
爱国、思乡,几千年来都是文人们反复吟唱的主题,这个渴望还乡的故事算不上新鲜。但是,故国、故乡在人们精神深处筑成的原型意象,不仅是历久不衰,也是常见常新的,因此离乡背井者的每一个还乡之梦,都会有许多新的内容。特别是古老的还乡之梦由福贵作为主体来承载的时候,新鲜的意趣油然而生。我们的许多梦想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福贵的也是这样。可是,我们明白这一点,明白之后就会放弃;福贵却不明白,因此也不会放弃,它比我们更加痴心,更加忠诚,这样,它的故事才更加让我们感到心酸。
《花朵开的花》,实际上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通过神秘的巫术仪式与祖先遥相呼应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尼玛,他有着突厥人的脸,他的身份是“波”——萨满教的巫师。虽然生长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尼玛与蒙古部族还是有着先天的心灵感应。尼玛一眼就看出“我”的相貌是蒙古人标准长相的一种,断定“我”是朝花可汗的子孙。他给“我”做法时,说“我”死在西伯利亚的先人正赶来,“不排除借我的躯体返回内蒙古这种可能”——又一个渴望还乡的灵魂。透过时间的迷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古代的亡灵寻找家园的身影,还有尼玛本人在异族统治的土地上寻找身份的焦虑面容。另一个是浪漫而凄婉的爱情故事,她的主人公是其其格玛,一个姑娘,一个蒙古部族的后裔,现在西伯利亚的乔巴山市当小学英语教员。她和“我”之间的故事充满浪漫色彩:在尼玛为“我”做法的时候,她一直在一边默默凝望,她爱上了“我”,并找人来相看。当早已结过婚的“我”面对其其格玛和她找来的证人说出“我不娶其其格玛为妻”的时候,她痛哭。“想起别人拉她走,她转头一望的样子,我竟落泪,不知为谁而哭。”
这两个故事表面各不相干,但实际却是相通的,都表达了当代流亡民族强烈的精神诉求:寻找归宿,渴望家园。
《对岸的云彩》所讲的故事比较简单:“我”在美丽的安加拉河畔跑步时,见到一位俄罗斯姑娘,站在山崖上,面向对岸的铁路线,身边有一条黄狗。一列货车开过来,她举起手中的花束向火车摇动,火车也鸣笛致意。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一个偶尔遇到的放牧人告诉我,姑娘是个瞎子,开火车的是他的恋人,一个随时有可能离开的军人。“我”第四天来到山崖下,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境:姑娘这次等来的是一辆客车,姑娘挥动花束,火车却没有鸣笛。以后的两天,姑娘仍然向火车致意,仍然没有得到汽笛的回应。“我”离开克孜勒那天,特地登上那高崖,看到那里有几束枯萎的花束。
这个故事有些似曾相识,以前曾经不止一次看过向火车致意的爱情故事,只是,滋味很不相同。当代,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种纯情的爱恋了。或许,作家正是想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纯情的乌托邦世界已经破碎,就像那些枯萎的花;但是,相信它并寻找它的纯情的人永远都存在,就像那位姑娘。一个虚幻的美丽的世界消散了,寻找者的形象却构成人类生活中一道永远的风景。
《甘丹寺的燕子》、《大清》、《谁是天堂里的人》、《金道钉》分别讲述了信仰、崇拜、欲望的故事,都很精短,也比较简朴。它们跟上述三篇一样,都成功地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那块不易觉察的领地。
我们强调了故事对于小说的意义,但是还必须指出,小说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它讲了什么故事。按照兰色姆的观点,故事只是小说的构架,而小说之所以成为艺术,主要不是依靠构架,而是靠肌质,就是作者在处理故事时增加了的那些东西。
二、人物该如何走进故事?
对于构架与肌质的区别,兰色姆讲得不甚清楚。在我看来,凡是构成“对象”的因素,都是构架,也就是兰色姆所说的“表面的实体”;凡是“程序”的产物,也就是作者在处理这些实体时按艺术规律所营造的一切,都可视为肌质。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属于构架还是属于肌质?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倘若把人物看成一个有确定身份和明确思想的客观存在物,他在小说中就属于构架的范畴。而构成人物血肉的那些独到的性情、感受、幻觉、梦想,那些朦胧而深邃的微妙言语和举止,就应该纳入肌质的范畴了。文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做“形象大于思想”。负责运载思想的故事、景物,就是构架。而表达思想之外种种复杂的意趣,则要靠肌质。构架使逻辑清晰,理性确立;肌质使形象饱满,趣味生成。
比较一下历史的叙事和小说的叙事,就可以比较明白地掌握构架与肌质的区别了。历史是一种构架性的叙事,它注重于“表面的实体”——人物、事件、原因、结果,以及由此概括出来的思想和规律。历史的书写是没有细节的,而且只要人物的性情没有影响到事件的发生发展,就不会顾及人物的性情。小说则是一种肌质性的叙事,它看重的正是历史无暇顾及的微观世界。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历史中止的地方,正是小说起步的地方。
我们强调,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衰老,不是单就故事本身而言。其实,任何故事,如果不赋予它新的肌质,它都有可能衰老,就像祥林嫂所讲的阿毛的故事。必须让人物带着特有的色彩走进故事,他才会为故事带来全然不同的质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福贵是条小狗,但读完关于它的故事,我就一直把它看作一个人物,一个没有被种种扭曲的观念所异化的人物。当老李讲完福贵火中救婴儿的故事,把阿巴干市政厅颁发的奖章戴在福贵的脖子上的时候,“福贵立身,胸前当啷着奖章,眼神无所适从。”显然,福贵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荣誉,它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英雄,它不看重这些。它崇拜母语,渴望回归故乡,为自己的流亡身份所痛苦,有着这样情感的福贵仅仅是一条狗吗?福贵这一形象最动人的一点,就在于它表达了人的基本品性——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和忠诚。
爱情,永远是人性最浪漫最美丽的一面。那位山崖上的盲姑娘向自己的恋人挥动的花束,以及其其格玛的泪眼,都令人感动,因为她们让人想起人类曾经有过的浪漫爱情。她们仿佛是从上一个世纪飞来的天使,在呼唤物欲之外纯真爱情的回归。
如果说上述形象表达了人性本色的一面,《甘丹寺的燕子》中那只会诵经的燕子表达了人的另一基本品性——对神性的崇拜,这一品性为人类超越庸俗的直观生活提供了可能,使人获得信仰和精神追求。对神性的崇拜在《花朵开的花》中有更充分的表达,其中的尼玛就是一位巫师,作品还对他的巫术仪式有直接的描述。巫术虽然是原始的、非科学的,但巫术却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直到现在,还有人认定艺术起源于巫术。尼玛这个形象是带着神秘性、历史性走进小说的。有关巫术,在《金道钉》中也有所涉及:“我太爷安加拉也在找这颗钉子。为此他娶了我太奶奶凯凯,她是茨冈人,会巫术。她说她生下来就知道金道钉在哪里。他们去了她说的地方后,凯凯说沙皇把它换了位置。当然,我太奶奶永远在撒谎,后来被蛇咬坏了左脚的脚趾。”凯凯是罗伯特·休和金为骗钱杜撰出来的人物,她的话是谎言中的谎言。尼玛的话当然也是谎言。但是对待这些谎言,我们不能简单地一味否定了事,因为这些谎言实质上呼应着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我认为,对神性的认同和崇拜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缺少了神性,人类的精神无法飞腾起来。因此现代科学家不相信神,却依然相信神性。
我相信,人物最有魅力的独特之处都源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鲍尔吉·原野让他笔下的人物带着自身独有的色彩进入故事,这就在故事的构架上附上了血肉,故事就具有了新的活力。
三、故事是粮,好的小说要“酿粮为酒”
清代的吴乔在《答万季野诗问》中,把文与诗的体性分别比喻为煮饭和酿酒:“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比喻,在阐释诗的文体特质时十分确切。但他说作文犹如“炊而为饭”,特点是“不变米形”,我认为并不完全如此。以小说为例,现实主义的写法确实有些“不变米形”的特征,而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写法就未必如此了。我认为,好的小说,特别是意图超越生活表象的小说,都追求“酿粮为酒”的境界,包括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
重“反应”还是重“感应”,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创作理念。倘若小说家过于看重对现实生活的“反应”,他的作品就是“不变米形”的。如果小说家是用心灵“感应”生活,他的作品即使形不变,也会有些质变。鲍尔吉·原野是一个擅长感应思维的作家,唯有这种思维,才能保证那些充满迷幻力的情境不会从世上消失。具体说,他添加了三种元素为故事发酵:一是民族历史,它与现实的遥相呼应使作品的内涵变得深远醇厚;二是爱恋情结,包括家国之爱和异性之爱以及二者的结合,爱会使世界染上绚丽的色彩,呈现动人的面貌;三是奇观异象,燕子颂经、巫术拜祖等,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神话性,用纳博科夫的话说,“好小说都是好神话”。
由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迁徙、兼并,蒙古部族的民族发展史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东胡、匈奴、鲜卑,直到成吉思汗统一的大蒙古帝国,这一切又与汉民族的繁衍生息相互缠绕在一起,使得蒙古族的历史具有壮丽、朦胧、深邃、神秘的特点。在鲍尔吉笔下,这些历史的沧桑感每时每刻都在对作品中的现实世界起着发酵的作用。最突出的是《花朵开的花》:
在贝加尔东岸,我见到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波”。
在一座刚建好的喇嘛庙,雪花石栏础和台阶两侧放满信众放的钱币,银光闪闪。停车场上,一个人盯着我看。他有着突厥人的脸——宽脸扁鼻、高颧细眼,这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蒙古人的长相。他前胸一面明亮的铜镜,用绳挂在脖颈上。
我对他躬身施礼,他没理。我改致帽檐礼,他点头,说:“中国海拉尔地方乌里根河的人,都长着你这样的相貌。这是蒙古人标准的长相的一种,朝花可汗的子孙。”
我有受宠的感觉。我近世祖正是朝(chao)花可汗,但我没有去过乌里根河。
这个“波”——就是巫师,测过“我”的生辰八字后,这样描述“我”祖先的历史:
你是黄金家族后裔。十六世纪,你的祖先来到布里亚特,后来到了蒙古国北部,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和我爸说的一样)。你的一位直系祖先在这里给人治病,病死在荒野里(我爸没说过)。他时时刻刻想回去,他知道你来了(我开始紧张),他快要到了,在路上……
在这样的恍惚迷离之中,历史与现实、民族和个人混溶到一起,酿出了一种深沉的品味。故事由现实生活伸展到历史文化,意味着由粮到酒的转变。
鲍尔吉·原野的这些作品中,处处充塞着爱恋情结:爱国、爱故乡、爱民族、爱万物;崇拜谦逊的帝国、崇拜佛典圣灵、崇拜天堂一样的中国;忠于爱情、忠于血统……因为有爱,小说中的人物真实、诚恳、可亲。强丹巴病了的时候,那只通灵的燕子啄他的眼皮,不让他睡,怕他死了。强丹巴说:“动物啊,草木啊,都有灵。你用好念头对它,它就对你好,这是常识。”当下的社会,物欲常常战胜情感,人因此而失去本真。鲍尔吉所讲故事的主人公远离现代化大都市,与遥远的祖先有着心灵的呼应,他们有爱,有赤子般的真诚。有了真诚,也就有了善与美。作者并没有过于宣扬这种本真,但它就像酒中的醇香,让人的心灵微醺。
《南西伯利亚故事》中有一些奇观异象的细节,如小狗的母语情结、大清“火焰珊瑚”般的梦幻之美、关于金道钉的那个虽然虚假却颇具魔力的故事、巫术仪式、燕子点灯与颂经等等。写实与奇幻手法相交织,不仅带给读者新鲜的感受,还能使日常生活与幻境或潜意识之间的界限模糊,而使读者在迷离的梦幻之美感中获得哲理的启悟。韦勒克、沃伦说:“一部小说表现的现实,即它的对现实的幻觉”,“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蒙古族是一个不缺少神话的民族,西伯利亚也是个不缺少神话的地方。从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的心灵史,看到一个作家从另外的角度对现实的透视。
酿粮为酒,是一种升华,是由肉身感知向精神原型的靠拢,是优秀艺术作品获得灵性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孙春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