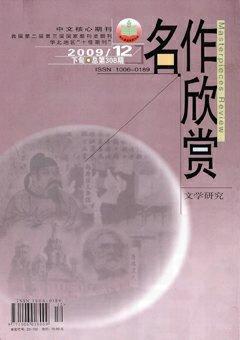十七年文学论争档案(歌词篇)
毛 翰 赵会凤
20世纪初,在旅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倡导下,为效法日本及欧美,进行现代音乐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推动国家进步,沈心工、李叔同等一批词曲作家积极创作,“学堂乐歌”诞生了,中国有了自己的现代歌曲。
学堂乐歌歌词的主题,大致为救国的呼号,革命的鼓动,民主科学思想的宣扬,以及少年壮志的激励。随之而来的是,歌曲创作自觉不自觉地涉及到另外的主题,包括青春的感伤、爱情的咏叹、生命的困惑以及人生和社会的幽怨。这一类主题的名作有李叔同《送别》、黎锦晖《毛毛雨》《桃花江》、吴村《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歌辛《蔷薇处处开》、黄嘉谟《何日君再来》、范烟桥《夜上海》……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歌曲,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为政治宣传,一派为心灵抚慰;一派抒发治国平天下的满腔豪情,一派倾诉拥抱人生的种种柔情;一派风格雄健豪放,放声高唱,一派风格柔媚婉约,浅吟低唱。而不少音乐人身兼两派,如田汉以《天涯歌女》闻名,更以《义勇军进行曲》著称,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声名远播,其《清流》也不胫而走。
1949年以后,以《东方红》和《解放区的天》为代表,来自红色根据地的宣传歌曲、革命歌曲,以胜利者的姿态,迅速占领了整个中国内地。《夜上海》的柔媚婉约之歌,则作为靡靡之音被扫荡殆尽。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的黎锦晖,1958年撰文《斩断毒根彻底消灭黄色歌曲》①,挥刀自宫。
整个“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内地歌坛几乎是宣传歌曲的一统天下,颂歌及战歌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与宣传口经稍有不合的歌词,立即会受到质疑和批判。歌风稍一柔婉,个性稍一显露,即难逃讨伐和封杀。
一、颂歌也被质疑
那是一个以颂歌为尚的时代。新政权的诞生,给了人们无限的希望和遐想空间,在政治意识的强力引导下,颂歌不断地涌现。即便反右的肃杀、大跃进的挫败和三年饥饿的悲苦,似乎都不曾让词家的浪漫情怀稍有降温。《歌唱祖国》、《浏阳河》、《社会主义好》、《听话要听党的话》、《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我们走在大路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联翩而至,各领一时风骚。②
不过,颂歌的创作也得格外小心,满腔热情的赞颂,杜鹃啼血般的献歌,有时也可能被指调门不够高亢,腔调不够纯正。
蔡庆生等:《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
我是保卫和平的哨兵,
守卫在朝鲜前线的山峰,
两只眼睛注视着分界线的南面,
我的心和祖国人民一起跳动。
和风吹过了大地,吹过了我的头顶,
风啊,请你停一停,
请你告诉我,你可是来自北京?
你可见过毛主席?你可见过朱总司令?
你可见过辛勤劳动的祖国人民?
和风吹过了大地,吹过了我的头顶,
风啊,请你停一停,
请你告诉我,你可是来自北京?
你可带来生产的捷报?你可带来丰收的喜讯?
你可说得清祖国建设的美好情景?
和风吹过了大地,吹过了我的头顶,
风啊,请你停一停,
请你告诉我,你可是来自北京?
你可带来母亲的欢笑?你可带来父亲的嘱托?
你可带来祖国孩子们幸福的歌声?
快快告诉我吧,来自祖国的风!
你今天说不完,我明天继续听,
我渴望着知道,祖国的每一件事情。
1954年3月7日,志愿军战士蔡庆生的诗《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发表于《人民日报》,并获志愿军文艺创作一等奖。旋即由晨耕、管平改词,晨耕谱曲,发表于1954年8月出刊的《歌曲》总第13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之播唱。
《人民音乐》1955年第1期发表泽民《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意见》,认为“这个歌不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而是一种潇洒无事的媚音,只是灌输了和平麻痹思想,消失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的警惕性”,“它所给我们的意境和形象,是旧社会里的学生形象,在月下垂柳河旁,发挥自己的情感,我认为它正是富于这种人情味。它不是工农出身的战士的感情”,“是把人领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深渊里去的”。(此文多语病,照录。)
接着,该刊第2期又发表戈风《“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不是一首好歌》,文章指出:“这样迎风望月感慨万端的情绪是低沉的、消极的,这完全不合乎手执武器面对敌人斗志昂扬情绪乐观高唱战歌气魄雄伟的志愿军部队和革命战士的精神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吟风弄月触景伤情式的思想情绪”,还说:“战士怀念祖国和亲人的情绪,可能向消极方面发展成为思乡的落后思想。”
面对这种批评,管平,歌词修改者之一,立即表示:“硬把志愿军战士热爱祖国怀念祖国的情感,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消极低沉的感叹,这是毫无根据和毫无理由的。”③
1955年第4期《人民音乐》发表“本社编辑部”整理的《读者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意见》,指出“在读者意见中,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大多数都表示了肯定的意见,认为它基本上是一首比较好的部队抒情歌曲”,“也有较少数的人发表了和上面相反的完全否定这个歌的意见”。
随后,该刊第5期,发表刘兆江《我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意见》:“我们看到了一种极端的意见,认为它是一首很坏的歌。说它是一种媚音,只灌输了和平麻痹的思想……我认为这样的意见是过火的。”
同期还刊登《读者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意见(续完)》。文中介绍,解放军某部郑逢的意见是:“过去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把战士的思想情感理解得过于褊狭与刻板,好像战士只能练兵打仗,不容许有普通人一样的思想活动,否则就是歪曲了战士的伟大品质……”玲军指出,“有的人一听到比较柔和、深沉的曲调,还没有来得及加以分析,就简单地认为不健康、带有小资产阶级情绪,几年来我们抒情歌曲的落后状态不能说与这种批评无关。”蔺四说:“泽民同志根据自己对战士、对祖国人民生活‘公式化的要求就把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扣住了这首歌,从而根本否定了它,这是不好的。”天津解放军某部王觉则坚持认为:“‘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就是脱离了志愿军这种特定的人物的特定的处境和他所担负的斗争任务,而硬要叫他在欣赏‘和风大地的情况之下怀念祖国,这当然就会造成一个不真实的意境和不健康的形象。”
鲁藜:《我爱北京》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爱你的清晨,爱你的黄昏。
爱你的天上星星千万颗,
爱你的云霞飘落水中。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爱你的庄严,爱你的芬芳。
爱你的花园里花儿千万朵,
爱你的红墙上红旗飘扬。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爱你的辽阔,爱你的深沉。
爱你的湖上船儿满载着歌声,
爱你永远向着理想前进。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爱你的清晨,爱你的黄昏。
爱你的钟声永远呼唤着东方,
爱你的灯塔万丈光芒。
此词发表于1954年10月号《歌曲》,舒模曲。不久,“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鲁藜身列案犯,言因人废。
1955年9月号《歌曲》发表一封“读者来信”,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萧道霖,题为《鲁藜“我爱北京”一歌的恶毒目的》,指其歌词中“尽是些……空洞的词句”,“这和旧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歌颂词是完全一样的”,“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祖国的心脏,也是东方和平的堡垒,在那里住着我们亲爱的领袖毛主席,住着我们的党中央。这才是全国人民所深心热爱的主要方面”,“可是胡风分子爱的是什么?他们喜爱北京吗?不,他们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他们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灭亡‘完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人民日报编者按),他们是完全不爱北京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能写出对祖国首都的伟大和美丽的热爱,而只能写出那些空洞的歌词来”,“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在这样歌词的后面,隐藏一个恶毒的目的。就是他企图引诱我们去爱那些空洞的‘清晨、‘黄昏、‘辽阔、‘深沉。这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挖心战术。”
这封读者来信的“编者按”写道:“胡风反革命集团为了扩大他们的阵地,曾从各个角落来进行对革命的‘挖心战,音乐领域也是他们不放松的一个方面。如鲁藜、绿原、冀等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就曾写过不少的歌词,借歌颂之名而实质上宣传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想情绪。”
石汉:《太阳啊!你再照照我》
太阳啊,你再照照我,
高山啊,你再看看我,
志刚哪,你不要想我……
多少美景我还没看够,多少事情我还没做,
天寒地冻盼日出,人到死时仍想活。
薄雾延绵绕群山,朝阳遥望凤凰岭。
天下景物有情意,红霞更知爱人生,
荣华宝贵我不喜,喜的青山和翠林。
爹娘生我两只手,敢劈山来能绣花,
我把青春比光明,断头流血不悲痛,
但愿山里人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
1958年上映的电影《红霞》,是依据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创作、演出的同名歌剧所拍摄的,讲述的是江西苏区赤卫队长赵志刚和未婚妻红霞,与敌人殊死斗争的故事。其中这首插曲是红霞英勇就义前所唱。
《人民音乐》1960年第10期发表张程万《这首歌缺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歌剧“红霞”中“太阳啊!你再照照我”的意见》:“在这首歌曲中,我们感觉不到一种为革命捐躯的自豪的情调,悲怆的基调掩盖了烈士英雄主义的光辉”,“在革命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献身,而不会缠绵悲切地唱:‘人到死时真想活。这是资产阶级渺小的个人的生存欲望,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此后,该刊1961年第3期发表山西长治淮海技工学校竹兰《〈太阳啊!你再照照我〉无损红霞的英雄形象》,为之辩护:“‘人到死时真想活,这并不是红霞不愿意牺牲自己。这是因为她觉得她应该坚持下去,多活一些时间,多为人民立功效劳。这种革命英雄主义是不能不为后人所尊崇的。”
指控之辞的偏执,辩护之辞的拘谨,都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希扬:《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说得到,做得到,
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
坚决跟着共产党,
要把那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
人民江山坐得牢,
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
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
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
李焕之作曲,发表于1957年8月号《歌曲》。其问世的背景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这里收录的是其1965年的修订稿。“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一句,原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不料,这样一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赞歌和信念之歌,竟然也遭遇过尖锐的质疑。1965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学生杨桂元的检举信《〈社会主义好〉有严重问题》,原来,“这些歌词使我们感到,帝国主义被我们赶跑了,反动统治阶级被推翻了,我们只要坚决跟着党,团结一致,搞本国建设就行了,因为‘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共产主义就一定能实现。这种提法,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注意进行本国建设,本国的革命事业就不会顺利前进;忘记了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很容易陷进民族利己主义的泥坑”,“《社会主义好》根本不提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只抽象地提了‘人民江山人民保,而更多地宣扬了阶级敌人已经被打倒,被推翻,阶级敌人反不了我们的江山,这就在客观上起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的作用”。
郑洪等:《送别》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
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间屋前川水流,革命的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梭镖望君还。
这是1963年上映的电影《怒潮》的插曲之一。《怒潮》表现的是1927年“马日事变”后,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武装暴动的故事。
《人民音乐》1964年4月号转载《电影艺术》发表的韶文《谈〈怒潮〉中的三支歌曲处理》,该文完全肯定包括《送别》在内的《怒潮》中的三支插曲。同一期发表的关于《怒潮》插曲的两篇文章,一篇肯定电影《怒潮》而批评《送别》“缠绵悱恻”、“情绪压抑”,“和影片风暴式的、怒潮似的革命基调脱节”(傅伯元《电影〈怒潮〉插曲——〈送别〉是一支好歌吗?》)。另一篇肯定《怒潮》中另两支歌“写得好”,批评《送别》“过分地强调哀伤、缠绵之情,使人感到压抑、无望,反映不出群众当时存在的那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陶克《听〈送别〉所想到的》)。
之后,该刊5月号发表北京一名小学音乐教师谢白倩《一个教师的意见》,指出“在电影《怒潮》中《工农齐武装》、《一支人马强又壮》这两首插曲,对青少年会有良好影响,但是《送别》这首歌,就未必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其“音调未能准确深刻地表达出当时人们对革命的心情,而更多地用了缠绵、哀怨、凄凉的音调。我觉得这和影片的革命性、战斗性格格不入。有些人唱这首歌精神上松松散散,显得疲惫无力”。
接着,该刊又在6月号发表了向异《关于〈怒潮〉的歌曲》一文,肯定这首歌“流畅婉转中显得朴素,含蓄平稳里略觉沉重”,“并没有感到它是哀怨、伤感”。不过,“歌词却以‘你、我相称”,“就使人产生词意与影片的规定情景脱节的感觉,甚至于把它看作是一首情歌”。
此后,批判升级。《中国青年报》1964年11月17日第3版载文,题为《〈送别〉是一首必须批判的坏歌》:“哪里有一点点革命气息!又哪里有一点点革命激情!”“还有的青年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比较浓厚,因而对像《送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这样一些以‘友谊、‘爱情、‘幸福为诱饵,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情调的歌曲,容易产生共鸣,发生兴趣”,“总之,我们认为《送别》不是一首好歌,不是一首革命的抒情歌曲,而是一首灰色歌曲,是一首披着革命外衣来抒小资产阶级之情的坏歌”。
1966年初,《怒潮》被打成替彭德怀翻案的“反党影片”。《怒潮》编剧之一,《送别》的歌词作者郑洪(1928~1968)被迫害致死。
二、柔情即是异端
“文革”前十七年,艺术被要求为政治服务,包括歌词在内的各种艺术都被要求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思想教化的工具。除了颂歌、战歌,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唱中心,许多词作家已不知道自己还能写什么。
1953年,贺绿汀在中国音协作了《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④的发言,指出:“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所有的抒情歌曲都归到小资产阶级一类去。我们的创作不应该仅仅是粗糙的叫喊,而应该是音乐,是诗。”为此,《人民音乐》1955年第3期发表社论《更深入更全面地联系实际,对音乐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展开彻底的批判》,并连续发表20余篇文章,对贺绿汀进行围攻。1957年5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旧歌重放音乐会,引起了持续一年多的批判‘黄色音乐的活动”⑤。
于是,人们视抒情和艺术个性为畏途,创作更加公式化,“主旋律”之外,别无创作空间。于是,像《敖包相会》、《蝴蝶泉边》、《婚誓》等,不大能配合政治宣传,不具备武器作用的情歌,受到质疑,就是必然的了。像《拂晓的灯光》⑥、《九九艳阳天》、《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⑦等,意欲别出心裁,融柔情于主旋律,配合得不大规范的,被人指斥,并不奇怪。
胡石言、黄宗江:《九九艳阳天》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
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依呀呀地唱哪,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想把军来参,
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哪,
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
风向不定(那个)车难转哪,
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告诉小英莲:
这一去翻山又过海呀,
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
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
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细听我小英莲:
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
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
啊,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呀,
等待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
此系1957年上映的电影《柳堡的故事》(胡石言、黄宗江编剧)插曲,高如星作曲。歌词清新上口,曲调委婉动人,深受听众欢迎。并引发热烈的讨论,仅《人民音乐》1958年第3-6期发表和转载的关于《九九艳阳天》的论争文章就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我喜欢“九九艳阳天”》、《不应该过分推崇“九九艳阳天”》、《战士喜爱“九九艳阳天”》、《我们这里不喜欢“九九艳阳天”》、《“九九艳阳天”过于缠绵》、《“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很健康的歌曲》、《“九九艳阳天”的创作方向值得研究》、《“九九艳阳天”不适宜给青年人唱》、《“九九艳阳天”唱起来劲头不对》……
有人称赞它“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情绪”⑧,有人赞许它“所以能吸引人,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具有优美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民歌风味”⑨。
否定的意见则认为,它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软绵绵的不够健康的情绪”,“好像是又听到了解放前扬州姑娘卖唱时的那种扭扭捏捏的音乐格调,也想到了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二者在旋律的装饰上很相似”(《人民音乐》1958年第3期,李桂芬《唱“九九艳阳天”有感》)。它“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粉红色的爱情幻想”,“迎合了很多青年的不健康情绪”(《人民音乐》1958年第4期,邓映易《我们应当把什么样的歌曲给青年》)。
《人民音乐》1958年第4期发表孙世琦《驳李桂芬的“唱‘九九艳阳天有感”》,第5期则发表胡国强《不能同意邓映易的意见》。
《北京日报》1958年3月28日发表李凌《从“九九艳阳天”谈起》,认为不少青年对《九九艳阳天》这首歌无限迷恋,而对《社会主义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则不爱唱,这种情况是不大正常的。
在1958年4月24日《北京日报》上,瞿希贤《什么是音乐生活的主流——也谈“九九艳阳天”》一文写道:“我认为‘九九艳阳天是一首比较成功的爱情歌曲,这首歌曲的情调是委婉动人的,旋律比较优美,并且有令人感到亲切的南方民歌的色彩。”不过,她主张:“我们歌唱生活的主流,应该是直接鼓舞干劲、令人情绪奋发的歌曲。”
同年,《大众电影》第8期发表李焕之的旗帜鲜明的文章《“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好歌》:“‘九九艳阳天这么快流传开来,因为它是一首好歌”,“‘九九艳阳天和‘天涯歌女不能比的。‘天涯歌女是那么哀怨、忧伤,而‘九九艳阳天是那么明朗、乐观”。此文一出,又招来伍雍谊《抒情歌曲的创作要不要继承与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传统?——对李焕之同志关于“九九艳阳天”一文的商榷》⑩。
《人民音乐》1959年第1期发表其“本刊编辑部”的文章《提高理论水平巩固音乐文化新的发展》,判定《九九艳阳天》“格调不高,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反复刊印和广播)大量加以推广”,试图亮起红灯,结束争鸣。
不料,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言九鼎:“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红灯转绿。
待“文革”爆发,罗瑞卿失事,《九九艳阳天》终于被禁。作曲家高如星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年仅42岁。
潘文林、郭颂改编:《丢戒指》
姐呀儿花园中绣丝啊绒啊依个呀儿呦
来一个蜜蜂儿它螫我的手心呀
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嗯哎哎嗨呦
金戒指啊不哇是啊值呀钱的宝哇依个呀儿呦
那本是我那个情郎哥儿给我买的呀
一钱得儿零三分儿啊嗯哎哎嗨呦
要哇是啊老头捡哪了哇去呀依个呀儿呦
请到我的家中啊赴上酒席儿呀
我情愿认个干亲戚儿啊嗯哎哎嗨呦
要哇是啊嗨小伙儿呀捡哪了哇去呀依个呀儿呦
要什么礼物我都乐意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呀依个呀儿呦
由东北民间小调改编的《丢戒指》,表演的是一位姑娘因故丢了金戒指,情急之下,顾不得害羞,道出原委,许以重酬,希望失而复得的故事。1953年在东北三省音乐舞蹈汇演中,郭颂的演唱即受到马可、劫夫等的好评。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更产生轰动效应。这首歌受到批评则在1959年。
在《人民音乐》1959年第4期“各地展开有关抒情歌曲问题讨论”的专栏下,黎民《“丢戒指”还有可取之处吗?》一文认为:“‘丢戒指不能算是毒草,也不能和黄色歌曲并列在一起,但也不能说它是一首理想的好民歌;应当说这首歌曲,在格调上和趣味上都是不够高的,我想不能因为格调不高就去禁演它;另外像这样的歌曲也值不得大灌唱片,到处宣扬和介绍。”另一篇署名影子的文章《“丢戒指”是不健康的》则指出:“‘丢戒指这首歌词,它不是劳动人民爱情生活中的真挚感情,而是反映了‘贵族小姐、‘花花公子的小市民式的低级趣味。‘丢戒指在个别场合也获得了一些掌声,那只能说迎合了一些‘小市民和‘无聊者的低级趣味罢了。”
同年,其他同类刊物也对此歌展开了论争。
《黑龙江歌声》3月号发表白海、吴影的文章《这是一首坏歌曲》,称之“只不过是无聊的贵族小姐和小市民的庸俗趣味的蒂合罢了”。
《劳动歌声》3月号发表火夫《试谈“丢戒指”和“看秧歌”》:“这些歌到底给观众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些什么有益的东西呢?!可以说没有多少,他们只会感到这些歌的空虚和无聊。”
也有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此歌。《群众歌声》第6期发表万苇舟《为“丢戒指”说几句》,称“不同意程瑞征文章中的‘内容是太无聊了,感情和趣味是太低级了,‘轻佻和调情,‘嬉皮笑脸、油腔滑调充满了全部作品等等说法”,认为“它虽不能鼓舞人们的战斗情绪,但它还是可以给人们一种比较明朗和愉快的感受的”。
随后,《音乐研究》1959年第5期刊出《关于〈丢戒指〉、〈小燕子〉、〈七女夸新郎〉、〈十绣〉等歌曲的讨论》,发表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1959年8月11日、12日两次专题讨论上的发言。关于《丢戒指》等,宋扬说,“我们不要把喜爱这些歌曲的听众都说成是‘螫手心迷,‘十八岁哥哥迷,应该承认大多数群众所喜爱的原因是正当的”。时乐则以为,“《丢戒指》无论是歌词或者音乐形象都不好,趣味低,最后一句‘就是不能拜天地更是人为的。”高介云表示,“《丢戒指》、《小燕子》这几首歌曲不宜推广”,“报刊上对这几首歌曲可以提出批评,指出其缺点,引导群众加以鉴别”,“但是也不一定要给戴上黄色的帽子”。万苇舟说,“有些同志批评《丢戒指》没有大跃进时代的情绪,我认为对一首旧民歌不能这样要求”。杨荫浏主张,对于民歌,“我们还是郑重一些,了解、研究在先,批判在后”。李伟声称:“《丢戒指》这首歌,我个人不喜欢,因为它风格不高。像‘螫手心、‘干亲戚、‘拜天地等,趣味是很低的。当然,还不能说它是‘毒草,它和《满洲姑娘》、《何日君再来》还不同。”马可说,“有些人说《丢戒指》涣散人民的斗志,歪曲现实,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民起毒害作用。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它的缺点是风格不够高,格调不够高……”
雷振邦改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花儿为什么这样鲜?
为什么这样鲜?
哎,鲜得使人,鲜得使人不忍离去,
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作曲家雷振邦1961年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的插曲之一,据塔吉克民歌改编。1963年随着影片公映,广为流传。
这首歌先是受到赞誉。《光明日报》1963年10月10日发表黄沫《一部有特色的反特影片——看〈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影片在运用音乐来帮助表达剧情和人物感情方面,效果很好。留给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经过改编的民歌。”《大众电影》1963年10月号发表王大启《简谈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表现手法》:“姑且不说它是如何悦耳、优美、抒情,单就它与整个剧情发展的关系来看,确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影片里这样运用歌曲,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不久,批判之声便不绝于耳。
《人民音乐》1964年第Z1期,任加《抒社会主义之情——从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谈起》:“这支歌的精神境界是比较狭窄的”,“唱了之后,只能使人陷入消沉、迷惘之中,丝毫不能激起人们积极向上的情绪”。
同期,李民《要使人捏紧拳头不要使人耷拉下脑袋——谈电影歌曲创作》进一步指出:“其主要问题,正在于歌曲本身在思想感情的表现上存在缺点,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消极不良的影响”,“加工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仍是一首忧郁感伤、时代感很不鲜明的情歌。将这样的歌曲通过电影向群众推广,显然是不适宜的。”
之后,在《中国青年报》开展的“我们要唱什么样的歌曲”的群众性大讨论中,此歌再受冲击。有文章指出,“整个曲子的感情格调十分低沉、压抑”,“而不稳定的装饰音”“却会造成‘哭泣的效果,增加了音调的不健康因素”,“转弯抹角的旋律底下是稀稀拉拉的歌词音节,听起来缠绵悱恻,情绪压抑”,“这首曲子‘软绵绵的性格正说明了它抒的不是解放军战士之情,不是革命青年之情,也不是少年阿米尔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之情,而是迎合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的感情”(《中国青年报》1964年10月13日第4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曲宣扬的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另有文章认为,“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种坏歌,所散布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是和我们今天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志在四方,献身于壮丽的革命事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的革命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和这些坏歌的情调有所‘合拍,就要认真检查一下原因,对自己的艺术趣味来一次革命”(《中国青年报》1964年10月13日第4版《电影歌曲也要政治标准第一》)。
继而,《歌曲》1964年第12期刊载了《中国青年报展开“我们要唱什么样的歌曲”讨论情况综述》一文,文中指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一首情调不健康的歌曲,它与促进青年无产阶级革命化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一种腐蚀剂”,“在披着抒革命战士之情的名义下,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哀伤情感”。
1965年6月19日《工人日报》发表马克《怎样对待抒情歌曲》,文章宣判:《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送别》“就是有严重错误的抒情歌曲”,“没有把时代的革命精神表现出来,而是抒发了一种庸俗的、萎靡不振的,充满感伤和顾影自怜的不健康的情绪”。
金波:《在老师身边》
自从踏进学校的门槛,
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
从一个爱哭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
虽然离开了妈妈的怀抱,
红领巾却抱着我们的双肩,
这一点一滴的进步,
花费了老师多少的血汗。
记得有多少晴朗的白天,
我们和老师漫步在校园,
我们谈生活、谈理想,
也谈那无限美好的明天。
还有多少寂静的夜晚,
老师的身影还印在窗前,
她为我们一点点进步,
竟会兴奋得忘记了睡眠。
将来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要走得很远很远,
告别了亲爱的老师,
告别了我们熟悉的校园。
带着老师深切的期望,
去把少年时代的理想实现,
到那时候我们的思念,
还会飞到老师的身边。
1962年问世的这首歌词,由黄准谱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唱,旋即收入小学音乐课本,流传久远,有的学校把它当“毕业歌”,在毕业典礼上演唱。
《山东教育》1964年第11期发表禹城县大李店小学姜步云《这支歌有资产阶级母爱观点》,《歌曲》1965年第2期转载,该文写道:“只是一味地歌颂老师的‘功绩,夸赞老师的恩情。这岂不是资产阶级‘母爱教育在作怪吗?”
《歌曲》1965年第2期还发表益都一中景传贵、潘才秀《〈在老师身边〉宣扬了什么》,指控“在这首歌词中看不到党的作用,看不到对党的感情”。该文还指出:“我们认为歌词的情调也是不健康的。如果不以政治挂帅,不围绕着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这一种新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一味的高谈阔论,就会把学生引入歧途”,“这首歌宣扬资产阶级‘母爱思想,是应该进行批判的”。
[意]皮阿维:《饮酒歌》
让我们高举起欢乐的酒杯,
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
这样欢乐的时刻虽然美好,
但诚挚的爱情更宝贵。
当前的幸福莫错过,
大家为爱情干杯。
青春好像一只小鸟,
飞去不再飞回。
请看那香槟酒在酒杯中翻腾,
像人们心中的爱情。
啊,让我们为爱情干一杯再干一杯!
在他的歌声里充满了真情,
它使我深深地感动。
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欢乐,
我为快乐生活。
好花若凋谢不再开,
青春逝去不再来。
在人们心中的爱情,
不会永远存在。
今夜好时光请大家不要错过,
举杯庆祝欢乐。
啊,今夜在一起使我们多么欢畅!
……
这首《饮酒歌》作于1853年,是意大利歌剧《茶花女》里的一首名歌,在该剧第一幕里,男女主人公在宴会上举杯对唱,相互表达爱慕之心。
1958年,音乐出版社推出《外国名歌200首》,1959年推出其续编。分为“现代创作歌曲”、“各国民歌”,以及“欧洲古典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曲”三部分。《饮酒歌》即在其中。
《中国青年报》1964年9月5日第四版发表韩昭、陈良的文章《〈外国名歌二百首〉散布了什么影响?》,指控“《外国名歌二百首》及其续编的出版,向一部分音乐爱好的青年,散布了许多资产阶级思想毒素”。
该报同日同版发表石云《〈饮酒歌〉这类“名曲”是什么货色?》称:“剧中高唱《饮酒歌》的都是些狂歌滥饮的嫖客和妓女,歌中宣扬的爱情至上和及时行乐的调调儿怎么能吸引我们一唱再唱?”“这绝不仅仅是个人喜欢唱什么歌的问题,而是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让我们将思想武器磨得更锋利,坚决抵制和批判那些有害于社会主义,有害于青年革命化的坏歌曲。”
《人民音乐》1965年1月号发表北京大学学生孙树的批判文章《毒害青年人的〈外国名歌200首〉》:“有那么一长段时间,两本手册型的歌本在部分青年中很受钟爱。他们一有闲空,就捧起歌本吟唱:‘青春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这两本歌集虽然介绍了一些外国优秀歌曲,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大量的饱含毒素、糟粕的歌曲充斥其中,谬种流传,几年来我们青年不少人受到它的毒害和腐蚀”。
《人民音乐》同期发表的游忠的文章《〈外国名歌200首〉宣扬了什么?》认为,集子中的许多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宣扬了阶级调和的思想”,“宣扬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表现了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感伤颓废的思想”,“宣扬了宗教迷信,歌颂了上帝、圣母、耶稣、天堂”。而《饮酒歌》这支“喧闹、狂热的圆舞曲把这种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情调渲染得绘声绘色。‘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快乐,我为快乐而生活,这正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哲学。”“我们有些同志把这样的段子单独抽出来,作为‘世界名曲而着力推荐,只能产生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志的作用。”
三、结 语
《东方红》原本是一首极普通的“哥哥”“妹妹”式的陕北情歌,其词云:“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取其曲,剔其词,改填为政治颂歌,颁行天下,然后宣布所有的情歌都是资产阶级情调、低级趣味,都在取缔之列。这不免有点滑稽。(饥者歌其食,鳏者歌其妇,情歌更属于娶不起媳妇的穷汉,而不是妻妾成群的富翁吧。为什么不说情歌表现的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情调,却说是资产阶级情调呢?这句套话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事实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歌曲的两大流派,激励斗志与抚慰心灵,抒发报国豪情与倾诉人生柔情,豪放之歌与婉约之歌,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原是互为补充,不可偏废的。1949年以后,这两大流派被一扬一抑。扬的是不无扭曲的政治的宣传,革命的鼓动,抑的是关于人生情怀的缠绵和感伤。十七年关于歌曲歌词的许多论争,其实只是在做着这么一件一扬一抑的事。
当一幕一幕的政治斗争让人们日渐倦怠,当“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让人们日渐疑惑,当人生的浅吟低唱被狠揭猛批,一一查禁,一个时代的歌儿,还剩下几首可传,几首可唱?当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批判,弄得最后,只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批判的价值究竟何在呢?
十七年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文革”,“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被荡涤得更为彻底,颂歌和战歌更加声嘶力竭,史无前例的语录歌也极盛一时,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非鳏即寡,爱情友情亲情一脉的歌咏更恍如隔世。稍稍像样一点的文艺批评和论争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些红卫兵式的口诛笔伐胡搅蛮缠贻笑天下。例如,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只因其中有一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竟被指为“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11}。有一首《马儿啊,你慢些走》,写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1年:“马儿啊,你慢些走喂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批判者不批其谀上欺世、粉饰太平,却批其“与大跃进运动唱反调,要让革命人民跨上了大跃进的千里马‘慢些走,用心何其毒也!{12}”又据说,马玉涛出国献歌,也不让唱这一首,原来,那里也在搞“千里马运动”,也容不得马儿慢些走呢!
作者简介:毛 翰,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赵会凤, 华侨大学文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① 原载《人民音乐》1958年第3期。
② 参见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漓江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
③ 管平:《关于戈风同志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批评的几点意见》,《人民音乐》1955年第2期。
④ 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人民音乐》,1954年第3期。
⑤ 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年鉴》1987年卷,第469页。
⑥ 《拂晓的灯光》,张明权词、瞿希贤曲,1955年问世。歌中唱道,一位老干部夜读《炼钢学》,睡着了,“我”给他轻轻披上大衣。有人批道,这里抒发的“不是老干部之间而是爱人之间的感情”。
⑦ 《草原之夜》,张加毅词,田歌曲,1959年问世,电影《绿色的原野》插曲。被批为“一首精神空虚歪曲草原建设者形象的哀怨之音”。语出《中国青年报展开“我们要唱什么样的歌曲”讨论情况综述》,《歌曲》,1964年第12期。
⑧ 澎潮:《谈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人民音乐》,1958年第3期。
⑨ 沈宝泰:《我喜欢“九九艳阳天”》,《人民音乐》,1958年第4期。
⑩ 《人民音乐》,1958年第5期。
{11} 参见樊星主编:《永远的红色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12} 转引自谢嘉幸:《旋律神韵、原生态与民族精神》,《人民音乐》,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