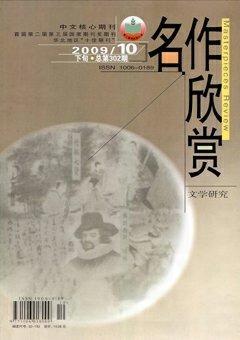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我者”与“他者”
史 敏
关键词:莫里森 身份 自我 他者
摘 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里·莫里森已成为当今美国黑人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关注种族歧视的同时,作家开始审视性别问题给女性造成的身心创伤,并通过人物塑造、话语结构和多声部叙事探讨黑人女性身份的建构和发展,力求超越他者与我者对抗的立场,解构白人权力话语的神话,摆脱黑人女性无言或失语状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话语观,代表了黑人女性文学的新走向。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 1931- )已成为当今美国黑人文学的领军人物,她的小说题材全部取材于美国黑人生活,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不胜枚举。迄今为止,莫里森已经发表了八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秀拉》(Sula)(1973),《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柏油娃》(Tar Baby)(1981),《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2),《天堂》(Paradise)(1998)和《爱》(Love)(2003)。1988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宠儿》更是被改编成电影,由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Oprah Winfrey)饰演女主角塞丝。她还于1993年发表了一本文学批评专著《黑暗中的游戏》(Playing in the Dark),斯坦纳(Wendy Steiner)在评论《黑暗中的游戏》时指出:“莫里森以一个女性和一个黑人的身份说话,恰恰强化了她以一个美国人身份说话的能力。”①莫里森在小说和著作中努力构建女性的叙事声音,展现黑人女性在充满敌意的美国白人社会中如何发展自我,实现她们的主体性。
一、寻找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
从哈莱姆文艺复兴到20世纪60年代,在关注种族歧视的同时,黑人女作家开始审视性别问题(gender trouble)给女性造成的身心创伤。莫里森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她的八部小说中,寻找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成为莫里森的母题研究,她巧妙地将非洲民族的原始图腾和神话仪式与黑人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寻求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写作模式,重构历史,在现实和想象的世界中自由地穿梭。
《最蓝的眼睛》颠覆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广泛流传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童话,指出黑人小女孩永远也无法变成白人文化中美丽的“白天鹅”。《秀拉》填补了黑人女性成长小说的空白,只是成长中的秀拉是走向毁灭的。《所罗门之歌》使用民间传说黑人会飞的神话来支撑整部小说的结构,奶人从北方的城市来到南方的乡村寻找自己的家族之根和民族之根,从而认识了自我,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柏油娃》直接取材于非洲的民间传说,男女主人公黑白文化碰撞与冲突也颠覆了西方传统中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宠儿》讲述了类似哥特式的鬼故事,一个离奇的魔幻现实主义故事,着力表现了黑人的精神世界,被践踏的人格与被戕害的心灵。杀婴事件的影响通过多声部文本展开散播于小说中,而宠儿的身份又采用多重不可靠叙述文本的建构原则,叙事的同时让读者参与故事的建构,给读者提供了多元化甚至是无穷的解读的可能性。《宠儿》《爵士乐》和《天堂》构成了一个“三部曲”,是莫里森对百年来黑人的历史所作的梳理和挖掘。莫里森在《爵士乐》中采用了多重视角的复调叙述,而其中叙述主体对人物语言原话直录,这些用引号括起来的直接引语恰似爵士乐中的独奏。《天堂》模仿了白人的建国神话,指出人类的天堂应该建立在谅解与容纳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追求一个绝对理想化的世界,理想化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爱》以“碎片化”的叙事继续了莫里森对黑人作为“他者”在美国的处境的思考。但她将爱置于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获得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新认识。
除了《所罗门之歌》之外,其余七部作品都是以黑人女性为主人公,而《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女性派拉特也引领了奶人的精神成长,莫里森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对黑人女性自我的不断拓展和其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进行了探讨。黑人女性究竟是谁?她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给她们带来怎样的精神戕害?如何在作品中建构她们的主体意识?黑人女性理想的“天堂”到底在哪里?
二、发展中的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
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突进宏大的历史叙事内部,通过主体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去发现历史盲区,权力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找寻。黑人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莫里森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运用多视角和多声部的表现策略,穿越历史和现实,运用独特的语言、符号和意象来记录女性的生活,让她们逐渐掌握话语权力,讲述自己的历史,建构自己的故事。黑人女性在寻找自我身份和地位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女人,还是人,是美国人。
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对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春、夏、秋、冬的创作原型进行套用和改造,作品分“秋、冬、春、夏”四章,克劳蒂亚通过对这四个季节的回忆,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莫里森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来凸显主人公黑人小女孩佩科拉走向疯狂的命运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出白人强势文化导致黑人女性的自我憎恨。莫里森选择了最脆弱、最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的一员——黑人小女孩佩科拉为创作对象,揭露了在白人审美观和黑人自我身份的双重标准下,佩科拉否定自我,妄图通过身体的变形来拥有童星邓波儿所代表的具有美丽的蓝眼睛、白皮肤的完美白人身体形象,最终只能是走向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身份。佩科拉盼望自己黑色的肉体消失,让白皮肤蓝眼睛的奇迹在自己身上发生。佩科拉最后的疯狂从深层折射出了陷于文化身份认同困惑中的黑人的自卑和无奈。秀拉的成长经历了母辈认同、女孩认同、自我认同和最终的精神认同,她的身份建构是一个不断与他人认同和分裂的过程。莫里森颠覆和解构了西方文学主体的人的神话。秀拉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柏油孩子”吉丁即便融入了上流社会,但是抛弃了本族文化的她又能走多远呢?
在以女性的视角揭示阶级、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同时,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宠儿》《爵士乐》和《天堂》以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黑人对不同含义的“爱”的追求为主线,塑造了光彩夺目的黑人女性形象,逐步建立起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身份,对历史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对黑人社区自身的缺陷进行反思和批判。康瑟蕾塔和贝比·萨格斯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康瑟蕾塔好像是非洲的巫师,她用魔法“迈步进去”救了娄恩的儿子,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引导逃到女修道院的几个“心碎”“惊恐”而又“脆弱”的女人走出噩梦,治愈她们的精神创伤。她给女人们描述“天堂”的景象,仿佛她已找到了向往的归宿。流落到修道院失去身份的女性们自我仇恨(self-hatred)、自我抛弃(self-rejection),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康瑟蕾塔事实上正是起着抚慰心灵、修复创伤的作用,她引导这些女子一一化解各自的痛苦,重新获得心灵的宁静。康瑟蕾塔对爱的参透使女修道院在被洗劫前沐浴在圣光中,她像上帝一样具有救人的天赋。《宠儿》中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也是黑人同胞的精神领袖,她定期的“林中布道”就是黑人们集会和交流的平台,她试图以这种宗教仪式唤醒黑人同胞的自爱和人格意识,寻找黑人的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宠儿》的创作基于真实的历史,莫里森颠覆了西方史学的主流观念,对原历史文本进行反思,“并予以改写,改写被主流历史观所忽略与边缘化的黑人历史,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是当代黑人确立自己身份的必要过程”②。莫里森通过宠儿多重不确定身份的文本建构,给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宠儿已经不是个别黑人家庭的鬼魂,而是“六千万甚至更多”(sixty million and more)的被遗忘的冤死的黑奴,她的存在本身证明生命和自由同样重要,象征着黑人从长期“缺席”和“失语”的状态中回到话语空间,并在历史的“多重奏”中恢复黑人应有的声音,重新建构独立的民族属性和文化身份。
三、抵达理想世界的“伊甸园”
“身份”(identity)又译“认同”,指个人对自己在所处环境中的地位的确立和认识,趋向于心理过程。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认识与建构过程,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更是多元的、开放的。主流社会对于少数族裔的销音,是希望其消失在历史中。少数族裔是美国社会的“他者”(other),历史的沉默者。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指出,莫里森的小说象征着人类的共同命运,超越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界限。③莫里森的创作没有停留在对白人的简单控诉上,它表现出当代黑人女性文学的新走向,超越了对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关注,把目光投向女性作为主体的建构,女性意识从缺失到苏醒,直至最后身份的重建,探讨了女性建构自我的可行性。
佩科拉不加分辨地接受那些将她引向毁灭的价值观;秀拉蔑视传统的幸福观,一生无悔地寻找自我、发掘自我;塞丝为确立自己的身份所做的抗争充满了无奈和辛酸;自立又自信的派拉特则是莫里森笔下理想的大母神形象,她使奶人得以出生,并最终引导着奶人实现了最后的飞翔,加入祖先的行列,回归到黑人民族的文化之根中。死亡和救赎是莫里森重点表现的主题,她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人类,考察女性充满着痛苦和磨难的生存状况。莫里森巧妙地使用非洲的民谣、神话和音乐等文化仪式,消解黑人女性的“缺席”和“失语”,疗救她们的精神创伤,表达那些“言说不出的东西”(unspeakable thing)和无法触碰的禁忌,重新审视和阐释黑人文化的民族特性,建构黑人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④
莫里森的作品也反映了许多其他少数族裔作家找寻自我的心理历程和意识形态,从回避自己的少数族裔属性到正视自己的“他者”身份,并理性地重构双重主体的“自我”,用这一身份从边缘走向中心,获取美国属性。在美国这个共同体中,“一个非白人,一个有色人,同时又完全可能是一个真正资格的美国人”⑤。莫里森的作品充满了寓言性和颠覆性,解构了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叙事方法,重新反省弱势的边缘群体如何维护其固有的文化属性,建构少数族裔美国人的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
作者简介:史 敏,文学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批评理论。
① 斯坦纳:《最清澈的眼睛》,《纽约时报书评》,1992年4月5日,第1页。
② 王玉括:《莫里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③ Gates, Henry Louis, Jr. Preface [A]. In Gates, Henry Louis, Jr. and Appiah, K.A.(eds). Toni Morri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C]. New York: Amistad, 1993.
④ 史敏:《莫里森小说创作中的原始图腾与神话仪式》,《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89页。
⑤ Emory, Elliot.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684.
(责任编辑:水 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