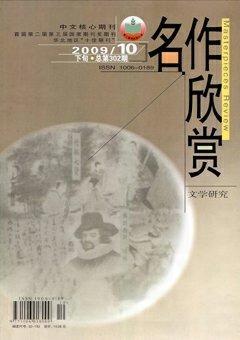宿命的呐喊和可畏的现实
读戈麦的诗歌是阴郁的。他诗歌中充满宿命的追问和无可奈何的呓语。而这样的近乎病态的诗歌却能够为所有人类在经历孤独和困境时疗伤。因为我们至少从他的诗歌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在感动的阅读里得到情感的释放。悲剧的美在这里,戈麦的诗歌充满了悲剧的神圣。
面对现实无奈的妥协是痛苦的。在《誓言》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自毁。即甘心情愿地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在面对希望自己完全垮掉的命运面前,他投降了,而这样的完全服从的降服,只能是绝望后的无从选择,看似从容其实深藏着巨大的悲哀。在诗歌《陌生的主》一首里,诗人似乎早就预见了自己的命运,感到命运的神秘之手,宿命之手的召唤。在他以为那便是归途。生是走在死的路上,死就如同一次回家。但人类永远也无法摆脱对死的恐惧,在诗人那里命运之手是看不到的,如此神秘而令人畏惧。尤其是最后两段的带着质疑性质的话语几乎让人心碎:
你是谁?为什么在众人之中选择了我
这个不能体味广大生活的人
为什么隐藏在大水之上的云端
窥视我,让我接近生命的极限
而他最终听从了命运的召唤:
我将成为众尸之中最年轻的一个
但不会是众尸之王
在诗人笔下,经常陷入对生死的拷问。几乎是呓语式的话语,构成了一首首诗歌。而这样的话语可以用“痛苦”两字概括。在诗歌《界限》里诗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宿命看到了不乐观的未来。他用自己的意志力保持着对自己尊严的认可,对坚强的极力扶持。但这样看似坚定的语言也许只是心灵懦弱时候的心理安慰和暗示,不能解救他内心真正的恐惧和无望。在生与死在发现和隐藏之间,他徘徊不前,极力表现出对生的渴望对更阔大生存空间的渴望。他拒绝单调拒绝狭隘拒绝聒噪和停留,也拒绝和上帝的交谈。因为这些在他看来都指向死亡都指向不可知,所以他拒绝。然而死亡是无法拒绝的。他希望不可能,但那是可能随时发生的。“诗人、学者、知识分子在当今这个精神稀释的时代似乎犹觉脆弱。因为生命主体在‘怀疑一切时,终于连生命主体自身也给彻底地消解了。”①由于对现实的怀疑,对自身生存意义的不停歇的追问,让诗人自己难以忍受生存。
《大风》就是这样一首疯癫之作,它形象地表达了人格分裂时刻的刹那困境。我不清楚诗人当时发生了什么,但就他诗歌长久以来关注的宿命主题和对现实的悲观感受来看,他分明在表现自身的困境,精神的无法摆脱,对现实和精神世界的矛盾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的焦虑。“一个人满身秋天的肃杀,伫立在河上/神经的人,落魄的人,不食烟火的人/他在心中遇见黑夜,遇见时间/遇见蛛网上咯血的鹿,遇见一个宽广的胸怀//一个人伫立在风中,他的心中裂为两瓣/裂为两半,一半在河岸,另一半在河岸//旷世的风像一场黑夜中降临的大雪,他在心中/看见一个人在大雪中,从另一个身上盘过”(选自诗歌《大风》)。犹如一张现代派的绘画,我们看到一个人和另一个自己。他在端详镜子中的自己,如此疯狂,如此孤单,一个自己带着另一个自己艰难跋涉。他渴望找到出路,却发现一个和另一个都那么孤独,互相牵扯而且都充满了疯癫,一路的狂奔让他自己停不下来。如果说一个是本我,另一个是超我的话,那么我们在诗歌里看到了,超我和本我几乎合二为一,他们都享受着理智和情感的疯狂状态,以至于他们顶着硕大的头颅在山峰的极顶。这似乎已经暗示着,天才的成长和毁灭。他们对人类终极意义的追问已经让大脑无法承受那不堪的负重,他们已经先其他人登上高处,高处不胜寒。大众心灵日渐虚脱,无所寄托,无所依恃,生命的恐惧仅限于对被“炒鱿鱼”或“下岗”的恐惧,而不是生存意义失落的恐惧。这种意义空虚使人的精神、心理、肉体都更致命地呈现出病态,从而加速生存意义的“空洞”,“并促使那些索求意义而失重的人,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②精神和生命原出意义的失落加速了对生存意义的失望,这似乎道出了诗人之死的原因,这似乎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死亡或自杀事件的一个注脚。作为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从诗人戈麦的诗歌中,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精神和生命意识缺失带给他的生存危机。在那首《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的诗歌里充满了亡灵的呼告,带着鬼魅的气息。我们似乎看到诗人在创作时站在一个亡灵的角度的书写。他用近乎梦幻的笔法表达着一个纯美的意境。鸽子在广场上飞,在弥漫的天边飞,这些鸽子似乎在寻找“我”一个亡灵的气息,出生和死亡的气息。这样飞翔的鸽子不断飞翔似乎就是一种告别或者凭吊。
那首《献给黄昏的星》中,我们仍旧看到的是挣扎和不得后的虚空。作者用“最后”表达着世纪末的绝望。我在黑夜的尽头,我是黄昏中唯一的星星,我就是我自己一生无边的黑暗等等词句,将一个内心充满自信却又无法找到自信,内心充满建功立业理想却又不断受到现实打击的敏感的心灵袒露出来,而在袒露的同时他不是找到解脱,而是精神上更大的黑暗,他意识到:“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因为我只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宿命和悲哀。这荒芜的大地已经到了最后,到了最后一点声音,而我也只是最后一个。青春的敏感加上世纪末情绪的无边笼罩,让他没有了呼吸的可能。宗教常常能让迷茫的人找到精神的支点,我们在戈麦的诗歌中不止一次地看到了他对上帝的呼告,甚至怀有虔敬的心。在他的灵魂深处充满了被屈辱的命运,充满了被仇视的人生,所以他甚至在最后几乎要喊出来:
主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屈辱的生存才能拯救,还要等到
什么时候,才能洗却世人眼中的尘土
洗却剧目中我们小丑一样的厄运
——选自《我们身上的污点》
上帝似乎听不到他的呼告,也许也正是在面对人群的失望,面对自我的失望,以至于面对整个时代失望的时刻,他才找到了宗教,然而宗教也没有拯救他,他只有痛苦地面对黑暗中的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洁净自己,去保护自己不受到屈辱。而诗人自我的避难所无非是想象力,和他诗歌的王国。在诗歌《南方》中,我们很少见地看到了一些阳光和温情的诗歌。那美好的南方小站,那些美女的歌唱,都曾经令诗人向往,当这些一旦过去,诗人马上清醒地回归到灯火陌生的街头,孤独地继续寻找,甚至于在他以为可以在客栈里开始一种新的人生,但这些都渺茫不可及。只是一时的想象而已。在诗人理智的强力下,他再次把自己从梦幻中拉向终极的追问,导致的是更大的迷茫:那就是如同诗歌所写“此后的生活就要从一家落雨的客栈开始/一扇门扉挡不住青苔上低旋的寒风/我是误入了不可返归的浮华的想象/还是来到了不可饶恕的经验乐园”。想象永远美好,但现实如此可畏。在理智中诗人看到了自己的局限和无可救药,美好稍纵即逝!诗歌《彗星》带着谶语的色彩。“万人都已入睡只有我一人/瞥见你在不眠之夜/神秘之光箭羽之光/砂纸一样地灼烧我侧耳倾听”,他看似在写彗星燃烧并毁灭的过程其实是在写诗人自身的心灵历程。尤其是最后一句,几乎道破天机,这样的死亡事件似乎早就注定,如同彗星的一闪而逝,死亡就在身边不远处,只是诗人深层次的思考在于:死亡的价值有高低。“是燃毁于云层”还是“穿越环形大地”这其实便是对死亡价值的考量:天才般迅速消亡还是持久地穿越时空,让生命力更恒久?这样的问题无疑是痛苦的?因为人类追求永恒的想法永远没有停止,而把这样一个命题落实到一个凡夫俗子身上又显得如此沉重。
在《大海》中,我们看到了诗人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他甚至用轮回的思考表达着自己对生命的认识。大海是浩瀚无边的,这暗合了人类对命运无边的看法,而大海的宏阔雄壮又成为人类的威胁,它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象征,无边的海浪滔天,让人类常常感受到自身的渺小。而提前感受到自己的无法解脱,感受到“晦冥时刻”的诗人,更感受到了自身的脆弱。面对大海他看到了模糊的前世,死亡的意象在那时候出现,而自己来到大海面前,在他以为就是今世的再次轮回。而最终诗人选择投河自尽是否也是他潜意识中对前世的回应:回到水中,回到大海。那宿命的所在。
同样是大海的意象,同样是静谧而神秘的意境,同样是世纪末无法抹去的死亡气息,诗人似乎在《当我老了》这多少带点临终告别的诗歌里,表现出几分淡定和从容。他似乎做好了准备,在向万物做着最后的告别,这时候万物都带着情感都是可以交流的。他在对黄昏说,对大海说,对衰老的知更鸟,对椅子,对秋天的泥土,对一头老马,对黄沙,对读书的少年,他深情地一一告别,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诗人最后的语言:
我的一生被诗歌蒙蔽
我制造了这么多的情侣这么多的鬼魂
你看这天空多像一个盖子
当我老了再也见不到黄昏
“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便缘此而生了。”③哲学家的话语有一定道理,但在诗人身上却要另当别论,我以为诗人的焦虑在于精神世界的超越性强力追求,追求完美的品质、高尚的爱情、博大的胸怀、对人类极度的热爱,正是这样的情怀让诗人致命地看到了和现实的差距,而差距的长期存在,让焦虑日日生长,诗人已经感受不到理想世界实现的可能。所以正如他诗歌所写,他在文字里制造着美好的情侣以及那么多因为空虚而死去的鬼魂,那不是偶然,是诗人看破尘世后的自觉选择。这世界如同一个鬼魂飘飞的世界,他当然是指让金钱奴役的众人,指精神世界贫穷的大多数,而看到这些却无可奈何无疑只能导致悲剧的一生。
作者简介:马知遥,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②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23页,第226页。
③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2页。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