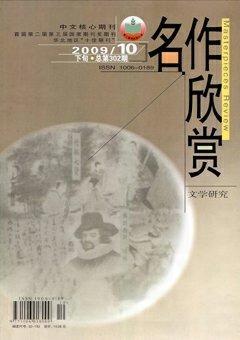繁复叙事的解构尝试
关键词:长调 成长叙事 回归 超越
摘要:千夫长的《长调》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7年度小说排行榜”,它探索的自卑与超越的主题具有人性的深度和人类的共性。小说对极尽繁复绚烂的叙事有解构和颠覆,在解构和颠覆中回归单纯、平淡、质朴,在单纯的诉求中获得和实现着对繁复的超越。
阐释人类灵魂构建的“生活故事”
2004年,中国第一部手机小说《城外》震撼了国内文坛,小说短短的4200字却在该年度就收入18万元稿酬,每字43元,作者千夫长以此被誉为“文字最昂贵的作家”。与此同时,国际主流媒体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日本《富士产经商报》及国内《人民日报》等上百家媒体争相报道。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认为,这是“2004年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事件”。小说还引爆了文坛对手机小说等新文学形态的热烈讨论。千夫长原名贺新年,这位曾投身深圳闯天下,做过记者、专栏作家的60后蒙古汉子,以其新锐而反传统的叙事模式的先锋姿态闯入文坛,成为广东文学院的签约作家。2005年他的长篇小说《红马》开始回归草原,但仍然有现代主义风格,论者以为类似《百年孤独》。2007年千夫长推出力作《长调》成就远胜于前二者,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7年度小说排行榜”五部优秀长篇之一①,在当下文学中较为少有的选择了成长叙事,《长调》因此有着它新的开拓意义。因为相对于欧美文学来说,中国文学不太重视成长叙事,一方面是有开拓意义的儿童文学的贫乏,另一方面是已有的成长叙事作品的浮浅。当代只有王朔、曹文轩、秦文君等少数作家真正重视这一点,而一些作家还缺少抵达灵魂的能力。安徒生、罗曼·罗兰、马克·吐温、林格伦等,一大批西方作家堪称是通过成长叙事建构灵魂的典范。《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爱》、《汤姆·索亚历险记》以及狄更斯和高尔基的名著里,成长叙事都直抵灵魂,他们为探求、构建人类精神的和谐作出了动人的探索,对于人类的心灵成长仍有引领的现实价值。
《长调》探索的主题具有人性的深度。蒙古少年阿蒙内心的自卑、对死亡的恐惧不是个体的偶然,而具有人类的共性。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②他认为自卑感本身并非变态,它反而促进人们去努力以提升地位。甚至于科学的兴起,也是因为人类要摆脱在伟大的自然面前的自卑处境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所以阿德勒说:“事实上,依我看来,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他认为,没有人能长久忍受自卑的折磨,人总要设法摆脱自卑而获得优越感,即成就感。获得优越感的途径虽然不尽相同,但“优越感的目标也同样是在摸索和绘测中固定下来的,它是生活的奋斗,是动态的趋向,而不是航海图上的一个静止点。”③《长调》的成长叙事所讲述的主人公阿蒙的“生活故事”(阿德勒语),审美化地揭示出爱的力量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意义,是文学审美版的《自卑与超越》。
《长调》的开头引用庄子的“道在屎溺”,和普鲁斯特的“人类是在胆战心惊中生存过来的”两句名言作为题记,它们是解读小说的钥匙。
庄子的“道在屎溺”,原意指屎尿这种看似平常肮脏的生命现象中,包含了生命的大规律、大原则,我们不可以轻视这种等而下之的生理现实。放眼当下文学“日常化”的潮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千夫长的用意:我所描写的是阿蒙一把屎一把尿地成长的“生活故事”,然而在这日常化的生命成长的故事中,却隐含着生活与生命的大“道”。这个“道”即是通过叙写一个人超越自卑获得优越感的历程,引领我们思索探究哲理的人性主题:我们超越个人乃至民族、人类自卑情结,走向自信自强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通往超越自卑的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建构的奋斗之路究竟有多远?
小说的成长叙事把时代锁定在“文革”,然而选择的是单纯的成长的“生活故事”,同时做了淡化政治、淡化成人世界的处理。小说的叙事视点是自卑胆怯的主人公少年阿蒙的眼睛。孩子看不懂成人的世界,但却感受了世界的不安和不幸。阿蒙有一个奇异的家庭,父亲曾经是转世灵童、尼玛活佛,而后被迫还俗为长调歌手。虽然与父亲从未谋面,却不能说他完全缺失,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高音喇叭里父亲唱的长调。但他却从未享有过父爱,当十三岁他独自来到旗镇寻找父亲时,却得知父亲在一年前已神秘失踪。阿蒙在成长的漫漫长途里,只有将自卑和孤独的探索之旅进行到底。作者没有正面描写那里的“文革”灾难,而是将历史的痛苦折射式的铺陈为阿蒙成长的背景元素。对阿蒙的心灵成长叙事连接了生理成长的时间,也展现社会、家庭和自然的空间。
父爱的缺失,使阿蒙的孤独之旅满溢着自卑,自卑延伸为胆怯,胆怯集中于对死亡的恐惧。作为首屈一指的草原接生婆,母亲让阿蒙跟随着给人畜接生,使儿子从小就深深体会到生的欢乐和可爱、死的恐惧和哀伤。阿蒙对死亡的印象很深刻。小说第二部第六节描写了阿蒙对死亡的恐惧心理的成因,主要是他过早的目睹了一个难产妇女死亡的场景,以至于使他从此对那家的房子都极度恐惧。
阿蒙的胆怯和自卑在生理上的表现就是尿床。小说至少有七次有关阿蒙的尿炕叙事。阿蒙每次感觉到成长拔节的成就感时,获得爱的温暖和安全感时,尿炕的事儿就烟消云散了;每当有恐惧和不安全感、有失乐园的挫败感时,每当多饮和劳累时,尿炕的阴影就挥之不去。
阿蒙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个体的,也是任何童年个体的共性,只是具体表现在个体中的情况千差万别而已。作者引用普鲁斯特的话“人类是在胆战心惊中生存过来的”,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解读其深刻的含义:人类是在饱受生存环境和死亡的威胁中走到今天的。相对于宇宙力量而言,人类是弱小的,永远处于担惊受怕的自卑地位;人类成长的历程,是在爱力推动下不断地超越自卑,提升自信的过程。
小说第一节描写阿蒙从草原到旗镇的惊险历程,在与死亡威胁的抗争时,他使出浑身解数,救助队长,用长鞭驯服烈马,逃离了死亡地域,获得了一次对死亡恐惧的优越感(成就感)和超越。英雄的力量本质上源自生存与超越的对生命之爱的本能欲求。从草原到旗镇的历程似乎具有象征意味:生死的考验,胆怯与勇敢、犹豫与果敢、欢乐与痛苦,总在不断的轮回之中。
人类克服死亡恐惧的方式和途径,阿德勒、弗洛姆及马斯洛等心理学家给出的科学答案是:合作与爱,是奉献之后所获得的成就感,是文化的创造欲和自我创造欲的实现,阿蒙的“生活故事”为此提供了审美化的文学阐释。
阿蒙进一步地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是在他因为爱而拯救雅图的奉献中完成的。亲如胞妹的雅图无意地报错了幕,当即被校长上纲上线地定性为小反革命要批斗。阿蒙心中陡然涌起兄长保护妹妹的使命感。在他飞奔回家报告母亲的途中,第一次无所畏惧地从他从来都要绕开的死亡产妇的房前经过。爱的付出化解了死亡的恐惧,使阿蒙成长并承担起兄长的责任。
拯救阿蒙自卑灵魂的人除了母亲、雅图,还有拉西夫妻、阿茹等。
阿蒙母亲是一位身份特别的蒙古母亲的形象。她因为嫁给还俗的尼玛活佛而被草原人尊为佛娘。佛娘善良、坚毅、勇敢,遇事沉着果断。她是集所有美德于一身的母亲。母爱的力量是阿蒙成长航程中的强大内驱力,母亲的美德是阿蒙成长航程的目标性港湾。
旗镇寻父时,善良的拉西叔叔夫妇父母般的关爱信任,使阿蒙获得一个了完整的家的体验,排遣了孤独焦虑,他告别童年,进入少年。他们的七个孩子待阿蒙如兄长,使阿蒙有了“哥哥”的责任感和优越感。在拉西家阿蒙奇迹般地从未尿过炕,成了七个“弟妹”的榜样,让他充满了成就感,觉得自己长大了。拉西叔叔使阿蒙多少获得了父爱的代偿。完整的代偿式的伦理之爱,也是阿蒙成长的一种巨大推力。
阿蒙与阿茹在歌舞艺术的切磋之中相知相爱,也是阿蒙超越自卑的巨大力量。从阿茹身上,阿蒙辨析了爱情与动物“发情”的区别,赢得灵肉和谐的爱情。阿蒙纵放悲歌,阿茹纵情激舞。当他赢得人生中完整的灵肉之爱时,他的长调艺术的成长也突飞猛进,琴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完成了心灵家园的构建,最终彻底超越了自卑和恐惧,成为一个精神健康和谐的、自信自尊的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
小说里阿蒙学习和领悟长调艺术精神历程,与他对生命的感悟、发现自我,完善、超越自我人格的成长过程是一致的,即人格与艺术境界的提升是同步的。作家的探索与思考,不但具有人性的深度,也有艺术的深度。以单纯的童年“生活故事”,阐释了人最深邃的灵魂构建的主题,这使千夫长小说的艺术境界获得了提升。
千夫长在小说中融进了拉西叔叔、花达玛、王钰等艺术家对艺术的执著之爱的叙事,他们直接影响阿蒙的艺术生涯和精神的成长。
阿蒙寻找父亲的历程,其实是孩子寻找完整的家,寻找爱、建构精神家园的艰难成长的心路历程,是超越自卑、焦虑和恐惧,走向精神和谐的过程。
阿德勒很重视并强调童年记忆的重要:“在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记忆绝不偶然;个人从他接受到的,多得无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只有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处境有重要性之物。因此,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而童年的记忆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显示出生活样式的根源,及其最简单的表现方式。”对于构建或解释灵魂的小说家来说,言说“生活故事”的成长叙事,是一种单纯而“最简单的表现方式”④。千夫长正是试图通过这种叙事,去揭示个人、民族及人类心灵成长记忆中的重要的秘密。
长调般舒缓深沉的单纯叙事
长调音乐与草原风俗画的诗意融合,长调音乐般的舒缓深沉的叙事节奏,是《长调》给我们展示的全新的阅读视域和奇妙的审美享受。它像流经草原的纯净长河,恬静透明,使人想起同是草原作家的前苏联的艾特玛托夫小说纯净宁静而淡远的境界。作者回归一种单纯的成长叙事,一种对原生态的生存环境的诗意歌颂;而“道在屎溺”的象征意蕴,在艺术张力很强的日常化“单纯”叙事中得以深度渗透和拓展。
《长调》一反《城外》的华丽与煽情,以洗净铅华的朴素文笔,叙写心灵纯净的蒙古族少男少女和草原民族悲天悯人的宽广仁厚的情怀,及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在特定的“文革”年代,尤其在缺失父亲的环境中,阿蒙之所以能克服胆怯与不自信,成长为身心健康的男子汉,最深刻的原因是:他在成长中获得了自由的体验和完整:母爱、拉西叔叔等父辈的呵护、兄妹之情、与阿茹灵肉和谐的男女之爱。阿蒙的成长环境虽然艰难,但草原人的心灵却像草原蓝天一样无比单纯。
“道在屎溺”的题记,已经表明小说对日常化叙事的定位。《长调》的叙事结构非常单纯,阿蒙寻找12年未能谋面的父亲,作为整篇小说的线索,贯穿始终,小说的语言是“辞达而已矣”,是尽可能简约素朴的写实的语言,作者摈弃了近20年来一些作家所热衷的繁复叙事技巧,但小说并未因此而乏味,反而焕发出干净、纯洁、朴素的诗意美感。因此,笔者用“单纯”的魅力来概括《长调》的艺术境界。
这对于千夫长来说是一种突破,也许对于弱化灵魂叙事的小说界来说也是某种回归,或许还包含着从童年成长历程中寻找精神故土和寻找未来的渴求。这种古典式的单纯的叙事,反而因为灵魂探究的深度而焕发迷人的诗化魅力。
贯穿小说首尾的长调音乐的描写,营构出小说的诗意境界,小说结构的单纯和情调的朴素宁静,使《长调》的审美空间像草原一样悠远。
作者巧妙地将蒙古长调《孤独的白驼羔》、《走马》、《安达》等作为诗意的意象,水乳交融地贯穿在阿蒙成长的故事与情境营构中,使小说具有意味隽永的诗意魅力。长调中蕴涵着蒙族人民对自然、生命的古朴的深深敬畏,对人间真情的真纯歌唱,其来自生命本身的纯粹的悲喜、豪迈和苍凉,深藏着人类共有的精神本质。小说贯穿始终的对长调的描写,奠定了小说的情感基调,纯朴舒缓的音乐节奏也自然地构成小说的抒情节奏。
理解了千夫长将长调作为诗意的意象,使小说的境界像长调那样悠远深沉而隽永的无穷魅力,也就感悟了《长调》最突出的审美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千夫长所描写到的长调的情境,与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命运相吻合。
阿蒙从小听妈妈唱的催眠曲就是长调。这是他长调事业成长的开始。小说第二部第二节描写阿妈给刚产羔的羊妈妈唱《劝奶歌》,使母羊和一旁的雅图都热泪盈眶。这种情境在蒙古草原是常见的真实生活画面,它们虽然平凡却蕴涵最动人的感情:一是动物与人的母爱竟然相同并且还能够相沟通。二是人与动物和谐共融的生存状态,阿妈给母羊唱歌本身就非常感人,她似乎是在唱自己,唱出内心的悲悯,唱出为孩子甘愿忍受痛苦做出牺牲的母爱之情。这是天人合一境界的动人抒写。这样的场面使人想起法国大画家米勒的那幅名画《喂食》。
阿蒙还从小从喇叭里学会了爸爸唱的长调《清爽的山岗》等曲子。小说第一部描写阿蒙到旗镇查干庙初次进入阿爸的房间时,发现了一本《蒙古族长调集粹》。在思念父亲的情怀越来越浓时,他情不自禁地唱起《孤独的白驼羔》:
失去母亲的白驼羔,被饿得不停地哭泣;比饿更难受的是,失去母爱的孤独悲伤。
歌词非常简单直白,其回环悠长的旋律就像阿蒙孤独悲伤的心灵一样深淼无边,催人泪下,令人为阿蒙未来的命运揪心。小说也因为有长调音乐的旋律贯穿而变得动人心弦。
《长调》是文学版的一曲蒙古长调《走马》,在结构和意蕴上都有《走马》的精髓。小说叙说的成长的不同阶段的“生活故事”,都可以配上相应的长调:童年是《孤独的白驼羔》,他与雅图共同成长的日子与《辽阔的草原》及相关歌唱母亲的曲子的境界相映成趣,他与阿茹灵肉合一的美满爱情跟《清爽的山岗》等爱情长调的境界很协调。小说《长调》与长调音乐交相辉映,意味深长,沁人心脾。
解构繁复叙事的回归与超越
《长调》意味着小说创作向朴素叙事的一种回归,一是千夫长自身的回归,二是大陆小说创作近30年探索,从极尽繁复绚烂的叙事,向归于平淡质朴的叙事方式的回归,向单纯风致的叙事魅力的回归。
《城外》是适应新的传播方式的商业化创作的成功实践,以华丽文字和婚外情故事作为阅读冲击力的成功之作。然而这种刺激的效应毕竟短暂,它显然登不上人类精神和艺术境界的高层。《长调》一反《城外》的华美风格,它拒斥都市的喧嚣和曲折的情节,抽身于都市恼人的生存压力,及纷纭复杂的人际纠葛,我们可用单纯二字归结《长调》的风格。《长调》写的是“草原的记忆”,作者淡化了时代,留给我们的是淳朴的自然,善美至纯的人性和科尔沁草原的芳香,是纯真、质朴的童年境界和青春的激情。
为什么经历千辛万苦杀入都市的千夫长要回归草原?最简单的缘由是:因为他的精神家园在草原,他人在深圳而根在科尔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还由己。曾有人逼问我们,为什么中国作家总是在农耕渔牧的文化体系中才有创作灵感,大部分成功之作仍然属于此列,与城市如此格格不入?我们不妨放宽心态来思考这个问题。虽然农耕渔牧的文化体系,在近3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渐渐淡出一些作家的叙事视野,可那样的土壤毕竟曾经养育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当作家们试图从中找寻美善的田园诗的记忆时,我们发现了即将逝去的文化中值得继承或思考的东西,它们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缺憾的参照物,依然在温暖着我们的身心。况且这种文化已经作为基因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要人为地割断历史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现代西方文明离农耕文化的距离,比我们离农耕文化的距离要遥远得多,但西方的作家从未放弃过这块领地,他们还不断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传统成为浪漫想象的源泉,永不枯竭。千夫长的回归仅仅是个开始,它与近年来我们重新关注原生态的音乐,回望“原生态”的思潮,是同步共振的。
近30年来,我们对小说基本叙事功能的怀疑,甚至决绝的批判,简单粗暴的抛弃和囫囵吞枣式的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套用,象征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轰炸,我们贪婪地享受金庸的跌宕起伏的故事、琼瑶的煽情、余华小说大悲大苦的沉思、池莉的都市小人物的苦闷、安妮宝贝人性的黑色……随后我们厌倦各种叙事艺术的新式武器的临床试验。现在,《长调》是一股清新的草原风,给我们吹开了草原的风俗画。
《长调》对繁复的小说叙事有解构、有颠覆,在解构和颠覆中回归单纯,在单纯的诉求中获得和实现着对繁复的超越。
作者简介:范肖丹,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①《中国小说学会“2007年度小说佳作”揭晓》,载《南方都市报》2008.04.03;千夫长.长调.作家·长篇小说号[J].2007,(9).
②③④[奥地利]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 黄光国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40,P52,P66.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