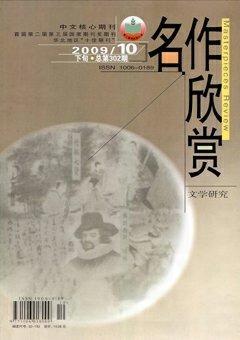论李少君的“草根诗学”及其诗歌创作实践
关键词:李少君 草根性 草根诗学
摘要:批评家李少君对“草根性”的反复阐释和最终定义,已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草根诗学”;而他近年的诗歌创作则是实践“草根诗学”的成功范例,由此完成了一个批评家向现代诗人的转型。
2003年以来,诗歌评论家李少君不遗余力地在当代汉语诗歌圈提倡“草根性”诗歌,直到最近(2009年3月11日),他在答《海南经济报》记者问时,再一次阐述了什么是诗歌的“草根性”。在笔者看来,李少君对“草根性”诗歌的提倡已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草根诗学”。更有意思的是,李少君从2005年左右开始,将自己的写作重心转向了诗歌创作,写出了一大批质量上乘、境界极高的作品,如果从“草根诗学”的理论视点来审察这些作品,其中的优秀之作无疑也是“草根性”诗歌的典范之作。
一、“草根性”与“草根诗学”
2003年,李少君写出《寻找诗歌的“草根性”》一文,提出“草根性”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并不是他的发明。据查,“草根性”是对英文“grass roots”的直译,英文中的这个词产生于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意指草根之下埋藏着黄金。后来词意扩展和衍生,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社会学术语。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对“grassroots”有三种释义:一群众的,基层的;二乡村地区的;三基础的,根本的。显然,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个词与官方、体制或上流社会相对;从文化角度看,与主流、中心或精英相对。二者都是对“草根”本义的借喻,其价值指向在于肯定“底层”和“基础”,且暗含着“根本”的意思。李少君在汉语诗学研究中借用此词也有一定渊源,因为他知道,“草根”一词在“台湾香港1960、1970年代就常用”①。
但是,作为中国当代诗学中的“草根性”显然别有意味,它主要指的是诗歌的“本土性”和“个人性”,而不是“底层”的意思。
“草根性”作为一个诗学理论的词根,李少君对它的解释前后是有变化的,表现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过程。最初,“草根性”“就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的一种生命力的诗歌”②。“一首诗或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人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③这时,“草根性”主要的内涵是着眼于“个人化”和“原创性”。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所谓的“现时性”,李少君《现时性: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倾向》一文,主要通过对“第三代诗人”(于坚、孙文波、肖开愚、翟永明等)的写作转型来考察汉语诗歌在90年代出现的“现时性”特征,即“具有痛切的个人体验中的当下性与现实性”④。这句话也大体上可以概括李少君对“草根性”的认识,这种来自当下与现实中的个人体验即“草根性”,大体上又分两种范式:一是作为“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的产物”⑤的杨键诗歌模式;二是“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经验的产物”⑥的黄灿然诗歌模式。这一认识显然还不具备清晰的概念化特征。
与此同时,“草根性”的另一层更本质的含义一开始就若隐若现地出没于李少君各种文章的字里行间,这就是“中国性”。《寻找诗歌的“草根性”》 一文的写作主要就是针对“新诗开始时就是引进的,拿来的,是与自己的诗歌传统完全断裂的”⑦这样一种诗歌现实而展开的思考。他不满意新诗“生硬、机械、缺乏活泼灵动的本民族气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的代表性诗人北岛还被西方评论家质疑缺乏‘中国性,缺乏独创性,与其他西方诗人的创作没有多少区别”⑧,因而寄望于“‘草根性将转化为一种内心的本能的力量,支持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从而创作出具有原创性特征的独特的具有‘中国性的诗歌,也才能最终完成学来的新诗本土化草根化的过程……”⑨文中提到对北岛的批评,见于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1990年发表的关于北岛英文诗集《八月的梦游者》的书评(其汉语译文《什么是世界诗歌?》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该文站在全球化视野中,用“世界诗歌”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新诗、印度新诗”以及“日本新诗”,几乎将欧、美以外的现代诗都视为欧美诗歌的“山寨版”。这个判断也许过于武断,但并非文化“构陷”,它有其特定的真实性,对中国诗歌来讲,也未必不能成为民族化反思的一个契机。
从那以后,李少君将自己的诗学视野转向东方,对中国的古典诗歌和诗学进行了研究。他对古老的“诗教”传统尤其动心、服膺于孔子的诗学理念,主张恢复“诗国”传统,颇有孔子“吾从周”的某种风格和意味。于是,他在多篇文章、访谈、讲话中反复强调“诗歌乃个人日常宗教”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诗歌确实是中国人的宗教。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与教育与诗歌的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藉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故林语堂曾指出:‘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种仁爱、悲悯情怀。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最多是有时候隐藏一些,有时候张扬一些……所以我曾感慨: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在古代,中国人失意时、悲观绝望时,诗歌都能给他们心灵的安慰,因为诗歌里有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⑩
通过对当代诗歌的“全球化”之痛和“中国性”反思,“草根诗学”终于瓜熟蒂落。2006年1月,李少君在他编选的《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中,对诗歌的“草根性”作了如下定义:“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11}作者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这里的四个“针对”和四个“强调”意义明确,都是当代诗学理论和评论界长期热议的理论命题。
笔者认为,“草根性”所“针对”的四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为两个。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观念化”其实也就是“公共化”——个体放弃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不付成本地共享公共观念,并用之于写作。这四个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老生常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汉诗的“西化”问题,“由于与中国古典的诗歌发生了过于巨大彻底的断裂,新诗在形式上一开始也不自然,只是模仿来自西方的翻译诗歌。”{12}一个是“观念写作”的问题,“观念性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界占主流位置,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可能是所谓追赶意识导致的。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通病,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而观念、思潮是最容易学的……”{13}
与之相应,“草根性”的四个“强调”也可简化为两个:“本土性”与“个人性”(或“经验感受性”)。因为“本土性”与接续“传统”本身是二而一的问题;“经验感受”与“个人性”同样如此。这两个方面又可以用一个字(“根”)来概括:“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14}这个“根”字同时有两方面的内涵:民族文化之根;个体生命之根。联系到李少君个人成长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根”字的现实渊源:对他个人的学术和事业产生过最重大影响的人物韩少功先生正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前提,“本土性”与“个人性”恰恰是站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背景上来谈的,强调前者不是为了撇开后者,其最终目的在于融合、转化与创新。李少君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过中国当代诗歌有“三大传统”资源,都应该加以借鉴和吸收:“构建和确立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和构建和确立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一样,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绝不是封闭自恋的,而是一种大融合,我个人认为:当代汉语诗歌到了一个转型的关口,我们面对着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和发展仅九十年的新诗,那么,对于这三大传统,当代的诗人如何认真消化、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是一个大挑战……”{15}
二、李少君的诗:“草根诗学”的成功实践
李少君虽然多年来以批评家身份发言居多,人们一般并不认为他是诗人。但实际上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读大学期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不过中间有所断续,直到2005年左右,才又重新拿起诗笔。由于对中国诗歌的长期观察,以及在从事诗歌批评中积累的经验,使李少君再次以诗人身份复出时,立刻显示出过人的见识和能力,短短两三年间就为中国诗歌贡献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引起广泛关注,其中《神降临的小站》、《抒怀》、《南山吟》、《麋鹿》、《意境》、《自白》、《山中》等都堪称“草根性”诗歌的典范之作。以《神降临的小站》和《抒怀》两首小诗为例,简要分析之。
《神降临的小站》这首诗要说出它的“好”来是困难的,因为全诗浑然一体,几乎没有任何破绽:
三五间小木屋
泼溅出一两点灯火
我小如一只蚂蚁
今夜滞留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央
的一个无名小站
独自承受凛冽孤独但内心安宁
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
再背后,横着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
再背后,是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
在黑暗中它亮如一道白光
再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
和孤寂明净的苍茫荒野
再背后,是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
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
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
诗歌在技巧上十分朴素,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按说,作为一个资深评论家,早已熟知各种诗的技艺,稍作一点卖弄就够一般读者慢慢去消化的了,但此诗没有。它只是完全平铺直叙地“背后……再背后……再背后……”,一连用了五个“再背后”。但其实就是这一个“背后”和五个“再背后”充分地显示了诗人的高明和技艺的娴熟,验证了“大巧若拙”四字真经。
诗的第一节,是诗的“本事”,暂不多言。
然后,诗歌向读者十分精确而细腻地展示出呼伦贝尔大草原晴朗的夜空下美丽的景观,以及这种景观丰富的层次感。
“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是诗人从身体出发,对贴近肉身的“寒夜”的直接感受。但为什么是“背后”呢?“寒夜”实际上不是整个地笼罩着诗人的身体吗?此处“寒夜”带给诗人的感觉不仅在于其“寒”,更在于一种精神的凛然之感,即第一节最后的“凛冽孤独”;不管是身体的“寒”,还是精神的“寒”,人的感知都是首先从脊柱升起。来自正面的东西,即便是直接的威胁,也不如背后那种“不可知”更让人心慌和畏惧。所以此处“猛虎”一词也十分传神,它的虚拟存在好像一种强力。另外,正因为是在“背后”,并非正面所见,诗歌所展示的全部景观都具有了想象的性质,这样更突出了诗歌美感的内在性和对个体感受力的依赖。
然后,一连五个“再背后”对五个空间层次依次展现:“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亮如一道白光”的额尔古纳河;“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和“苍茫荒野”;“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和夜幕上“闪烁的星星”——这四个层次都是具体的景致,美而宁静。最后,一个相对抽象的“北方”出现了,它笼盖四野,既远又近,显得无比的幽深而神秘,仿佛有某种不可知的力量隐藏其中,暗自调配着一切,神秘的感知顺理成章地被体验为一种“神”性的存在,从而,“凛冽孤独”在诗人的感受中同时是一种“内心安宁”,这就又回到了诗歌的出发点。诗人将这句诗单列一节并以此收尾(这是诗人在多首诗歌中用过的一种结构方式,比如《春天》等),不仅显得既干净利落又神韵笼罩、余味无穷,而且具有了诗歌美学上充足的理由:一方面是诗歌意蕴的自然升华,另一方面又将读者的阅读感知拉回到第一节,形成结构认知上的心理循环。
当代批评家、诗人耿占春曾在他的诗学著作《失去象征的世界》一书中提出“感受性主体”和“意识的微分”两个概念,强调恢复诗人的个体感受力之重要。现代诗人的写作,最普遍的问题也许就是过分依赖于某种先验观念,而失去了古代诗人那种对事物普遍存在的差异的敏感,失去了细致的微观感受能力。在这方面古人比现代人强得多,比如,《尔雅》对“野”字的阐释,就充分显示出古人对空间的层次和差异感是何等敏锐,并坚持用差异性的语言进行精确的命名:“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何等细致!在诗歌方面,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评杜甫的《登高》,也曾反复惊诧于“上二句十四层”、“二句又十四层”、“二句又十馀层”等。《神降临的小站》这首诗最突出的价值,正是其感受性特征与之相似,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差异性感受。另外,诗人还有《雾的形状》、《春天》等诗与此类似,这说明诗人的追求具有自觉性。如《雾的形状》,虽然不像《神降临的小站》那样层层推进,而是在同一平面进行排比,却同样展现出诗人独特细致、个人化的感受力:诗歌首先肯定“雾是有形状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逐一铺排出诗人感受到的雾的形状:“雾浮在树上,就凝结成树的形状/雾飘散在山间小道上,就拉长成一条带状/雾徘徊在水上,就是水蒸气的模样/雾若笼罩山顶,就呈现出塔样的结构。”这些诗说明,诗人正在致力于恢复主体的微观感受能力,其对中国诗歌的贡献难以随便衡估,但起码可以判断,诗人是在自觉地实践“草根诗学”中“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的内容。
如果说《神降临的小站》旨在恢复汉语诗歌的个体“经验感受性”,那么《抒怀》、《意境》、《南山吟》、《山中》一类的诗则重在恢复汉语诗歌的古典意境。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本土化”追求,实则就是要探寻一条融合现代精神与古典趣味、西方技巧与中国美学的汉语诗歌的自新之路。当然,这类诗歌同样要以独特细腻的个人感受为前提,因为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长处。我们看《抒怀》一诗:
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理想”是一个同时富有思想魅力和乌托邦魅惑的词语。一方面它代表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它若被乌托邦化,也容易成为历史和生命的灾难,人类历史反复地验证过这一点。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思考和谈论“理想”,是每一个现代人的重要生命体验。过去,在一个乌托邦中国,没有“理想”或者“理想”不够宏伟、远大的人都被视为胸无大志的平庸小人。什么是远大的理想?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牺牲,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最低限度也应该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诗中“你”的理想,却是为非党、非国、非集体、非人类、无生命的“山”“水”立传、写史。退后三十年看,中国人的理想不正是要创造移“山”填“水”(消灭山、水)的伟大奇迹吗?与之相比,“我”的理想更加平庸:“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这完全是无所事事的无聊之举。“云”是瞬息万变的,何能写“真”?有谁知道何为云之“真”?“窗口的风景”同样变幻不定。至于“拍”或“画”出“一两声鸟鸣”更是荒唐的想法。最后,“画”的对象定格在“家中小女”身上,更加显得胸无大志,俗不可耐。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首诗,却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丰富的寓意:(1)对人类现代“理想”的解构与重构(由伪崇高向世俗人生的回归)。(2)最有价值的理想人生恰恰是表面上看来最无意义的古典式的艺术和审美人生。(3)艺术和人生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相互尊重。(4)艺术的虚幻之“美”须以实在的对象(审美意象)来定格,这是一条艺术的铁律。山也好、水也好、云也好、风景也好、鸟鸣也好,无非都是一种情感的“兴寄”,并非实指,尽可以变幻不定。但最后诗人的镜头聚焦于“小女”身上,一切得到最终落实。诗人在审美意象的不确定中找到的这一确定之物有双重意义:一是美学意义上意象的定格,体现了变与不变、动与不动的辩证关系;二是意象与情感关系上,突出了情感的中心地位,只有它是万古不变的艺术主题。(5)“小女”暗示出中国艺术之美的实质是一种“亲”情,由此反观,中国人与自然风景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审美关系,不如说是亲情关系,这是最高境界的天人关系;(6)诗的最后一句“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在暗示什么?现代诗歌呼唤生活的审美化,必须以生活本身的完整性为前提。日常生活的诗意生成,一方面依赖于生活状态的自然与感性色彩;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双能够一下子就“看”出“小女”是“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的特殊“眼睛”。
我们切不可将这首诗看作是单纯的古典诗歌或古典意境的复活,死去的东西是不可能复活的。它实际上是诗人站在自己的美学和诗学立场对当代生活的重新发现,甚至是发明。比如,诗的开头强调“树下”,中国人谈论“理想”时场所的转移(过去多在讲坛、舞台、广场等貌似庄严崇高的场所),既可暗示“理想”的转移,也暗示出诗人的某种不自信,离开这一特定场域,可能一切都不一样了;同样,《神降临的小站》的背景只能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央”。可以说,这些诗不是现代生活在“存在”意义上的艺术再现,而是镶嵌在现代生活底版上的一幅幅意境淡远却又深邃的风景画,尽管技巧已经天衣无缝,但背景与画面仍没有完全融化为一个整体。这不是诗的问题,而是生活的底色所带给人的感觉分离,诗人已经无能为力,艺术的最后成就者是时间,它终将通过对生活的缓慢侵蚀改变人的内外感觉,与艺术达成一体。一切艺术的经典化过程也许都是如此。
作者简介:向卫国,土家族,广东省茂名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 李少君:《就“草根性”等话题答记者问》,《海南经济报》,2009年3月11日。
②③⑤⑥⑦⑧⑨李少君:《寻找诗歌的“草根性”》,《那些消失了的人》,南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6页,第7页,第8页,第8页,第4页,第4页-第5页,第10页。
④ 李少君:《现时性: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倾向》,《那些消失了的人》,南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9页。
⑩ 《诗歌乃个人日常宗教——答〈晶报〉刘敬文问》,《晶报》,2007年3月10日。
{11}李少君:《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页。
{12}{13}李少君:《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第287页-第288页,第289页,第288页。
{14} 李少君:《诗歌与诗人的归来》,《新京报》,2005年5月26日。
{15}李少君:《重构当代汉语诗歌新图景》,《晶报》,2007年11月10日。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