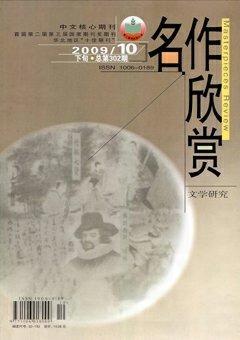用“语言的利斧”归还一切
编者按:戈麦(1967-1991)是一个久被忽略的重要的汉语诗人。他在现代诗歌和现代小说这两种极为不同的思维轨道上,走的是双向修远的道路。他的诗歌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功底和语言素养,以及丰富的文风。1991年9月24日,年仅24岁的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决绝地他毁弃全部书稿,也没有任何遗言,为世人留下几多遗憾。本期我们特邀三位诗评家对其作品作不同方面的分析,以聊慰读者。
《最后一日》写于1990年8月,曾被戈麦的好友、诗人西渡认为“这是一个神明最后一次怅望人间。这是他留给朋友们的遗言。”①这个结论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至少包括诗歌主题意蕴以及艺术价值两个层次的内容。毫无疑问,戈麦是一个以全部生命实践其创作的诗人:从《戈麦诗全编》收录其遗作的情况来看,戈麦的文学生涯不过短短的4年(1987年7月至1991年9月),但其自觉的精神、独创的风格以及生命的沉思却足以使其作品成为“语言的利斧”——“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一定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诗歌直接从属于幻想,它能够拓展心灵与生存的空间,能够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②戈麦对诗歌的认识决定了诗歌在其心中的位置,因而,诗歌、语言与生存最终在其笔下可以得到完整的统一、融合,不过是自然的逻辑。
一
顾名思义,“最后一日”在客观叙述上呈现某种终结的意味,而从诗人主体的角度来看,则带有强烈的“诀别”意识。尽管,翻开《戈麦诗全编》,《末日》、《岁末十四行》、《死亡诗章》、《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等作品单纯从题目上看,就具有强烈的“死亡意识”,但具体到《最后一日》本身,其濒临“界限”的书写仍然如此与众不同:
我把心灵打开
我把幸福留下
我把信仰升至空中
我把空旷当作关怀
在“最后一日”,诗人的生命姿态竟然如此澄明清澈。他以近乎超然的心态面对生命、死亡和芸芸众生,那种“凌空蹈虚”般的姿态体现了沉思冥想后某种日趋成熟的“勇气”——“既然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要被夺走一部分——既然我们每一天都处于死亡之中——我们停止生存的最后那一刻本身并未带来死亡,它仅仅完成了死亡的过程。与这最终时刻相联系的恐怖只是一种起于想象的东西。当把我们投射给死亡的恐怖面罩摘掉后,恐怖也就消失了。”③这显然是属于诗人的“最后一日”,属于坦荡面对生命的一日。由此联想到古今中外多少诗人以身殉诗、慨然赴死的历史,所谓“诗人之死”以及“最后的书写”始终包含着对人性、生存终极的叩问与质询,那些“向死而生”的锋芒必现,使其在揭示和批判人性的限度时往往毫不留情。但此刻,戈麦的《最后一日》却显现了内心剧烈冲突已然闪过的倾向,“我把黑夜托付给黑夜/我把黎明托付给黎明/让不应占有的不再占有/让应当归还的尽早归还”,诗人以如此高度的理性表达“最后一日”的所作所为,他的情感饱满但绝无过分的感伤,这一写作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与海子晚期的抒情诗有几分相似之处,“眷恋”、“托付”以及宗教般的情怀,构成了“最后一日”独特的风景。
按照现有掌握戈麦诗歌创作的材料,《最后一日》属于“厌世者时期”之后的作品④。无论是诗歌《厌世者》本身,还是作为自印合办刊物之《厌世者》,之后的戈麦“一变过去的写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形式”,“这是他天才焕发的最初的日子。之后,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完全自觉的时期,而他也因此陷入了全面的孤独。”⑤而后,即1990年7月至8月,戈麦又完成了诗集《铁与砂》,在这部被友人称之为“关于他的生命,关于诗歌,关于人和世界的命运”{6}的创作,显然构成了戈麦创作的一次“综合”与“转向”——无论从主题还是诗艺,《最后一日》对于曾经的写作具有总结性的意义,从此,他进入了生命同时也是创作的最后阶段;《最后一日》同样也是一种关于生命和写作的告别,诗人最后的生命选择在这里已显露出“预兆”。
二
戈麦,原名褚福军,来自黑龙江边境的一个农场。戈麦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但与当时一代大学生普遍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相比,戈麦开始写作似乎有些见迟,“直到1987年,应当说是生活自身的激流强大地把我推向了创作,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时候,我认识到:不去写诗可能是一种损失。”⑦1987年以后,戈麦开始正式接触现代诗歌,并开始着手创作。1989年大学毕业后,诗人开始使用“戈麦”这个笔名,在朋友眼中,诗人终于在“戈麦”这个笔名中找到了自己——“某种坚实、严峻的东西。”不过,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将戈麦的早逝和他的笔名联系起来,认为“戈麦”这个名字不吉利,“戈”为兵器,加于“麦”,“分明意味着杀戮”⑧,但显然,“戈麦”两个字无论从单字解读还是谐音角度,都具有不同的意蕴,这种与生俱来的意象性所指,或许正是诗人臧棣评价时指出的诗人的“天赋之债是最难理喻的”⑨。
从意象的角度,《最后一日》使用了黑夜、黎明、田野、谷穗、往日等元素,这些元素在配合整首诗那种时而哲理,时而叙述;时而遥想,时而回顾的笔触过程中,构成了某种怀旧的情调——
屋宇宽敞洁净
穹寰熠熠生辉
劳作的人安于田上
行旅的人四处奔忙
我把黑夜托付给黑夜
我把黎明托付给黎明
让不应占有的不再占有
让应当归还的尽早归还
眷恋于我的
还能再看一看
看这房屋空无一物
看这温暖空无一人
此时,戈麦的诗歌态度,既构成了汉语诗人进入“青春写作”所流露的典型状态,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有幸进入语言与艺术层面上的孤独直至疏离的状态。可以想象的是,正如《戈麦自述》中提到的那样,“戈麦欣赏叔本华的哲学,我怀疑若能从头再来的话,他很可能放弃文学生涯,因为他对哲学和思想史的东西有更大的兴趣”;“戈麦经常面露倦容,有时甚至不愿想25岁之后的光景”⑩,构成(也许,使用“反衬”更为合适)了此刻《最后一日》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形象与智慧共同构筑的景象。“诗是对人的生存和内心的省悟,是语言的冒险。”{11}《最后一日》中那带有明显古典主义气息的味道,显现了诗人对理想、情感、生命经验的把握能力。在几个简单的意象遍布之间,戈麦对于汉语诗歌本身的洞察力超越了他对诗歌意象与素材本身的洞察,他由写作本身表现出来的悬浮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语言所能抵达的可能与高度。
三
《最后一日》曾多次提到第一人称“我”,其中处于句首位置的更多达八次。“我”这一人称的反复出现,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些浪漫主义式的抒情诗篇。但在这里,戈麦对于“我”的使用却更多偏重一种对应结构——“我”与生存世界的“对应”。在“最后一日”,“末日”般的启示来自于心灵的感知与外化。“我”把幸福留下,并不意味着“我”无所眷恋;而那“始终惦念着的”,又成为某种“遥想”。在《最后一日》中,“你”仅出现一次,但显然,此刻的“你”与“我”已经获得了统一。在可以面向任何一个对象的同时,戈麦使诗作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获得了自由与毫无限制的交流。
在《文字生涯》中,戈麦曾写道:“我常常在夜里坐在庭院之中空望明月,直到曙光升起。我将一轮明月看作一面虚幻和真实世界的镜子。有时,从它的面庞上还能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我。这种习惯与死亡相通,我在过着一种无死无生的日子。有时,我对这样一种文字生涯有些惶惑。”{12}由此可见,对于《最后一日》以及此前写作中大量出现的“我”,除了可以理解为某种“理性的抒情”,还可以理解为某种“自我想象”直至“自我虚幻”的结果。戈麦以“我”的形式将生命的讯息和自我的经验撒播给写作,他的宽博、恬淡以及虚拟和写作之间的“矛盾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体对“自我”和文字负载的多义性理解。正如戈麦在同篇文章中提及他心仪的文学大师博尔赫斯,那位洞彻万物又因此陷入唯心、孤独的阿根廷作家,和关于他“因痛苦而幸福,因沉湎于细琐而抵达无限”{13}的判断,谁说不与戈麦的《最后一日》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由此推究戈麦这位“死于青春”的诗人,其过早的辞世一方面在于“我”的分裂直至丧失,另一方面,则在于主体把握语言时代焦虑渗透生命的旅程。“诗人之死的助推力主要不是由性格和心理因素产生的,而是对语言的欲望产生的”{14},说明了写作在一个被规训的历史情境下,可能引发的语言的悲剧。作为一个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年轻诗人,戈麦以自己的个性回应写作带给他的压力,他对语言的贪婪和欢乐构成了生命中某种神秘意识,同时,也构成了对自我的严重消耗,“不能说:这时候的我就是现在的我”、“像一笔坚硬的债,我要用全部生命偿还”,戈麦在《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中的诗句不止一次以类似的表象出现在其写作之中。“我是唯一的表演者,观众们在周围复仇似的歌唱”,体现了戈麦面对自我时刻的冷峻、高傲和毫不留情,“他追求绝对和彻底。他不能容忍妥协,这人性的弱点。他在内心里默默承受了生活和时代的全部分量。他实现了里尔克的名言:‘挺住意味着一切。”{15}是的,戈麦以燃烧自我的方式凝视“最后一日”,此时,他唯余肉体和灵魂的“自我分离”。
四
从以上《最后一日》中关于“我”的解读,再联系诗中的铺叙,比如——
我把黑夜托付给黑夜
我把黎明托付给黎明
让不应占有的不再占有
让应当归还的尽早归还
……
但是也只能再看一看
但是也只能再想一想
我把肉体还给肉体
我把灵魂还给灵魂
诗人妄图通过语言“归还”一切已一目了然。但是,值得指出的,这些平淡无奇的句子,一直隐含着诗人在“最后一日”的“自我分裂”。显然,此刻的戈麦期待以“语言的利斧”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归还”,进而回归“源出”或者介入“未来”的情境,但这种诗意的想象,在现实意义上反映的却是语言和生存环境之间的张力。如果可以进一步联系戈麦以往的创作,在写于1989年末的《家》中反复出现“我要抛开我的肉体所有的家”;《誓言》中的“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那么,《最后一日》的“归还”或许只是一个阶段的终结。
当代诗歌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究竟使用怎样一种语言进行写作和表达生存问题已成为重要的课题。无论从“第三代诗歌”带来的口语化、浅表化和世俗化情境,还是生存问题本就是文化转型之90年代的“第一要务”,都对往日的诗歌写作或曰传统的诗歌标准给予了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以语言实践和生命探寻为己任的诗人往往倍感孤独,海子、戈麦之死在一定程度都可以理解为语言“涨破”生命的结果。反思上述事实,不难发现:在某些时候,“曲高和寡”和“难以为继”具有等同的意义。“我把肉体还给肉体/我把灵魂还给灵魂”,代表了诗人以语言还原生命的过程,只是这样的刀锋隐含着自我的戕害,其分裂的伤痛始终大于外在的压力。“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16},刘小枫关于“沉重的肉身”的论断,很能说明《最后一日》中的语言的“归还”,在“拓展”与“承受”之间,能给诗人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正在于“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
从诗歌本身看待戈麦最后的日子,“我”的隐退使《眺望时光消逝》(一)、《眺望时光消逝》(二)、《关于死亡札记》等充满了末日预言的特质。从事实的角度,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戈麦已经告别了个人的倾诉走向了世界本身,而这,正是其处理个人与世界的最后的方式……
作者简介: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 西渡:《戈麦的里程》,《守望与倾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② 戈麦:《关于诗歌》,《戈麦诗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页。
③ [美]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第14页。
④⑤⑥ 《厌世者》一诗写于1990年5月1日,《厌世者》作为与友人合办刊物在1990年4月至6月,共出5期,之后戈麦开始刊印《铁与砂》,具体可参见西渡:《死是不可能的》,《戈麦诗全编》“序言一”,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页,第6页。
⑦{11} 戈麦:《〈核心〉序》,《戈麦诗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0页,第421页。
⑧ 西渡:《燕园学诗琐忆》,《守望与倾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⑨{14} 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戈麦诗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6页,第435页。
⑩ 戈麦:《戈麦自述》,《戈麦诗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5页。
{12}{13} 戈麦:《文字生涯》,《戈麦诗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8页,第432页。
{15} 西渡:《死是不可能的》,《戈麦诗全编》“序言一”,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16}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