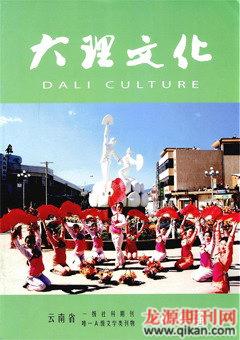走出我的皮肤
敬一兵
我在看书的时候,无意间被刀片划了手指。刀片,这个与文字毫不相干的锋利物,此刻摇身一变,就成了冥想,与我注意力背道而驰,带着扼杀的企图,或者至少也是命令我委身于它的姿势,突然从天而降,置一切于不顾,用锋利的刀口,切开皮肤,侵略到身体内部。犹如惊鸿一瞥间,容不得我与它商量,就有比七月太阳还要殷红热烈的血,汩汩淌出来。看一眼这流淌的血,它就成了有胆量的演讲者,就能够听见尖锐的冥想唆使血液说,我要走出你的皮肤。再看一眼,还是这般一个情形。
突然而来的侵略,说不上惨烈,却具有金属的质感,凉嗖嗖,沉甸甸。分明可以感觉到身体在隐隐作痛,虫子啃噬骨头的那种痛。我想摆脱,于是拿了茶杯,从桌边,把屁股挪到了沙发上。继续读书,却怎么也读不进去。书上的每一个字,俞平伯写的字,一个已经走出了自己皮肤的人写的字,此刻全都摆摇摇地表现出对锋利的刀,或者剑等所有尖锐之物,怀有敌意并保持距离的姿势。这样的姿势,不由自主,再次与曾经流淌在俞平伯皮肤里的血,联系在了一起。
俞平伯的血,很有胆量。他的血,看不见前途,可还是沿循了他祖先弯弯曲曲的血脉,一路经历了不测的风险、灾情和潮汛,流进了他的身体,然后又穿过无数风吹雨浇、天灾人祸的日子,再沿循弯弯曲曲的血脉路径,流出了他的身体。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逗留的时间中,也没有停止寻找突围的机会。这根血脉,如果说成是他的一把火炬,那么,他本人,就是握火炬的手。手稍微有点闪失,都会使火炬熄灭,一线文字的血脉,从此中断。对此,他是高度警惕和重视的。即便这样,他的血,还是找到了突围的机会,走出了他的肌肤,只有撒落在干枯沟槽里的文字,还在见证他的血,以及曾经构建了他生命秩序的谱系。细想想,任何文字,往深处读,就读成了神的谱系,不是吗?
我说的神,不是庙里供奉的菩萨。庙里的菩萨,是人用泥巴做成皮肤,以此来包裹人的寄托和期盼。真正的神,是不需要包裹的,反而是赤裸裸站在那里,不断用自己无形的手,来撕扯裹在人身上的皮肤,让血液流出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岩石要风化,新的生命总是要从旧的生命体上脱落,这就是神的谱系要说的,或者已经说过无数次的故事。虽然故事的描述有点残忍,但它的意思很清楚,再现和重复自然的秩序。
除了照片和文字,没有一件事物,会为快要走完不惑之年的我,保存二十岁的青春,二十岁的肌肤。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打消有一天,所有的血,都会从我的皮肤里走出去的念头。每一次走出皮肤的血液,数量不等,强弱不同,没有预约,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除了先后排列的秩序。
显然,呈现的秩序线索,是我能够从混沌的迷雾中,捕获到的自然线索。这条线索,清清楚楚铺在我的身后,那是我走过的路,也清清楚楚展在我的身前,那是我的先人走过的路。海明威,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川端康成就不说了,他们走在另外的血脉路上,我与他们搭不上边。还是说说俞平伯。他的曾祖父俞樾,是天地间用另一种笔墨写俗小说的一个人,是俞平伯的祖先。俞樾用割裂经文的胆量,搭救了俞平伯的胆量,让他看见,乾隆皇帝为修建团河宫耗资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成的罪己碑时,有了在特殊氛围下,说出“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这句话的脾气。与此同时,俞樾顺便也就遥遥地搭救了我胆小的父亲,让他第一次有了胆量,走出自满自足的地主家庭,在高原的一棵杜鹃花旁,邂逅了我的母亲,并使我的血液,从此烙上了高原太阳的色泽。
之后,我父亲的胆量,由于社会原因的始终纠缠,在他不时用火焚烧他写在纸上的字的时候,一起被焚烧了。他瓦解自己的胆量,也试图瓦解我。这个情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直到此刻坐在沙发上,因了尖锐冥想的刺入,再也读不进俞平伯的文字,我才知道,这个刀一样锋利的冥想,与我的父亲有关。提及我的父亲,只是我敬重的母亲出场前的一个铺排,就如同风的吹拂,只是对一场山雨到来的铺排一样,没有预谋的意思。我的母亲,时刻也不会忘记,用类似杜鹃花鲜红的光芒,温暖了作风粗砺的父亲的同时,也在没有父亲理性阳光照耀的阴霾天空下,隔了万水千山,用她的挂念,用她的念叨,特别是她那双颤抖的手,疏导蛮荒的生命河流中,父亲焚烧文字、焚烧胆量而淤积在我生命河床上的堵塞物。母亲的疏导,从来没有间断,这不仅阻止了灾难的发生,让我的胆量,一次次获得搭救,而且也验证了,所有的瓦解,都不会让大地颗粒无收,都不会让皮肤合围起来的微小空间,影响到大自然的秩序。
我的生命之河,是我母亲心中、眼中、呼吸中甚至脑海中的生命之河,一条只有我母亲才能够抚摸到并且讲述出来的河。我没有理由否认,我的心跳、脉搏和呼吸,都是为了感恩我的母亲而表现出来的。我常想,母亲的疏导,使我有了可以浮流而下的上游,能够顺利地从高原,被波浪驮着,来到了盆地里的一块鹅卵石上。这块鹅卵石,覆盖了许多的浮游生物,呈黑褐色,是许多的先人,在它身上走过,摸过,看过的一次次积淀。我不知道,早已走出了皮肤合围的李白、杜甫、陈子昂和俞平伯,是否变成了一粒沙砾,曾经在这块石头上驻足过?但我确定,这块石头是一颗放大了的痣,它处在我视线的左侧位置,与我左手腕上的痣,还有我母亲脖子左边的那颗痣,相互对应。那么确定和恰好的位置,似一种不偏不倚的美学!呈现大美的物质,必定是天地运行与血脉运行的共同创造物,必定是在一个神秘时刻里的和谐结晶。这条线索太重要了。
皮肤是一种概念,充满了固守或者看护的张力,十分强韧,像巨大的山脉,对流经山谷的河,形成强大的逼迫态势,令我敬畏和臣服。于是,我过去所做的一切,包括吃饭、读书、写字、挣钱、谋官、占有,都是在迎合皮肤的观念,顺应皮肤的思维,或者干脆说,就是不断为皮肤的巩固,不倦劳作。皮肤这条大坝,被我心甘情愿地越垒越高,坝内的理想,与坝外的现实,落差越来越大。透过巨大的落差,我看见了自然秩序的背面,黑漆漆,阴森森。一切的存在,都与心灵,发生联系。感觉与否,有的时候,的确依赖一次与文字毫不相干的尖锐冥想,对皮肤发动的突然侵略。游吟盲诗人荷马,正是被尖锐的冥想侵略过,才把眼睛里所有的景象统统驱除,再改由七弦琴和嘴巴,排放他的词汇。贝多芬把耳朵里的东西全部排放了,长了翅膀的音乐,才能够飞出他的脑袋。川端康成更是绝决,口含煤气管,将皮肤合围了的所有东西,彻底释放,如果不是这样,他身后的文字,哪还有继续舞蹈的空间?我不具备他们的胆量,但我却被他们启迪,重新认识到,俞樾搭救俞平伯,还有我的母亲用双手疏导生命河流,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暗示。
寻找对应物的准确性,以达到暗示的最为幽深辽阔的边界。这个经由暗示获得的想法,从此让我变成了一条蚕,沙沙沙吃着文字的桑叶,然后一个劲从身体里吐出丝,再化成一只蛾,从丝织成的边界,彻底穿越而出,作一次冒险的飞行。这就是暗示的准确意思。除了要用文字的方式,走出我的皮肤外,还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