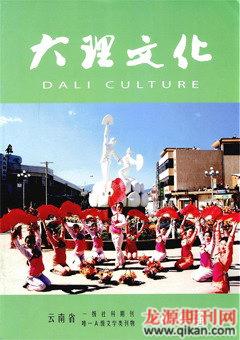从前有一个人
常江龙
有许多事情,时间隔得久了就会变得不那么真实了,正如远距离的景物。童年的许多记忆对我来说有恍如隔世之感。能使我的记忆变得真实的是那些儿时听过的故事。
儿子小的时候总是缠着我讲故事,而我总是以“从前有一人……”这种模式开场的,讲述中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一个人的影子,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当我静下心来认真地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时,这个影子开始逐渐凸显出来,它让我记起了一个儿时的伙伴和由这个伙伴带来的一段岁月记忆。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他叫小虎,是筒子楼里出名的闹包,但他却是我童年时心目中的英雄,我们崇拜他顺口胡诌也能成故事的本领。小虎是我们孩子群里的老大,他知道自己在我们群里的分量并利用这种权威常常教我们干一些叫大人们咬牙切齿的恶作剧。
小虎最怕的是他妈,小虎妈才是真正的老虎。她决定要教训小虎的时候就会在楼道里用低沉的声音叫小虎的名字。那种叫声真的像老虎的低吼,能令小虎魂飞魄散。正在给我们讲故事的小虎听到母亲的低吼立刻像火烫了屁股一般跳起来往楼下跑去,不知好歹的我们依然尾随在他后面继续缠着他讲故事。小虎并不烦我们,他带着我们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大口地喘着气,惊魂未定地又开始讲他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还是他自己瞎编的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小虎忽闪着一双长睫毛的眼睛开始讲。讲着讲着他的气平了,故事流畅了。故事很简单,就是从前有一个人,家里如何的穷,这人如何的善良,恶霸地主如何欺负他,神仙如何的帮助了他,让他娶了玉皇大帝的女儿等等。但简单的故事却被他讲得光怪陆离,神神鬼鬼,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
我们不知道从前的人是什么样的,小虎也不知道。只感觉从前的人很遥远,也很模糊。既然那些人既遥远又模糊那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于是小虎就可以很从容的讲,很坦然的讲。他讲得昏天黑地,讲得唾沫四溅。故事让他和我们都忘记了危险依然存在,直到小虎妈提着棍子虎视眈眈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作鸟兽散。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小虎讲故事,后来我们家因父亲的工作调动而搬出了筒子楼。再以后我又听过许多的故事,故事也总是以“从前有一个人……”开场的,这些故事总也听不厌,因为讲述方式虽然不变,内容却随着时间在变。一个阶段在听一个阶段的故事,故事里人是不变的主角,从前是不变的开头,从前的人总是永远的话题。
在许许多多的故事里,我常会记起小虎讲的故事。
让我再次在现实中见到小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下午,天很冷,天空还下着小雨。我因小有不适到医院看病,在医院大门的坡道上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衣服褴褛双腿截肢的男人,我慌忙过去帮忙。当轮椅推进医院大门时,轮椅上的男人感激地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一下就认出了轮椅上的男人就是当年爱讲故事的那个小虎。此刻,他的眼睛充满了无助和悲哀,巴巴地看着我像一只走投无路的鹿。
显然,他没有能够认出我,我也没有向他说明我是谁。我低头看了一眼男孩,惊讶地发现,男孩有一双长着长睫毛的眼睛。轮椅被缓缓地推进医院,松手时我木然地看着小虎坐在轮椅上的背影,直到我被人撞了一下。我恍惚地走出医院,忘记了我是来看病的。
在以后的时间里,小虎坐在轮椅上的身影一直搅扰着我,让我寝食难安。我通过一个有联系的儿时伙伴了解到:小虎在企业改制时下了岗,一年前得了骨癌被截了肢,妻子因他贫病交加离开了他,那个推轮椅的男孩是他的儿子。我的心一颤。再次想起那个以幼小的身体拼力推轮椅的男孩,那双长睫毛的眼睛和小虎小时候一模一样,只是不再有调皮活泼的光泽。不知道小虎是不是也给自己的儿子也讲故事,也从“从前有一个人……”开始。
以后,我就经常地见到坐在轮椅上的小虎和他推轮椅的儿子。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始终没有和他打招呼,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西晒的太阳下那重叠起来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人群中。后来知道小虎每过几天都要到医院打止痛针,陪他打针的一直是他幼小的儿子。小虎的遭遇让他的儿子过早的目睹了痛与忍着两种沉重的感受。
再后来,我没有见到小虎了。我好多次在小虎经常出现的地方,用目光搜寻他们父子俩,但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我向伙伴打听小虎的情况时,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小虎死了。我知道小虎迟早会死,但是他的死讯还是让我嗓子发干,手心发凉。
那他儿子呢?半天我才突然问了一句。谁知道呢。伙伴还是轻描淡写甚至有些冷漠地回答。我心里一阵痛楚,很长时间我没有说话。我把目光越过伙伴,抬眼望去是满目的秋黄,几片黄叶在地上翻卷着漩涡,然后又散开,一粒沙子迷住了我的眼睛。等我再睁开眼睛时,刚才的风波已归于平静,大地还是原来的大地,只是那几片黄叶不知去向。大地是博大和坚韧的,但在他广阔的胸膛上依然有柔弱的生命。
我知道,又有一个生命结束了,他已经成了故事里从前的人。他的故事会不会有人来讲呢,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