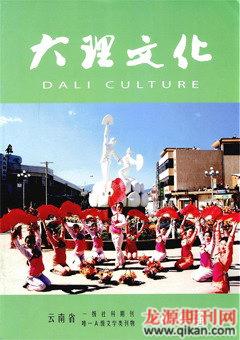外婆的甜苦茶
茶 铭
很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便把我和姐姐寄养在外婆家。也许因为生在茶乡,再因外婆喜欢品茶,因此我从小便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甜苦茶,其实不是什么特别的茶种,也没有复杂的加工工艺。只是烧一盆碳火,用一个小拳头般大小的土陶茶罐,放上产自无量山的大叶茶,在火上慢慢烤,慢慢抖,待茶叶焦黄,香飘四溢之时,冲入用铜壶烧的开水而成。甜,是因为外婆会在茶中添加白糖;苦,便是茶叶天然的苦涩。那种简单混合的味道,是童年的一种气息。
回到父母身边之后,每到周末都一定会去外婆家。外婆每次都坐在小院角落的沙发上,身前的陶制小茶罐在火盆的边缘咕噜噜吐着泡沫。寒暄之后,外婆一定会慈祥地问我们,要不要喝一杯甜苦茶。那是我们到外婆家惯例做的第一件事。
在品茶过程中,我们围着小小的火盆,坐在比我年纪还大的木凳上。长辈们聊天。我只顾着在碳火上烧烤食物,馒头花卷,花生核桃,有时候还有饵快。待到烤出些香气,就下着甜苦茶吃。
喝茶之后,大人们还在谈论。我和姐姐则到屋里,和电视为伴。有的时候,母亲会让我们给花浇水。小院里、楼梯拐角的地方,都摆满了盆栽的花草。茉莉、米兰、月季、粉团、马蹄莲、太阳花等等,还有些始终不知道名字。我和姐姐从厨房接水到木桶里,然后用葫芦瓢把水小心翼翼地浇入每一个花盆里。记得我一直分不清月季和粉团,区分那两盆花的功课我做了整个童年,最终仍旧没有个结果。每次外婆都会在甜苦茶里加一个米花糖做奖励。而我们则如获珍宝般欢欣。
进入金秋季节,我们会采集一种花的花瓣,混上一种黄色的细细的藤状植物,然后揭碎敷在指甲上,外面用一种叶子包好,扎紧,过了一夜指甲就会变成橘黄色。谁染得好,谁就可以多喝一杯甜苦茶。虽然结果往往是大家都能喝到茶,可是大家仍旧乐此不疲地把甜苦茶当作战利品并为之奋斗。
更多的时候,到外婆家便意味着喝甜苦茶和玩耍。什么砸块、斗鸡、躲猫猫,随着年岁的增长,都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只有那甜苦茶,每每想起,仍觉口有余香。
甜苦茶,其实不过是一杯普通的加糖茶罢了,但仔细想来,那些淡淡的甜和苦在岁月更迭之中,便多少含有些人情冷暖的意义了。
后来,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们搬到了遥远的城市。只有假期才能回家乡一趟。外婆生了场重病,之后便半身瘫痪。考虑到外婆的行动不便,舅舅先后给外婆买过几套电茶具,但外婆总以“烤出的茶不香”、“烧出的水不甜”为由,宁让那些“现代”的电器落满了灰尘,却仍旧守着沿用几代人的碳火茶罐。于是,每次回到外婆家,外婆仍旧坐在原来的位置,用不便的右手操弄火盆中的器皿。外婆还是慈祥地问我们是否要喝杯甜苦茶。我们开心地点头,像多年前的孩童。
外婆生病之后,便不太到远的地方活动了。偶尔到门外古街小店和店家聊天。她的生活已经缩小成为这块小小的天地。一方湛蓝的天空、繁盛的花草、冒着微弱青烟的火盆和沉默的外公,就是外婆的生活,简单、宁静。
我们把外面的故事讲给她听,希望这短暂的交谈时间可以弥补她漫长的寂寞。外婆总是慈祥地微笑着,说到好玩的事情的时候就爆发出童稚的笑声。但是,有的事物她已经不能理解了。外婆说世界变化太快,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坚强的外婆永远慈祥地笑着,但眼角不时也透露出一些无可奈何和落寞。或许太平静的生活在淡化欲望的同时也逐渐沉淀情感,积淀到一定程度,便需要倾诉与关怀作为宣泄的出口。可是大多数时候外婆也只能面对着安静的小院沉默。
也许我们都认为大家聚在一起会好一点。可是,当大家聚在一起,却发现能共同交流的话题逐渐少了。外婆听不懂“互联网”,也弄不懂“3G”是什么;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听外婆讲“雷响茶”、“百抖茶”……大家闹哄哄地聚在一起,无非相互问候,相互祝福,最终各找地方倒头大睡。到了吃饭的时候又热闹起来,大家又开始拉拉家常,说说笑话。饭桌是家庭最温馨的地方,可以放下所有包袱,开怀畅谈。饭后大家都围坐着看电视,偶尔有话题抛出来,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再次回归沉默。电视一完,便散场了。不知道热闹冷却之后,外婆是什么感受。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直到一次,一个我们即将离开的早晨,外婆对我说:“你们回来我很开心啊。现在你们要走了,突然安静下来,我很不习惯了。”我的眼眶突然热热的。外婆没有再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心疼地看着外婆,一阵酸楚。外婆把一杯甜苦茶放在我前方:“喝吧。到了外面就喝不到了。”我用力地点点头。
临行前的最后一杯甜苦茶,一口口很认真地品茗。温热的液体顺流而下,在体内形成一股暖流。甜密之后有淡淡的苦涩回味。突然觉得这难以表达的亲情便似这甜苦茶:给予彼此的关怀便如这茶中的甜,而那些无法传达的伤楚便是苦,享受甜蜜的同时又要甘于忍受苦涩。
在异乡的日子常常怀念外婆的甜苦茶,却从不去复制这简单的茶。因为,我知道那甜苦茶的味道是不能复制的,一定要回到外婆家,去感受外婆亲自泡的甜苦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