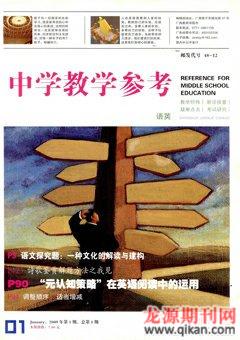试评《伤逝》
施泽红
有人说,《伤逝》是鲁迅的一篇“自传体”小说。对此,鲁迅先生曾在《致韦素园书》时无可奈何地说:“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是愈做愈难了。”虽然鲁迅非正面地否认了,但其中有些情节和心绪无疑与他和许广平相爱的经历相似。《伤逝》中有鲁迅先生对男女平等、女子自由及爱情问题的见解。从“单知道仍然要战斗”到“洋鬼子学说”不能指明妇女解放的道路,说明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套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封建礼教的枷锁。鲁迅先生一直认为妇女问题和爱情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指出,妇女必须投身于解放社会,为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只有解放了社会,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伤逝》写作于鲁迅由革命主义者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关键时刻,是一个爱情悲剧,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悲剧。
《伤逝》是涓生的内省性的自剖。鲁迅创作这部作品时,也正是他《野草》大量繁殖之时。《伤逝》同《野草》一样,主要是鲁迅自我心像的艺术写照。当我们看到这篇剖心自忏的“涓生手记”时,不仅充满哀怨的诗情,而且有些片断从构思和文学技巧上,像在读一篇编外《野草》。文中写涓生在通俗图书馆枯坐时,眼前似乎看见了“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白日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这每一个形象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生涯,如一个个快镜头,连成一个异常广阔的天地,使涓生倾注了热烈的向往;当他向子君表示不再爱她时,他又一次重复起这种想象,“我便轻如浮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他愈来愈渴望摆脱子君而走向自己的新生活,所以这想象中的主人公也变成了他自己。到子君走后,他便再次看到了:“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这时他的心情是沉重而又轻松,他觉得有了解脱的前途。像这样用跳跃而浓缩的形象进行心理描写,在章法上既有照应,又互相错落;既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心情变化起落的几个层次,又造成了散文诗的凝练而又浓郁的抒情气氛,在小说中可谓别开生面。
《伤逝》从整体来讲偏于主观,直抒情愫,通篇以“手记”的形式表现涓生的思想、与子君的聚离以及与子君在一起时的矛盾、子君死后的那种悔恨和悲哀等。他认为自己和子君要“脱出牢笼”就必须去斩杀油鸡,放逐阿随,进而认为真正的累赘在于子君,要开辟新的道路,必须遗弃子君。这里充斥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逻辑。“我是我自己的”在某种场合会有反封建的因素,但又深烙着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把自我作为圆心,万物都得围着它转。涓生用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获得了子君的爱,让子君去追求“自由”,最后又用同一套让子君作出牺牲,给他自由,最后迫得子君离他而去直至死亡。他在悔恨时,认为子君的死是因为他向子君讲了真话,他一再阐发他对真实和虚伪的见解,其实他只是从自己的主观出发,他根本不明白在那种社会,无权无势的子君怎可能“是自己的”呢?而“我是我自己的”这句话的确切内涵又是什么呢?
子君并非死于他的真话,而是淹死在旧社会礼教的唾液之中。涓生的真实与谎言都不可能挽救子君的死亡,反而加剧了子君的孤独死亡。涓生太主观臆断了,他代表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明白自己的“第一步”该怎么走,他只能靠说谎与自欺来鼓励自己前进。子君的死正是吞服了涓生大剂量的思想毒药的结果。
对于《伤逝》的思想和主人公的评价,各研究者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我想鲁迅先生并非要批判子君与涓生的个性主义、恋爱自由,而是旨在批评他们个性解放的不彻底,联想不到社会的解放,故而经不住封建势力的夹攻。《伤逝》的思想、艺术特点值得鲁迅研究家们去作进一步的分析,让它永远在文学史上放射出它应有的不衰的光辉。
(责编 覃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