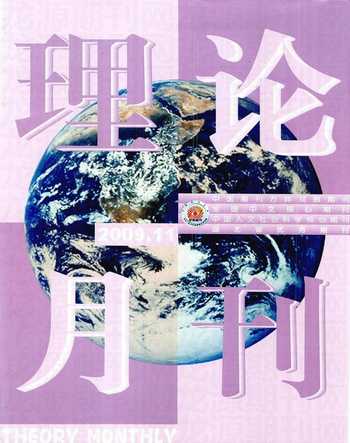论当代历史叙事范式的转型
袁 园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历史叙事范式急遽转型,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元历史叙事彻底瓦解,个人化历史叙事成为新的历史文本生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历史叙事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小说的多元发展,而且暴露出传统历史叙事理论的滞后,当下历史小说批评亟待突破。
关键词:历史叙事;转型;个人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1-00128-03
一、元历史叙事的解体
建国以来至新时期以前的历史叙事,从本质上说是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元历史叙事。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对历史理论的垄断以实现对历史话语的规约,恩格斯对历史作出如下经典论断:“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则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加以引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上述论断无疑是当代历史话语生成的逻辑起点,具有绝对权威的元话语地位,当代历史话语的生成都是对其复制和扩充。姚雪垠谈到为何早期写不出《李自成》:“……首要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征服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明白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文革结束以后。极左政治意义上的元历史叙事逐渐解体,“反封建”成为新时期以来历史叙事的重要主题,以《李自成》、《星星草》、《风萧萧》、《九月菊》、《天国恨》为代表的长篇历史小说,均表现了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统治的共同母题,如吴越所说:“每一个从事于编写或创作历史小说的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反封建这个主题放在第一位。”
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历史叙事衔接上了“五四”反封建的启蒙话语,但总体上仍局囿于官方限定的话语空间内,残留着浓重的政治气息,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叙事内容上,题材选择仍然局限在社会政治学范畴内。对历史小说的题材价值判断标准,取决于能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再现历史全貌,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中,大部分仍是农民起义题材,仅太平天国题材的小说就有《天国恨》、《大渡魂》、《天京之变》等;其次在叙事结构上,较多作品故事情节以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为主线,沿着开端向高潮逐步展开,呈现出鲜明的二元对立框架。由于阶级阵营的划分,因而人物形象序列划分为黑白分明的敌我阵营,比如《李自成》中的李白成与崇祯、《九月菊》的黄巢与田令孜、《星星草》的赖文光与曾国藩;其三在艺术表现上,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是主要风格,现实主义是一统的艺术手法,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主要美学原则。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大多篇幅宏大,力图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仅就塑造人物而言,《李自成》前三卷有350人之多、《辛亥风云录》200多人、《戊戌喋血记》有180人,近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因而任光椿认为:“史诗式、纪念碑式、百科全书的作品是衡量作家攀上艺术高峰的主要标志。”这样一来,复杂丰富的历史被简化为宏大的社会史、政治史和阶级史,导致历史小说的社会学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创作实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禁锢的逐步松弛,历史观念变革大规模展开,越来越多历史小说突破了单一的政治社会学模式,表现重心从社会政治转移到了人性冲突、情感心理、民间文化等美学层面,彰显出独立的审美品格。不仅传统历史小说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门柳》、黎汝清的《皖南事变》、乔良的《灵旗》等突破了阶级论的框架,力图复原历史的真实和复杂,而且以莫言、余华、格非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积极探索历史叙事手法的变革,冲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诸多禁区,有力地加速了元历史叙事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文化语境的全面转型为历史叙事变革提供了根本动力,历史小说进入了急速发展时期,元历史叙事分裂为无数个体的小叙事。历史创作呈现出多元无序的格局:既有主旋律范畴的革命纪实历史叙事、精英文化范畴的先锋历史叙事和文化历史叙事,也有属于大众文化范畴的历史传奇叙事和玄幻历史叙事等。纯文学意义上的精英历史话语不断边缘化,消费化娱乐化的大众化历史叙事迅速崛起,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横扫一切,彻底瓦解了建国以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元历史叙事。
二、个人化历史叙事的生成
建国以来,国家意识形态以毋庸置疑的权威向人们承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在阶级斗争推动不断进步,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姚雪垠曾谈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写好阶级斗争,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而不写自己所不理解的事,也不写在历史本身规律之外,历史条件允许之外,附加不可能的事。”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下,作家无法独立自主地进行艺术构思,只是被动机械地反映历史本质,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从而制约了历史创作的多元发展,导致建国以来历史小说创作艺术质量普遍不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冲击。元历史理论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历史事件作为已经逝去的存在,在没有主体介入之前,只是一种散乱无序的存在,是构成历史的原材料,自身不具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所看到的历史只能是不同个体阐释的产物,而非对历史客体的复制,因而“谁在说”决定了“说什么”和“怎样说”,进而制约了历史文本的生成。因而在创作实践中,不同个体从不同视角、趣味和目的出发,选择多元艺术表现方式书写心目中的历史,从而赋予僵死的史料以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个人化历史叙事由此生成。
具体说来,个人化历史叙事具有以下特征:(1)独立性。文化转型后自由开放的文化语境已经形成,赋予作家叙述历史极大的自由,作家不再被元历史话语禁锢,而是真正以个体经验为核心。独立自主地进行艺术创作。如李锐所说:“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不愿意去做这徒劳的努力。”其作品《银城故事》完全虚构了“银城”这一历史空间,通过对革命党武装暴动的描写,全面颠覆了宏大革命历史的叙事模式,表现出个人对历史非理性的反思。(2)差异性。由于不同个体的文化背景与审美趣味不同,面对相同史料存在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没有哪一种理解更真实,如波普尔所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以武则天题材为例,不同作家对于武则天的艺术处理是不同的,格非、北村、苏童的《武则天》注重表现存在主义式的形而上思考,赵玫的《武则天女皇》、冉平的《武则天》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发掘女性复杂精神世界,野岭伊人
的《风流女皇武则天》则着重渲染其旺盛的情欲与传奇经历。(3)创新性。根据伽达默尔的接受文论,由于不同个体的理解结构的不同,作家面对史料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文本的意义,而是在对其解读的基础上,发挥主观想象生成新的历史意义。比如历史上关于高阳公主的文献记载仅有寥寥数行:“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婿……”玫的《高阳公主》却不拘泥于有限的史料,大胆发挥创造性艺术想象,以女性的心灵去感知历史,从容貌、性格到心灵复活了这一尘封多年的历史人物。
所以。个人性历史叙事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生成机制,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小说的艺术表现空间。不同作家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表现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创造力,无论在叙事、结构还是文体、语言都呈现出多元的艺术风格,表现出多方面的艺术创新。
三、历史叙事环节的转换
面对新的历史文本生成机制的生成,只有通过对个人化历史叙事范式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历史创作才能得到根本阐释。任何历史叙事的生成过程都必须经过以下环节:历史认知一历史价值评判一历史审美转换一历史小说的传播与接受。与以往相比,20世纪90年代历史叙事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换,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历史认知范式由元历史认知向个体理解转换。建国以来的历史叙事对历史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宏大革命史,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本质真实观,认为史料能够像镜子一样再现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由宏大历史转向细微历史,由外在的历史事件深入到历史人物内在的心理,注重不同个体对历史的多元理解。比如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女皇武则天》将武则天塑造成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领袖,20世纪80年代李瑞科《武则天》则凸显其大胆改革的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作品则侧重于挖掘其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体现出不同时代作家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认知。
其二,历史价值评判方式由一元政治价值向多元价值转换。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普遍认为政治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作品的艺术价值,《漠南魂》的作者张长弓认为:“阶级斗争,那是历史的规律。我们搞创作的,不能为了感时髦去违背历史,违背马克思主义。”因而笔下的历史人物形象按照阶级属性打上了鲜明的政治价值标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的多元与价值标准的多极,不同个体从不同的价值取向重新评价历史,历史翻案说成为热潮,比如唐浩明《曾国藩》、二月河《雍正皇帝》、吴果迟《李鸿章·海祭》超越了狭隘的道德与政治价值评判,以多元价值观重新评价历史人物。
其三,历史艺术表现手法由全知全能叙事走向多元。建国以来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下,为了让历史小说承担图解政治与宣传教育的任务,全知历史叙事成为一统的艺术表现方式。作家普遍认为叙事技巧是无足轻重的,叙事手法长期局囿于现实主义,如杨书案所说:“我以为衡量一部历史小说的高低,无例外地首先也应该看它是否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突破了单一的写实手法,既充分借鉴西方叙事技巧,又积极汲取民间艺术资源,无论叙事话语的风格、叙事结构的编排还是叙事技巧的运用都体现出了创新。比如李洱的《花腔》打破了传统的全知叙事,采用“多重式内聚焦”的叙述视角,80后作家的玄幻历史叙事则呈现出影像化、平面化、拼贴化的审美特征。
其四,历史话语由政治话语转向多元话语。20世纪90年代历史话语由社会政治学范畴扩展诸多领域。在语汇、修辞以及叙述策略方面呈现出多元的话语风格。传统历史叙事较好地将文言与白话相结合,具有典雅古朴的话语风格,比如唐浩明《曾国藩》中,曾国藩对王世全说的一段话:“国藩当年从汪师求学,便向往船山公的特立卓行。先生克绍箕裘,远承祖业,近年又刊刻令先祖不少遗著,嘉惠士林,功德不浅。”而先锋历史叙事较多运用反讽、戏仿、拼贴等叙事技巧,对历史话语进行实验,探索语言的反常规使用,如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中戏仿手法的运用,袁绍戏拟马克思主义话语:“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嘛!”曹丞相检阅新军时。猪蛋大喊:“苏修必败,刘表必亡!”
其五,历史小说的传播媒介由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转换,传媒由单一的信息传播载体发展为文化产业,对历史小说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以《回到明朝当王爷》、《新宋》、《五胡乱华录》为代表的架空历史小说,就是在网络媒介上生成的历史小说思潮。在历史小说的接受方面,历史小说的受众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代际化和群体化。
四、历史小说批评亟待突破
个人化历史叙事时代的到来,不仅戳穿了元历史叙事的神话,而且冲破了传统审美观念,面对如此迅猛而剧烈的转型。如果再依据传统历史叙事理论去统摄复杂的创作现状无疑是削足适履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取得了较好的实绩,形成了巨大社会影响,但批评界的反应较为冷淡,甚至出现了尴尬的失语,暴露出历史小说批评的狭隘与滞后。
首先在历史真实与虚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学界普遍认为,历史小说必须遵循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原则,艺术虚构不能不顾及史实,而对其采取主观随意态度,要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制约:(1)史料的真实,如人物、事件、地点等,这是基本要求;(2)文化的真实,如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氛围、历史人物的文化心理、文化人格等,这是较高层面的要求。唐浩明、熊召政、刘斯奋、凌力等历史功底深厚的中年作家、为了追求逼真历史效果,“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的历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学界把上述作品当作达到历史真实的成功范例,并以此为标准把虚构成分较多的历史作品贴上了历史性不足的标签。如此说来,历史创作仿佛是历史学家的专利,没有深厚的历史功底则很难获得成功,于是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王小波的《青铜时代》以及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等大批非写实作品就只有被命名为另类历史叙事,被排斥在正统历史小说研究之外。
不可否认,上述观点对于传统历史小说创作无疑具有正确的指导意义,确实也产生了《曾国藩》、《白门柳》、《张居正》等优秀作品,而且在今后仍然占据不容置疑的重要位置。然而,如果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去评判所有历史作品,就不免暴露出局限性来。不同于写法较为单一的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元,许多作家为了追求艺术创新,大胆突破正史思维定势,探索表现历史的诸多可能,比如刘震云、王小波的作品故意打破真实的历史效果,让古今不同的历史人物穿越历史时空相见,其目的在于表现对压制个体的宏大历史的批判。20世纪80后作家则虚构出现实社会中的青少年,因突发事件穿越历史时空,凭借着自己的现代理念最终改变历史进程,从而将青少年特有的青春心理投射在历史中。如果严格用历史真实的尺度去衡量,上述作品无疑是失败的,甚至引发了是否还是历史小说体裁的质疑。由于评论界在历史虚构限度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导致作家不能放开手脚,创作成为正史所载史实的演绎。随着个人化历史叙事时代的到来,我们不能再以是否逼真再现历史情景作为唯一尺度,来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创作,从而忽视虚构性较强的历史作品。毕竟,历史真实并不等于真实历史,其本质只是艺术真实的一种表现而已,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历史真实,只存在历史理解的真实,且最终为艺术真实服务。
此外,还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历史小说批评仍局囿于传统美学观念,以至于阐释新兴历史创作现象时往往苍白无力,从而遮蔽了多元的大众化历史小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的无孔不入不仅彻底终结了宏大历史叙事,而且冲击着精英文化意义上的传统美学理论,历史叙事的启蒙与教化功能逐渐弱化,消费与娱悦功能前所未有地得到彰显。文化产业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下,生产出数量庞大的历史文化商品,呈现出影像化、平面化,拼贴化等诸多新兴特征,预示着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叙事的急遽转型。然而批评界却看不到这一重大变革,依然固守着纯审美理论体系,把大众化历史小说一律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动辄扣上篡改历史娱乐历史的帽子予以否定,导致其对当下新兴的历史课题,如历史小说与电子传媒、历史小说的接受与消费、历史小说的市场化生产机制的研究近乎空白。
综上所述,我们要以开阔的视野观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历史创作,避免将以某种类型的历史小说为标尺,去衡量其他历史作品,更不能以某种创作方法为模式,制约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和创新,这是历史小说进一步繁荣的重要保证。只要历史小说在历史性、艺术性与当代性三者之间达到和谐统一,侧重或淡化某一方面都是允许的,对于具有不同审美风格、满足不同审美需求、存在不同历史价值判断的多元历史创作,都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去研究。
责任编辑仝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