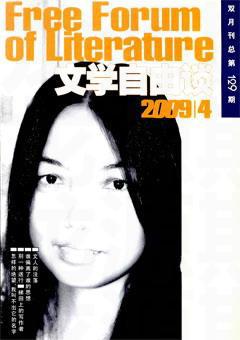梯田上的写作者
冉隆中
现在,哥布就坐在我面前,神色澄静,面带微笑,目光与我对视——但你分明感觉到的却是,他的眼神,正不由自主地看着别处。不是他在走神,而是因为他生就了这样一双眼睛,他似乎更留意余光观察到的影像世界。如此情形,本身就像是一个隐喻:他将肉身安置于滇南这座皇宫般富丽堂皇的城堡之中,而他的灵魂,却总飘浮在故乡梯田的山岚之匕。
这是2009年5月1日的午后。我从300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城池赶来,与蜗居于滇南小城蒙自的哈尼族诗人哥布再一次进行文学对话。地点在哥布办公室,它同时也是一家文学内部刊物的编辑部。哥布的现实身份,正是这家刊物的一名编辑。到处散乱着的书刊,使本来就逼仄的房间更显拥挤凌乱。惟有一曲名为“哈尼长街宴”的背景音乐,在电脑上反复播放,调剂着我们的谈话,略显轻松。
“我是一个母语诗人。在哈尼族作家群中,或者说,在哈尼族一百多万人口中,我都是惟一。”哥布这样对我说。当一个少数民族写作者特别强调自己的“母语”身份时,我知道,这其中一定有它很特别的意味。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少数民族作家只需要贴上自己族群身份的标签,就可以获得文坛的一份特殊通行证。这样的情形,类似于他们在节庆和盛会时的着装,虽然鲜艳夺目,却完全被符号化了。现在的哥布,强调的却是他“母语”的写作身份,也就是说,“母语”,不仅是他文学思维的材质,更是他书写的直接工具。他的母语,当然是哈尼语。进入到书写呈现时,则是哈尼文字——相对于古已有之的哈尼语言,哈尼文字要年轻得多——它迄今才诞生半个世纪。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才“创制”出来的一种以拉丁文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要以这种既年轻而且并未真正推广开来的语言文字去进行诗歌写作,这无异于是冒险。但是哥布对此却义无反顾。我知道他绝非是心血来潮。作为一名诗人,他已经有近十年未出版过一本书。那么,他都在忙些什么呢?
“我从来没间断过自己的诗歌书写。无论是被派去当乡长,或者去做新农村建设指导员,还是在这里编刊物。写作,永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法想象,离开了诗歌写作,我还能干什么。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比写作更重要的是,我对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写作意义的思考。”当下,像哥布这样四十多岁年龄的写作者,大多数都是在忙着匆匆赶路。写作,发表,获奖。更多地写作,更多地发表,然后是争取获更大的奖。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如此轮回,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哥布选择的却是停下脚步来思考,而且是颇为形而上的问题:写作为什么?
这当然是常识性的问题。写什么,为何写,为谁写,如何写?这些常识性的问题,对不同阶段的写作者都会产生困扰。比如哥布,一个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功成名就者,现在他遇到的问题,依然是回到原点,回到常识。
我在这里说哥布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功成名就者,并非虚夸,至少在云南是如此。放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序列中,大概也当是如此。一位见证过哥布写作史的老作家陈见尧就跟我说起过,“哥布,我认识他时,他才16岁,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他的文学才华,为他创造条件,后来在文学方面他有大成就”。陈见尧应该算哥布遇到的第一个文学“贵人”。因为陈当时不仅是一个早有成就的作家,还是哥布所在地区执掌意识形态的重要官员,因此他对少数民族年轻作家的发现和栽培就更有特殊而实际的意义。而那时的哥布,则只是一个初识汉语,以小学毕业身份就开始了小学教师工作的懵懂少年。偶然的误打误撞,让哥布进入文学之门,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从山村小学教师变为县文联编辑、再进入到州委宣传部、州文联,并且代表云南省作家,数次参加全国“青创会”、“作代会”,作品数次获“骏马奖”、云南省文学奖等奖项,并成为了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为他赢得诸多文学声誉的当然是他写作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作品,包括:《母语》(1992,哈尼和汉语对照)、《遗址》(1996,哈尼和汉语对照)、《少年情思》(1997)、《空寨》(1998)、《大地雕塑》(2001)等。
我注意到,哥布曾经走过的诗歌道路,其实是从汉语书写开始的。他写作发表最早的作品,是收在《少年情思》里的诗作。从1986年开始,在云南若干文学刊物上,人们见到了“哥布”这个在当时还很陌生的名字。他的《滇南》、《母亲》、《我在山谷独坐》等一首首诗歌,不断获奖,并引起人们注意。这个据说到18岁才学会讲汉语的哈尼族少年,是怎么在22岁时,就能在遥远的山寨,写出娴熟而且精当的汉语诗歌的,已经不得而知。我们来看他写于22岁(1986年)的一首题目叫《母亲》的诗:母亲从山里来看我/她不知道我的汉名/人们也不知道我的乳名/我的母亲问了好多人/人们都听不懂她的话//我的母亲在高楼下/矮矮的黑黑的走来走去/很多人陌生地看着她/她走累了
没有找到我/人们看见街边的墙角/一个黑女人甜甜地睡着了/(她在梦里一定见到了我)/她的手放在背篓上/里面是给我新做的衣服/……我的母亲没有找到我/她吃完树叶包着的糯米饭/就悄悄地走出了小城/看远山的炊烟这样温暖/她想儿子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要长大呢……
我在23年后再次阅读这首小诗,仍然会被诗里质朴而深沉的母爱情感所打动。这是古代汉诗《游子吟》的哈尼族当代版,而且诗里有一个更生动、更纯粹、更纯净的母亲形象。那个矮矮的黑黑的母亲,为已经进城的儿子送一件新衣,走了很远的山路,最终却迷失在语言和建筑的双重阻隔之中,然后悄悄地走出小城。平静的叙述里揭示着“走不进的城堡”这一隐喻,更传递出一种无助的乡愁和美丽的痛感,直抵读者内心深处。这首诗当然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哈尼民族色彩,但是它又是跨时代和超越民族地域的。在《滇南》、《我在山谷独坐》等诗歌中,我还看到,当时的哥布,居然已经娴熟地运用起汉语诗歌象征、隐喻、通感等手法,而且简洁、明快、质朴、生动,从一个细节、一个画面、一丝情愫的捕捉和描绘中,就能状难写之物如在目前。从那些诗行里,我分明感到,少年哥布确实有诗人天分。
比天分更难能可贵的,却是他在母族文化选择上的自觉。他还在文学起步之时,就选择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归依。他也许从那时就已经意识到,强手如林的汉语诗人队伍中,并不缺少一个刚刚起步的哈尼族文学少年;而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特别是用母语写作,去为并不成熟的本民族文字增添活力和魅力,或许才是自己更重要的本分。这或者可以用来理解当时为什么哥布已经完成了汉诗《少年情思》写作并屡获成功,却要先出版双语诗集《母语》的原因。
事实上,正是他这种文化自觉,无意中却更快地成全了这个有天分少年的诗人之梦。1992年,他用双语对照出版的《母语》,成为了他的一座文学标高。凭借着这部作品,他摘取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骏马”奖。比获奖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自己文学之旅的第二个“贵人”:于坚——这个被哥布视为自己精神导师的汉语诗人。
于坚对哥布的《母语》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在云南,朴素而沉默的高原上,听见像哥布这样的诗人的声音,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哥布的心那样美丽而朴素。听吧:乌鸦飞过田野/夏天呀夏天,山冈已恼人地绿了/一个孩子唱着催眠的歌
(《乌鸦飞过田野》)
……这个在大地上歌唱的孩子,常常令我想到那位同样朴素、简单的西班牙诗人洛尔伽。但哥布不是洛尔伽。他在云南的高山长大,红河流过他的故乡。他十八岁才学会讲汉语。这些诗是他先用哈尼文写作,再译成汉语。他是如此惊人的朴素,他的诗即使使用古老的汉语表达,也是那样单纯,令人怦然心动。我多次读过这些诗,多次为它们感动。我写不出这样的诗来,在当代也很少见到有和这些诗同样感人的诗。
于坚认为,哥布的诗歌是“从大地的根上发出的声音”。并且进一步指明,哥布诗歌的根不在别处,正在于其母族文化之上,母语文化之中。在于坚的鼓舞和启发之下,(当然,哥布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诗歌启发者,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随后,哥布也发出了自己庄严的诗歌宣言:操起母语之剑!“假如我的母语妨碍我的作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假如我必须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和走向自己民族之间作出选择,我将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地球上语种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少数民族大面积丧失母语的今天,我像堂·吉诃德一样操起母语之剑,是……因为作为诗人,我能做的仅仅是用母语写诗。”
用母语写诗,对于哥布而言,就是要用哈尼文来写诗。也就是说,他要退出原本好不容易进入了的汉诗写作竞技场,要改变自己符号化的族群身份,进而实现全面和真正意义的母族回归——从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开始,回到真正的起点之上,去发声,表达,对话。
这确实是一个惊人之举。它远远超过“换笔”的痛苦——比如从纸面书写到电脑书写,就曾经让很多人极大地不适应。哥布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换语言:从汉语回到母语。对于一个写作的个体而言,这无异于是一场艰难的战略转移。要告别一个已经适应并且斩获颇丰的竞技场,进入到完全陌生的无竞争领域,需要勇气、决心、耐力、信念,当然也存在着去领略无限风光的巨大诱惑。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商业的最高领域在于无竞争。所谓无竞争,说的其实就是垄断,这是多少商人梦寐以求的境地。这意思用到诗人哥布这里,难道不是同理吗?
正当人们为哥布走上一条诗歌的康庄大道而要额手称庆时,却无人知晓,这其实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回到母语写作的哥布,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哈尼族母语诗歌,在哪里发表?发表,是每一个作家和诗人存在的前提。而且,发表作品的文学刊物档次越高,通常也被认为作家诗人达到的档次越高。有诗人曾经跟哥布开玩笑,说《梯田文化报》等哈尼文报刊才是他的《人民文学》或者《诗刊》。这个玩笑其实近乎残酷。因为,即便是哥布参与创办的《哈尼梯田报》也基本是用汉语出版的。在哥布生活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真正用哈尼文出版的报刊,几乎等于无。据哥布本人参加调查并撰稿的《中国云南红河州哈尼族语言文字现状调查报告》称,“哈尼族语言文字工作开展得比较正常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些哈尼文报纸,如《哈尼文报》、《学习哈尼文》报、《求知》报等。此外,元阳县文联的《南高原》报出过一期哈尼文版;红河州哈尼族文学研究会的《梯田文化》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哈尼文稿子。至今仍然存在的只有绿春县大兴镇牛洪村委会阿倮那村几个农民自发办起来的《哈尼文化》报,该报2002年初到2004年底共出了24期,每期印数500份,主要读者是绿春县城附近村寨学过哈尼文的农民”。说到发表,哥布说,他倒“更愿意把自己的母语诗歌发表在哈尼文的报刊上,但这只是一种奢望而已,因为现在只有一份哈尼文报纸,就是绿春县的几个农民办的《哈尼文化》,要挤占这个一年也出不了几期的小报的版面,我实在不忍心”。这或者正是哥布从一个原本高产的诗人变得沉寂的原因。近年来,他无处发表母语诗歌。他发表在汉语文学刊物上不多的作品,是他先写成母语又由自己转述(翻译)而成的。对于这样的方式,哥布感到既别扭,也没太大的兴趣。他说他早过了追求作品发表的时期。但是,作品写出来,就是为了能有相应的平台发表。即便写哈尼文诗歌不能走向外部,走回自己民族也是不错的选择。问题是,现在好像连此路也根本不通。
在回归母语写作的荆棘路上,哥布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哈尼母语诗歌,读者又在哪里?这其实是跟第一个问题紧密相联系的问题。母语诗歌无处发表,就意味着找不到读者。但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即便有地方发表,用哈尼文字创作的诗歌,现在也基本找不到读者!还是据《中国云南红河州哈尼族语言文字现状调查报告》统计,哈尼族人能在生产生活熟练使用哈尼语,多数人却不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哈尼文。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哈尼族对政府为他们创制了半个世纪的哈尼文,基本处于隔膜状态。但是哥布并未因此而灰心。他找到了变通之途——将自己的诗歌变为“听”的艺术。他认为,哈尼族语言中古已有之的诗歌,其实就是“听”的艺术,而非“读”的作品。也就是说,它是以歌谣体的方式存在和传承的,是用来歌唱的,至少,是吟哦的——这让我想到古代汉诗,它不也是可以用来吟诵的吗?但是汉诗却同时是用来阅读的。我甚至认为,一切文字作品,只有在阅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她蕴藏的丰富美感。但是哥布却坚定地认为,他的母语诗歌是只属于“听”的艺术。“现在我创作的哈尼语诗歌越来越接近哈尼族的诗歌传统,越来越具有那种说唱艺术的特征(由于哈尼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她的诗歌一直是一种‘听的艺术而不是‘读的艺术)”。他在向我表述了这些观点后,原本沉静的面部表情开始变得眉飞色舞,他甚至忍不住地找出一首自己创作的哈尼母语诗歌,吟唱起来——全然不顾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根本听不懂哈尼语的汉人。他的吟哦,音调平缓,尾音绵长,似歌非歌,让我感到陌生好奇。而他的兴奋和急于表达,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正说明,一个当下的母语写作者,其实与他的读者是处于隔绝状态的。而一个失去读者(听众)的诗人,他该有多么压抑和孤寂?
还有第三个问题,哥布的哈尼族母语诗歌,要不要翻译为汉语?如果需要,那么,又该由谁来翻译?在哥布已有的几部作品中,他有两部(《母语》和《遗址》)是采取哈尼文和汉语对照方式出版的。这样看起来可以照顾两个读者群体。哥布说,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学习文学创作,一开始是用汉文进行创作并发表了一些诗歌。1989年后,他开始学习用哈尼文进行诗歌的写作。用哈尼文创作的初期,很难摆脱汉语的思维方式,每一首诗的构思都是汉语和哈尼语同时完成,很难说先用汉语写还是先用哈尼语写,只能说一首哈尼语诗歌完成的同时,它的汉语翻译也完成了。他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诗,从哈尼语的角度看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从汉语的角度看有着明显的哈尼语思维痕迹,读起来有一种新鲜感,可以明显地区别于其他人的汉语诗作,诗歌艺术上显得别具一格。但是他现在依然对这样的成绩感到并不满意。于
是他采取了直接用哈尼语思维,用哈尼文书写的创作方式。然后自己再给自己的作品进行翻译。在他看来,“这些诗歌在哈尼文文本里我感觉很满意,它们有着来自祖先的语言、节奏和思想,传承了哈尼族文化深处的很多东西,但是翻译成汉语后离汉语诗歌的欣赏习惯却更远了,所以汉文刊物的编辑和读者就面临一个重新适应我的问题。这些诗歌如果出自一个诗歌新人的手,任何。‘个汉文的刊物也不会发表,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之所以还能在汉文刊物发表一些作品,是由于我曾经多年用汉文学习写诗并发表过作品,同时仰仗刊物和编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应该说,哥布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客观的。看来他认为即便是自己的母语写作,也还是不能失去汉语读者。而且,如果写作者要跟世界对话,就必须走翻译之路一哈尼语不仅要翻译成汉语,如果可能,还应该翻译成更多的语种。但是,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并非翻译的正途。问题是,他如果不亲自翻译自己的作品,又有谁来翻译并且能翻译呢?
少数民族母语诗歌,该由谁来评价,或者是困扰哥布的另一个问题。此前哥布的诗歌也曾经好评如潮——至少在云南是如此。但是却都是来自汉语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发出的声音。而他们发声的依据是对他的双语诗歌的阅读,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对他的汉语诗歌阅读后做出的评估。于坚认为哥布的诗歌是“从大地的根上发出的声音”,诗评家胡彦则认为哥布的诗歌有一种“诗意的澄明”,另一个诗人和评论家马绍玺对哥布诗歌也是赞不绝口,以为已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我在数年前写作的《云南当代文学简史》中,也曾经对哥布做出过如下赞美:“他的双语诗歌文本,既有为本民族书写,让本民族读者阅读,在母语写作中能找到更合适的表达方式的多重意思,又有与外族交流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作为汉族的阅读者,我们无法猜测他在母语写作中有哪些是属于‘更合适的表达,仅就我们阅读的汉语文本,我们已经知道,哥布用诗歌建构起来的独特的精神世界,是多么让人神往和迷醉。……哥布用诗歌对我们现存文明社会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从而表达了他的生活理想。”直到今天,我认为,对哥布诗歌的这些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问题是,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的评论,都是从他的汉诗出发的。那么,他的哈尼族母语诗,又该由谁来进行恰当而准确的评估呢?
似乎,谁都不能。比如我,我根本不知道哥布的哈尼母语诗歌作品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天书。但是作为一个调查研究者,我必须一直追问哥布,并且找到可能进入的一条路径。于是,我看到了哥布付出数年时间,悄无声息地蜷缩在滇南大地一隅,以哈尼文字写作完成的一部名为《哟咪哟嘎,哟萨哟窝》(翻译为汉语即《神圣的村庄》)的长诗。这首3300行的长诗,它的叙事者(吟唱者)由诗人、咪谷(寨子里的宗教领袖)、摩批(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县长、巫师、村长、当家的男人、当家的女人、男青年、女青年以及众人等多种角色组成,全诗分为十章,除序诗和尾声外,另有祖先、寨神、寨子、梯田、公路、电、县城、红河、个旧、心愿等十个章节。我能看懂的是已经被哥布自己翻译过来的“序诗”“读诗”等片段。但是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或者说不懂得欣赏现在哥布的写作。正如哥布自己所说,这些诗行“翻译成汉语后离汉语诗歌的欣赏习惯却更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从已经读到的部分,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向后转”的作品。即:从现代诗歌退回到初始歌谣,从人的审美的文字的现代诗歌,退回到神的宗教伦理的口头的古代歌谣。如果我的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它印证了诗歌评论家马绍玺关于20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诗歌现代转型的某些观点——只是它刚好呈相反方向。这样的方向,难道真的是对的吗?如果是错误的倒退,那么,诗人哥布为此而做出的努力,岂不要付诸东流?但我又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只是站在俗人的立场上在为哥布担忧呢?
我面对的哥布却是依然澄明澹定而宁静的,一如他以往那些让我心仪的汉语诗篇。但是他自己却更喜欢他已经写的和正在写的,那些让我不能欣赏的哈尼族母语诗歌。他也坦承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但是他不会为之动摇。他已经坚持了十多年时间。他从一个书斋诗人变为了一个行动诗人。他最近的一次行动是在2008年6月22日。地点在云南省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委会箐口村。他召集的10多个“摩皮”、哈尼族文化专家、歌手、学生或者农民,聚集一处,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母语诗歌《哟咪哟嘎,哟萨哟窝》讨论会。通过作者哥布和与会者的朗读,对长诗全文进行了认真“阅读”(倾听),并对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或建议。与会者还就长诗中涉及到的尚未用哈尼语命名的名词,如汽车、公路、电、城市、飞机、电视机、照片、手机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参照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国的哈尼(阿卡)语称谓,用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哈尼语进行了命名。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有可能成为传统哈尼族社会与现代化之间的一座精神桥梁。并建议把作品制作成VCD光盘,让寨子里的人能够听到它。哥布做着这些事情时,是一丝不苟的。没有名,也没有利——至少现在是如此。他认为名和利是与成功有关的事情,而与诗歌理想无关。他需要成功,因为他必须为无业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幼儿负责。但是他现在却过着没有稿费也基本没有其它收入的简单日子,一家三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500元——即便在滇南小城,这也是很低收入家庭了。然而这些却没影响哥布关于母语诗歌的理想和信念。他还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吟唱着:今天是属鸡的好日子/今夜是属鸡的好夜晚/我们父子相见的一日/我们兄弟聚会的一晚/让我们的歌声飞过红河/让我们的诗歌传向远方/把我们心里想的话统统唱出来/把我们眼睛看到的全部说出来/好听的歌不要藏在心里/好看的风景要互相指点……我感觉到,他的肉身虽然安放在辉煌城堡,而他的心和灵魂,分明还是留在他故乡元阳县一个叫热水塘的梯田之上——那正是他的衣胞之地,他现在比从前更像一个梯田里插入诗歌秧苗的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