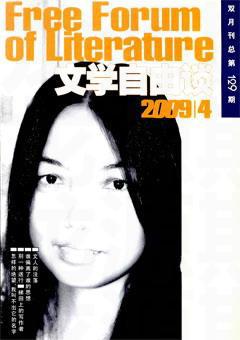《南京南京》的日本感觉
陈 冲
日本有个电影导演叫黑泽明。他被奉为电影大师应无疑义,但我们的评论界几乎不提他对武士道精神的崇尚,更回避论及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和一部分日本人一样,他对于广岛、长畸的“原爆”很痛心,但不认为应该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上找原因,只认为死于两次原爆的日本人是受害者,而加害者美国人应该就此道歉。直到晚年,他也没有等来这个道歉,遂于1991年拍了一部叫《八月狂想曲》的影片,里面有一个弯弯绕式的情节:主人公是位日本老奶奶,她的弟弟后来移居美国,收养了一个有美国血统的继子,在这个继子得知姑父(也就是老奶奶的丈夫)是死于长畸原爆时,千里迢迢来到日本,向老奶奶就原爆(代表美国?)表示了道歉。于是老奶奶也就淡然地说:没关系了……我从盗版影碟上看到这部影片时,第一反应是:这种一厢情愿是典型的精神“自慰”。更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这种“自慰”的荒唐性就被无情地予以证实。2000年,一个名叫蒂贝兹的美国大兵,当年把原子弹投到广岛的美国飞行员之一,打破保持了55年的沉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轰炸广岛,我从不内疚,也不后晦!”他还毫不含糊地说:“如果还遇到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我还会愿意干的!”
电影《南京南京》(当中那两个感叹号既没用又看着别扭,从略),再一次干了这种荒唐到滑稽或滑稽到荒唐的傻事。我们都知道,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事实,日本政府和相当多(究竟占多大比例我们好像从来没弄明白过,只好从略)的日本人,采取的态度是不认账、不认错、不道歉、不反省、不忏悔。这五个“不”,是“日本可以说不”的典型实例。东京审判的时候,他们还不敢这样说,到了“日本可以说不”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很“坚决”,从而形成了他们对那段历史事实的历史判断。作为一种立场,这个历史判断从来没有改变过。看起来,这让编导陆川先生很着急,就在影片里设置了一个日本兵,给他取了一个日本名,姓了一个日本模样但少见有日本人使用的姓,让他在一群兽性发作的日本兵中间罕见地玩了一个“人性的觉醒”,并最终以自杀来表示——表示了什么呢?这就算是“谢罪”了吗?我还真是说不好。
日本(日本国、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以日本政府为代表,对南京大屠杀采取的这种“五不”态度,确实让人着急——不过应该是替他们着急,不是我们自己着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对于中国、中国人来说,这个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只对日本人重要。对日本人重要的事,应该让日本人去想,什么时候他们想明白了,真心地认账了,认错了,道歉了,反省了,忏悔了,我们宽容地予以接受就行了。我们应该想那些对我们自己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很复杂,天天想都想不过来,而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放着自己的问题不想,却急赤白脸地去想应该由日本人去想的问题!从同一个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加害者和受害者所应记取的教训是不同的。对于日本、日本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再发生蒂贝兹所说的“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而他们的“五不”态度,危险性正在这里。我们也要防止再出现“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但这个“情景”对我们和对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杀人!我们是被杀!我们要想的,是怎样才不会再次陷入这种任人宰割的境地,不会再次成为别人兽性发作时的宰割对象,不会成为“百人斩竞赛”的目标物。我们希望他们“不来”;但究竟来不来,最终取决于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来了也不怕”。他们自己不反省,倒由我们先假装变成了他们再代他们反省,算数吗?管用吗?虽然电影院里放电影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也不能这样当众自慰呀!
据说《南京南京》有两项“突破”,一个叫“人性”,一个叫“反战”。虽然这两个词语很时髦,但硬要拿南京大屠杀来说这俩事儿,太离谱了吧?什么叫南京大屠杀?就是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在南京城内外,有30万个中国人的生命被毁灭。发生于此前的南京保卫战,是另一个历史事件。那倒是战争。在那场战争中阵亡的中国抗日将士,是不算在这30万人之内的。这30万被屠杀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平民,包括大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余下的、比例已经不大的中国军人中,真正死于战斗(也只是那种最后以命相拼的战斗)的又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的散兵,和已经投降的俘虏。这是真正的屠杀,根本不是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儿只有抗战不抗战的问题,根本没有反战不反战的问题。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还去跟人家讲反战,讲人性,讲得下来吗?在南京大屠杀这个特定的事件中,这两个话题,只有“为刀俎”者才可以讲,“为鱼肉”者是没资格讲的。陆川先生却来讲这个事,看来他真是找到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感觉了。
面对30万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人被恣意杀戮奸淫,一个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感觉?比如说真有一个日本人在检讨这个历史事件时,不是从他们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上反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兽性大发作,而是强调还有一些日本兵人性未泯,我们能不能接受?再比如,那30万个被杀害的中国人,他们在被杀害前的“表现”重要吗?他们是昂着头去死还是低着头死去,是高呼“中国不会亡”去死还是在极度的惊恐或非人的折磨中死去,重要吗?更或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国家”已经不再去或不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时,还要求他们死得有“骨气”,荒唐不荒唐?有人说,正是这“骨气”让人看到了希望,这就更荒唐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只会昂着头去死,这个国家必定毫无希望!
面对30万这个巨大的、让人无比震撼的数字,一个中国人最痛心的应该是什么?不错,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今后要努力富民强国。但是这就完了吗?国有强弱,战有胜败,在世界历史中,一个国家弄到保护不了自己子民百姓的程度,南京大屠杀并非孤例,但是被杀害了那么多人,实属罕见。日军的极端残暴是一方面,在我们这一面,除了人口密度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我们能不能少让人家杀掉一点?显然,这不能靠杀人者的“人性觉醒”,只能靠让杀人者付出更高的代价。代价高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得不少杀一点了。在南京大屠杀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出现过有组织的、有效的抵抗——退一步,哪怕是出现过有组织的、有效的逃离——再退一步,出现过哪怕是无效的、但毕竟是有组织的抵抗或逃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想想这个,却要拿临到被杀害前“不低头”当“正气歌”来唱?不觉得这也是一种任人宰割者的精神“自慰”吗?那些低了头的死难者就不是中国人了?就不该甚至不配受到我们的追思、悼念,就可以不算在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上?我知道我说这个话所要承担的风险。我和现在的愤青们所受的教育不同。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教导我们要记取中国被侵略、中国人被杀戮的种种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像“一盘散沙”。老师们也讲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没人再说这个话了。然而,这是进步吗?
我知道现在来做这样的反思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没有鼓动别人、尤其是晚辈去膛地雷阵的意思。法捷耶夫写过一部《青年近卫军》,描写克拉斯诺顿的青少年,自发组成“青年近卫军”,与纳粹占领军斗争的事迹。斯大林看了据以改编的电影后勃然大怒,因为这些青少年的行为是自发的,他质问道:“共青团的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实际上,在当时大溃败的情形下,那些被占领地方的领导人多被杀害,领导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不会不知道这样的事实吧?
不想中国人该想的事,却替日本人去想他们该想的事,是荒唐。拿日本人该想的事,来遮蔽中国人该想的事,是罪过。如果实在说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那么就低下你的头,为那30万亡灵祈祷吧!这样做好像不怎么够,其实已经够了。至少没有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