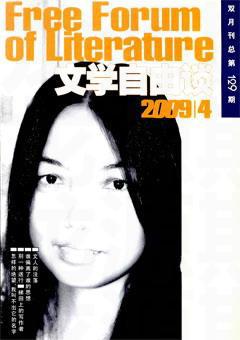怎样的绝望,我叫不出它的名字
严英秀
关于那一切,我多么不愿再回想。然而,我只能面对,我必须担当。当我的名字无可选择地和一个抄袭者的名字纠结在一起,我就注定了要承受生命中这突如其来的被损害,被掠夺;当我在感受着太多公道正义的温暖的同时,也无端地被猜疑,被诋毁,甚至被恫吓。那时,我就知道了,善良只能使善良者蒙羞,而宽容将会怎样地被无耻和黑暗所用。
“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
杜拉斯如是说。
我等着这样的拯救已经太久。而写作尚未降临。似乎永不降临的样子。我惟有投身于这无边无际的洞穴之中,等待写作的脚步,划破密不透风的孤独,向我走来。但事实上,我惟有倾听着太多虚妄的真相,太多疼痛的追问,一步步向我走来。
怎样的写作,才能拯救一个写作者的灵魂?在今天,我还能触摸到这样的写作吗?
不能不提到这个春天,这个五月。从去年的五月到今年的五月,这么多不平常的日夜。让人泪流不绝的人和事蔓延不休,未曾停止。还有,关于文学。这一年,灾难中文学没有缺席,文学应声而起,爆发出了“井喷式”的热情和责任。整整一年来,从祖国的西南到西北,我们走在伤痛中走在希望中,也仿若走在诗歌的抚慰中。今天,终于所有的感动都到了可以回望可以总结的时候了。据多家媒体报道,作为地震重灾区之一的甘肃,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异常活跃。震后第一时间,甘肃文坛组织了“诗歌之夜”大型朗诵会。随后,诗人们亲赴灾区,写出了大量作品。2009年5月15日,“5.12全国抗震救灾文学研讨会”在兰州举行。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这是些我几乎熟悉的人。然而,除了无言的崇敬,我无法融入他们。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也算是一个写作者,然而,千首诗歌中,没有我的一丝声音。那么多铺天盖地的激情文字中,竟没有一个字是我走过的“5.12”。
还是在去年,地震后十几天,网上曾有这样一张照片:两个农村小孩,一个五六岁的样子,一个更小些,他们靠坐在墙缝斑驳的土屋里,茫然的眼神盯着镜头。照片下的文字说:他们的妈妈已经被地震夺去生命,但孩子们不知道。孩子们正在等妈妈回来做饭。
那当然是一幅让人极其心酸的画面。但在那个时候,那也只是一张平常的照片。太多的苦难、泪水、感动已经麻木了神经,许多时候我们只好匆匆一瞥,眼睛又朝别处看。
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我亲戚的孩子,是在多日以后。暑假里从省城匆匆回到白龙江畔的县城。父母的孤独晚景里又多了一层劫后余生的凄惶。连日余震不断,江边河沿和小小的广场上,挤满了人和帐篷。然而,父亲不离老屋,他说逃哪儿去都逃不过命。我惟有守着他们,一天天熬到天亮。我知道我正和许多的人摸索在同样的遭遇中,我知道我其实幸福完好得无以复加。然而,这样想过之后,孤独还是一样的,恐惧还是一样的。没有一个时候,一种来自群体的同在感可以全然地抹煞个体的疼痛。
所以,面对我身边的故事,面对四川,我说不出一个字。
那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个29岁的我的亲戚女人,在天气晴朗的5月12日是去采摘一种叫乌兰头的野菜的。在长期的挨饿年代,乌兰头曾是人的救命菜;在青年男女背着背篓唱着山歌呼朋唤友的田园风光里,乌兰头也是一份浪漫的农业记忆。现在,太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剩下的人渐渐失去着对手里的庄稼地的热情,山野村头,还会有谁以热切的目光去打探乌兰头在春天的花信呢?除了那些不但分外勤快也还讲究点生活的意思的年轻媳妇。
我的亲戚女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中午饭后,去摘野菜,她说她要给孩子们尝点鲜。然而,一阵巨大的山体震荡中,她被滚下来的大石头击伤,她背篓里青葱的野菜顷刻间成了血色。同死的,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人。
我知道这些后,好长时间里都不能去看看照片里的那两个孩子,那两个亲戚的孤儿。我不知道我该去做什么。已经有一些远方的人看过他们了,送给他们好多文具盒,和漂亮的新书包,用他们听不懂的普通话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一定要坚强。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我一遍遍想象着那两个孩子,我不明白那样两个孩子。我不明白那么多的孩子,为什么瞬间就没有了妈妈,为什么瞬间就告别了童年?他们本该选择游戏,却偏偏得选择学会坚强?
我不是不知道天灾人祸的道理,我不是不相信生命总是在这样的磨难中成长和升华。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沉溺于太过狭小的经验世界中。我常常神思恍惚,泪水总是在不经意间跌落。疼痛的感受是一把无法甩开的碎金,我握着它们。它们有尖利的光芒,但在我凌乱焦躁的思绪里,它们无法结晶成一句恰如其分的表达。
余震基本平息后,去了丈夫的老家。那是灾情一般的山村,没有人死于地震,只有牲畜。和过去的许多次一样,刺疼我的双眼的依旧是贫穷,甘肃南部山村极其典型的那种贫穷。地震似乎没给这儿带来什么大的破坏,所以也看不到灾后重建的新气象,虽然好多土墙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些旧标语旁边,又新刷上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大红字。村口依旧是眼神呆滞的老人,和看见小汽车就一哄而上看热闹的小孩。
然而,变化还是有的。许多人家的房屋都明显倾斜了。公公说不碍事的,能住就行。如果推倒重修,公家给两万块钱。两万块钱能修房吗?不像从前了,木头、石头都得掏钱买,一块砖从坝里拉到山上就一块几,谁敢为两万块钱推倒这还能住人的房子?公公说,地震后,公家发给每家一袋面,还有,今年的农忙时节,大家都闲下来了,因为来了几十个兵娃娃,把家家的麦子都抢着给割了。公公说着从堆放什物的偏房里扯出来一个巨大的包裹,打开给我们看,里面有半新的羽绒服、毛衣、裤子,挺时髦的T恤衫等等。公公还拿出来了一双尖高跟的女式靴子,笑着说:你们看,公家来人分配的,一分就这么多,人家也不知道咱家有没有女娃,就摊上了这些东西。
我无语。我难以想象,就算有女娃,在这样的山庄里,这样的一双靴子穿在她的脚上,是什么样子。如同我难以想象那些凝聚着全国人民爱心的捐赠衣物,那些写着英文字母印着奇怪图案的毛衣T恤,穿在我的公婆身上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公公展示完毕后,极其郑重地叮嘱我们:我看这些衣服够三五年穿,你们俩以后可再不敢给我们买衣服了。他笑着说:现在公家的政策可确实好啊!
我公公的笑,那从道道皱纹里绽开的阳光般由衷的笑,在那个下午是那么地感动了我的心。那样的感动,就像是一种刺痛。
这些,都是一年前的事了。一年来,我也曾试图写下点什么,像所有的写作者那样,以文字表达痛惜和怀念,以文字温暖伤悲和残缺,以文字记录生命与尊严,以文字见证平凡和伟大。然而,我总是泣不成声,笔不成句。如何记忆,如何纪念,如何抚慰,如何重建?如何如荷尔德林所说,在神圣之夜走遍大地?如何在伤痛之夜,走过自己?如何在和平的太阳下,真正地想起那些没有了妈妈的孩字,和没有了孩子的妈妈?
一年了。一年里,在我们这片共同的故土上,发生了太多,泯
灭了太多。最初的万众一心中,我们曾寄希望“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中国”;当诗人们冲破多年的沉寂和边缘,终于集体性地发出声音时,我们也相信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诗歌涣散的灵魂终于凝聚成了不倒的旗帜。然而,一年过去了,许多时候,放眼望去,重建的只是村庄和城镇的物质形态,泪雨纷飞中喊过的那些口号,正在一点一点地沦落为作秀的工具;一年过去了,诗歌也并未恢复曾经的荣耀,那太多的激情澎湃,只成了应时应景的一堆文字残渣。
当然,变化总是有的。希望是有的。那些重生的故事,那些灾区的孩子,那么多志愿者的足迹。那是神州大地一年里绵延不绝的感动。还有,那些在安静地思考的写作者。然而,我依旧难以提炼难以整合,我无力对世界的驳杂,对自己的失语做出沉淀和反思。我不知道经过了去年的五月,在流下了那么多的泪水后,清明沉静的日子为什么还是和我们的心灵遥不可及?我不明白在今年的五月,我为什么陷入了如此更为深重的困惑和绝望?
尤其是,从“5.12”纪念日的前夜,当我身不由己地走进一场有关文学的是非漩涡;尤其是,当神圣的文坛这么偶然而又必然地向我展现了那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当那海面下冰山的一角一点一点地露出。
现在是六月。关于那一切,我多么不愿再回想。然而,我只能面对,我必须担当。当我的名字无可选择地和一个抄袭者的名字纠结在一起,我就注定了要承受生命中这突如其来的被损害,被掠夺;当我在感受着太多公道正义的温暖的同时,也无端地被猜疑,被诋毁,甚至被恫吓。那时,我就知道了,善良只能使善良者蒙羞,而宽容将会怎样地被无耻和黑暗所用。这是多么奇怪的事,这是些多么让人看不清面容的人啊!他们好心地提醒:“你知道那人的背后是谁谁谁,还有谁谁?你斗得过吗?你是一个疏离于文坛的教书人,你不知道文坛水有多深,就这点事,忍忍就过了,千万别把自己搅和进去!”他们积极地游说:“让她给你私下里做出经济赔偿,如何?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于人于己都留个后路!”他们恶意地威胁:“抄袭之事自古有之,你捅出来就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媒体是双刃剑,搞不好大家鱼死网破,谁也别想混!”许多天后,那被许多人认为极不真诚的“我的道歉”问世后,我又在第一时问被告诫说:这是“中国文坛抄袭史上史无前例的道歉”,所以要心怀感激地接受才对,要“见好就收,适可而止”……
所有这些。这些好心的恶意的浊流,就那么袭卷着我,袭卷着我小小的反抗。我要一个真相,它来得多么不易。是的,见好就收。但为什么,我只能如此尴尬地卑微地见到这么一点“好”?我为什么没有理由追求一个更好的“好”?比如文坛环境的整肃净化,比如人和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比如对“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些简单的社会伦常的尊重?
我要怎样才能“适可”,怎样的姿势才能使我不从一个隐忍的受害者被妖魔化成一个恶意炒作者?我是多么傻啊,我一直坚信善恶自有公断,是非不可以混淆。而今,年近四十,我才明白,善恶的界限是如此微妙,善如果自恃为善,而敢于抓住真相不放,而敢于越人情世故的雷池一步,就会被毫无疑问地打入恶的行列。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真相,他们不要真相。他们左右逢源,平衡事态,他们看上去多么善良。然而,不能求真不愿求真不让求真的善,是一种多么恶的伪善啊!
一个小偷在公交车上偷人钱包,被发现后百般抵赖不成,只好承认说那是别人的,不是我的。而旁边立即就有人响应:承认就行了,道歉就行了,还要怎样?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偷你一点东西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你不依不饶,想达到什么目的?这种情形,但凡有眼,谁都可以看出那些很“费厄泼赖”的人若非帮闲,必为同谋。但文坛的事没这么一目了然,文坛云山雾罩,坛外人往往难测高深。所以,一个编辑老师打了上面那个比方。我喜欢听他说话,他总是用打比方这种很“前现代”的说理方式简单直接地拨开迷雾,呈现真相。
其实,真相多么简单。难的是把它说出来。
我是多么厌倦。一个多月来,耳朵里天天灌满了文坛这个词。厌倦早已压倒了愤怒。是的,我不知道文坛水有多深。从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1996年开始专门的文学教学,到今天,我还只是一个疏离于文坛的“文学爱好者”。我爱文坛,也愿意相信它的神圣,但如果,在今天,我被太多的人告知,这眼前的丑恶、污浊和黑暗就是文坛,这些毫无耻感的偷窃者,这些以权势亵渎着文学的同谋帮凶们,这些失却了良知准则的好心人,这些明哲保身的苟且者——他们就是文坛。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唾弃这样的文坛,永远地自绝于它。
6月2日的早晨,身心俱累的我走向课堂。然而,就在我站到讲台上,看到台下学生眼里的热忱、期待和热爱时,有一种力量神奇般地复苏。就在那一刻,我懂得了自己的宿命。是的,我可以不是作家,可以从此不沾染文坛,但我永远不能逃开文学,逃开这被那个叫顾彬的德国老头斥之为垃圾的“当代文学”。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安身立命的根基。这一茬又一茬来到我面前的孩子,我对他们有着命定的责任,我必须得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的文学,什么是文学的尊严?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学,为什么文学温暖人心安妥人性的力量在现实的时态中日见稀薄?又为什么,一个粗俗恶劣的时代是短暂的,但文学澄明、广大的境界肯定是跨越时空的?
就是这样,就在这个我无数个教书日子中的平常的一个早晨,我决意不再逃避,不会先自离开我的这一份遭遇。我这才真正走进了我的担当。也就在那个早上,从去年的五月到今年的六月,整整沉默了一年之久的我,重新渴望写作。我在充分地懂得了自己认知的局限,懂得了倾诉的无力之后,仍然如此地渴望写作。尽管我知道,在广大无边的文学的星空里,我始终是连自己都听不见的一个微弱的声音。尽管我更知道,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太多的心碎被漠视,甚或被践踏,太深的痛苦和忧患无处置放。然而,我还是无可救药地渴望写作。不能被说出的生活,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是无法想象的。
杜拉斯说:作家的审核职责往往是针对自己的。于是作家变成了管自己的警察。我经常想起这句话,在目睹了近年来花样不断奇峰迭起的“文学现象”后,在这个五月自身也如此地经历了淬心砺骨的“文学遭遇”后,我才开始明白这句话的重量。我愿意做一个管好自己的警察。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变成管好自己的警察。因为,外面确乎是一个多么喧嚣而模糊的世界,文坛是一个多么容易迷失自我和本在的地方。也许,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幸免?也许,全世界的文坛大抵如此?因为还是杜拉斯,她说:那些垂死的人在写一些羞羞答答的书。甚至有些年轻人在写一些吸引人的书,一些没有发展,没有黑夜的书。没有沉默。换言之,没有真正的作者。一些白天的书、消磨时光和外出旅行时看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反映生活悲哀和思维模式的书。
我仍然想要怀念。在已然过去的五月,在热浪扑面而来仿若要蒸腾尽一切记忆的六月。我怀念那个在晴朗的5月12号去采摘野菜的年轻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怀念祖国西南那一片苦难的土地上重生的春天,那么多走下去的妈妈和孩子。以及,更久远年代里的那些流血和牺牲。那些被自由的热望所掩埋了的躯体。怀念所有残酷的成长。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人们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我自然不希望他们死掉,我也懂得他们的不会死掉。但是,现在,六月的热浪扑面而来,仿若要蒸腾尽一切的记忆。那么,我愿意低下头,面对自己的内心,默默地浇水,把伤口都看成忘却的花朵。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泰戈尔说。但我依旧唱不出歌。我惟有等待。久久地等待写作的拯救。一种黑夜一般的写作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