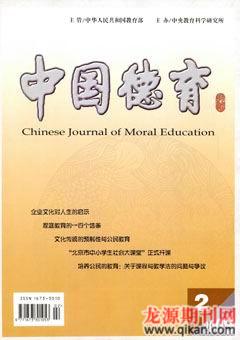文化传统的预制性与公民教育
李 萍 童建军
摘 要 文化传统潜在地影响着一定社会人们的生存样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深刻的预制性功能。所谓文化传统的预制性,是指特定的文化传统对现实的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而显现的潜在、先在和先天的制约性和影响特性。这种文化传统的预制性可从根源性、特殊性和生存性的角度去理解,公民教育的定位必须考虑以此为前提。
关键词 文化传统;预制性;公民教育
作为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和核心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公民教育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合法性为底线,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它由此表现为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主体性教育与平民教育特质,并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1]公民教育是世界性的,它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公民教育又是民族性的,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成为它的预制性因素,影响着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公民教育的展开和公民教育的设置,使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其内涵所及与包容的是一个变数。
一、一个调查引出的问题
我们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通过半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提纲,以笔谈和口谈的方式,总共访谈了广东省部分高校200名大三和大四的高年级法律本科生,调查研究他们接受法律专业教育后的人情观念。
调查表明,98.5%的学生认为,在中国法律实践中服从人情法则,是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发生影响作用的必然结果。在他们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干什么都要适当地考虑人情因素。因此,司法实践中的人情是一个传承下来的习惯,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潜规则,是一个深深地刻在我们民族内心的印记。
95%的学生指出,当代法律实践强调人情法则的规范作用,是很多法律工作者适应残酷的社会现实需要的选择;法律教育灌输法律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可是社会现实逼迫个体逐渐卷入人情的大熔炉,公正廉明等法律职业道德要求最终只能在顺从人情的大潮中被遗忘。他们认为,律师在法律代理实践中如果要接收到案源或者能够在诉讼中取胜,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还必须多与公、检、法各个机关部门的人员,通过人情的运用,建立良好的关系。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深谙国情,为了赢得诉讼,往往优先选择与司法系统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厚人脉的律师。
57%的学生认为,人情干扰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甚至使人们失去了对法律工作者与法律的信任。在他们看来,当人情介入时,司法的公正诉求就变了质,换了样。沉重的人情负担使得中国很难实现司法独立,从而无法保障司法公正。法院在审理一个案件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些其它方面的因素,包括来自公、检的,也包括来自律师的甚至犯罪嫌疑人的,这些都会影响到司法独立,影响到审判公正。
在人情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100%的学生选择服从人情的需要。他们认为,人情是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情无处不在,世人无法离开人情而存在。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问题,并非势单力薄的法律专业人士朝夕之间所能改变的。既然无力改变,就应该接受。以法律的公正理想抵制社会的人情现实,反而可能会陷自己于不利之中。在一个人情味很浓厚的社会氛围中,如果个体仍然坚持“包公审案”时的不阿情怀,最终可能遭受社会现实的遗弃。
90%的学生认为,要改变中国司法领域的人情现状,从长远而言,取决于人们价值观念从群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变迁。但这种转变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因此,他们提出,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可行方案,我们只能依靠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司法监督制度、司法准入制度等,加强对司法行业与司法过程的规制。同时他们也对这种设想能否落实表示了深层担忧,指出如果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仍然以人情为主导,那么这些制度设计也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切实遵循。
众所周知,“人情”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维系交往关系的工具。它是社会生活中公认却又未能或无需明言的行为交往准则,正如学人指出的“关系、人情和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摆脱不了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主线;另一方面,我们所调查的对象,都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基本没有接受传统文化的正式教育(指学校),甚至是成长于传统文化受到全面反思、扬弃的时代。而且作为法律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他们接受的专业价值观与人情文化观念恰好是相悖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却有着如此明显的人情文化的印记呢?
二、文化传统的预制性
所谓文化传统的预制性,是指特定的文化传统对现实的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而显现的潜在、先在和先天的制约性和影响特性。包括80后在内的现代中国人,正生活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交错汇合中,生活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维文化向度共存的空间里,他们是现代的,亦是传统的;他们是传统的,同时又是后现代的。传统文化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样式和思维方式,同时使得文化的发展主要地不是表征为普遍的和制造的,而是呈现出经由历史延续而培育的特征。文化传统的预制性可以从其根源性、特殊性和生存性去分析。
1.根源性。每一文化必有其源头,也就是文化的根源。从源头到支流是一整体。从支流的角度而言,经过时间的流逝后,源头就成为传统。现实的文化无疑正是这一条条支流,它们最初始的传统就是其各自的源头。源头不同,那么经源头流淌出的支流会存在差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通过对其“轴心时代”观念的展开,从理论上论证了文化多元性的“原初”根源。在他看来,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了许多大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反思路径出发对宇宙人生等根本性问题作出了思考,这些反思路径又是迥异而互不影响的,由此导致了经此路径发展而来的各民族精神文明形式的差异,成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构成不同民族生存的“集体意识”,世代影响并塑造着个体生命。杜维明在分析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的历史论证的基础上,得出鲜明的结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倾向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多元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而不同“轴心时代”的文明有不同的源头活水,不同的精神资源,不同的潜在力,不同的发展脉络。这种“源头活水”的根源性差异导致当今世界各种现实文明的差异和人们思维习惯、生活样态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时,认为东西方曾经走了两条不同的途径,即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和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古典的古代”是从氏族到私产再到国家的进程,个体私有制冲破了氏族组织,而后国家代替了氏族。“亚细亚的古代”则是由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到国家,国家的组织形式与血缘氏族制相结合,我国古代奴隶制的形式可以说就是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如侯外庐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有)、国家”三项作为人类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中国氏族公社的解体和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是从家族制、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中国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2]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由此表现出明显的处理社会事物时的家庭化和亲缘化倾向,强调通过人情法则的运用,在彼此之间发展和维系关系。
2.特殊性。儒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的。[3]96因而人是人伦中的人,是在人我关系中被定位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考证,“仁”从二,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个体并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在复杂人际关系中显现的中心点,是人际社会相互依存关系中的网结。“我”是谁?我就是关系,是关系的产物(父母关系的结晶),是关系中的角色(相对最早的关系父母而言,是他们的孩子)。正如有学者考查中国文化中“人”的概念时指出的:“人与我对称,使人、我两称谓的意蕴显得十分明确。与‘我对称的‘人,是指我以外的、与我发生关系并具有与我同样意识的别人或他人。人与我总是相比较而存在,舍我无人,舍人无我。……在人我关系之中,我为一,人为多,从而使我处于人我交往的轴心地位。”[4]孔孟看来,人一生下来就离不开对父母、对他人的依赖,离不开特定的群体关系,这是人之为人的天性。儒家正是基于这种认定,推演出了其全部的伦理原则、规范及实现道德目标的方式、途径。任何个人都必须寄寓于特定的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维护、协调自己所处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或“我”是依附某种群体及其关系而存在的,个体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关系本位的社会系统中,主体不把重点放在任何一方,而是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3]93有些关系是基于自然血亲而形成的,但更多的非自然的关系则是个体在生活中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人情作为发展和维系关系的一种规范,它所调整的不是有着深厚的自然血亲基础的父子兄弟之间,也不是彼此陌生的外人之间,而是熟人之间。通过人情法则的运用,交往双方可以使工具性的关系情感化,使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亲缘化,从而使对方做出有利于己方的行动安排。这种文化传统成为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型塑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
3.生存性。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搜集的资料显示:文化的定义多达160种以上。无论对文化定义如何诠释,它与人类生活的内在关系都是极为紧密的。梁漱溟把文化直接定义为“人类生活的样法”。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的样法”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说文化传统对人类生活的“样法”有着无形的、潜在的和极大的影响。因此,即使在生产力水平、经济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类生活样法也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彼此的生活样法就会有差异。梁漱溟指出,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种路径样法: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他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面要求;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条路向:变换、调和、持中;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条路向:反身向后要求。[5]61所以,“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中国人另有他的路向和态度,就是他所走并非第一条向前要求的路向态度。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镊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5]72这种断言即使过于主观,它还是深刻道出了“文化”对于人类生活的“样式”潜在的、长久的内在制约性。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其力作《论传统》中对“传统”的三个特性做了揭示:一是“代代相传的事物”,既包括物质实体,亦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以及惯例和制度;二是“相传事物的同一性”,即传统是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变化链,尽管某种物质实体、信仰、制度等在世代相传中会发生种种变异,但始终在“同一性”的锁链上扣接着;三是“传统的持续性”。[6]15—17由此可见,传统不是历史,因为历史只能是过去;传统亦不是政治,因为政治必定是现实的,故不可能代代相传;传统更不是经济,因为经济是不断变革的力量,不可能相传事物的同一性和具有持续性。毫无疑问,“传统”与历史、政治、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但传统最直接的载体却是文化。文化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可通过物质实体、社会范型来表达,亦可通过思想意识、制度理念来体现。因此,文化,尤其是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方式,才具有渗透到每个人的毛孔,流淌到每个人的血液中的功能。而从“文化传统”的社会功能来看,“她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7]。
三、公民教育定位的思考
文化传统的预制性对于公民教育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晏阳初曾指出,“外国的公民教育未必可直接模仿为中国的公民教育。外国的公民活动亦未必可直接模仿为中国的公民活动。有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出他特有的公民教育。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我国办理教育数十年,成效未著,原因固然复杂,而我国从事教育者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也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一个大原因”[8]。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公民教育与外国公民教育具有绝对的不可通约性,特别是西方公民教育有着较长的历史,必定为我国公民教育的开启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作为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具有紧密联系的公民教育,不能不关注文化预制性的影响。
1.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要考虑文化传统的预制性因素。就当前国际公民教育实际来看,不同国家或地区都会立足于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开展公民教育。由此,不同文化传统中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有关公民权利及如何在权利与义务之间达成平衡的历史,对该国家或地区对公民教育涵义的理解及所采用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影响,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公民教育基本价值的界定,影响着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如,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背景下的公民教育和以英美等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文化背景下的公民教育就存在很大的区别。”[9]
关系本位是中国文化传统重要而显著的特质。它使得中国人不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他们不会追求自由主义式的权利、利益与自由;他们也不是共和主义的,因为他们不会强调共和主义式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善。如果非要贯以“主义”的称号,对他们更为贴切的表达应该是关系主义的。因此,中国的公民教育就应该致力于教授学生批判性建构现代化关系的能力。这一公民教育价值目标包括对传统关系审慎的批判能力和反思意识;对现代关系理性的建构能力和自觉意识;与现代关系相吻合的德性修养和主体意识。通过以“关系”为核心概念的公民教育,学生在对关系本位的文化传统存有温情敬意的同时,不失批判的立场;在走向现代化关系社会的途中,不失对传统关系特质的认同。他们在传统的批判和现代的建构中,能够对关系予以识别与描述、解释与分析、评估与辩护,并形成关系的批判能力、关系的建构能力和关系的参与能力,养成关系的批判意识、反思意识、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它使得经由此路径教育而成的公民既区别于“无他”的私民,又区别于“无我”的臣民;既不是原子式的个体,也不是奴隶式的附庸。他们在“我—他”的关系中历史地和文化地确立自身的地位,承担自身的责任和享有自身的权利;他们立足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并在这一关系中完成社会人和政治人的使命。
从关系本位的文化传统视角出发,社会是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个体成为关系网络中的网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熟人社会的五种关系,称之为“五伦”。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以血缘、家族、亲情为纽带的熟人关系,要扩展至个人与陌生社会大众的关系;传统社会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要进展到处理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资质合格的公民在于能够恰当地履行使命,辨别“网结”的关系结构,并根据各种不同的境遇予以权衡与合理取舍。从这种意义而言,香港教育学院李荣安的观点是有启发性的。他将公民关系视作公民教育的起点和公民身份的前提。“人首先从家庭这种最亲近、最直接的关系出发,才能理解逐步扩展到邻里、社群、国家、国际等较远、较间接的社会关系……必须要从公民置身社会中多重关系的层次性出发,否则就会出现很多公民不愿意接受的问题”,“公民教育就是公民身份的教育,公民身份的教育就是公民关系的教育,公民关系的教育要先从人际关系开始”[10]。
2.公民教育的展开要关注接受主体的文化预制性倾向。公民教育作为教育活动,是在主体之间进行的,包括了教授与学习两个过程。就教授的过程而言,教育者、传导者是主体,被教育对象、接受者是客体;就学习过程而言,被教育对象、接受者是主体,教育内容、教育者是客体。不言而喻,主体的预制性倾向是不能忽略的。由于关系本位的文化传统,无论是从中国历史传统还是从近现代社会现实来看,民众因公共生活经验的普遍缺失,往往难以形成“公共性意识”“公共性知识”“公共性思维习惯”“公共性道德”以及“公共性人格”等现代西方公民社会意义上的品质。韦政通认为,在传统的中国,除了家族外,就没有社会生活。“这是不易培养客观社会意识的,如果有客观的社会意识,则公共事务、社会事务的观念必将产生。有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观念,则公德观念必随之俱来。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人一向没有守纪律的习惯,也缺乏团体精神。”[11]韦政通对中国民众作出了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病根的诊断。但是,由此断言这一病根成为他们缺乏“公共性”的唯一或者主要原因,并不完全是客观的结论。中国民众并不缺乏“公共性”,家族或者宗族就是他们“公共性”的生活和领域。但这种“公共性”迥异于现代西方公民社会的“公共性”,前者建立在以己中心往外而推的关系中,距离越远则“公共性意识”越淡薄,表现为费孝通式的“差序格局”。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关系本位主导下的民众心理思维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由此,中国社会公民教育的展开就必须深刻关注关系本位的文化传统对接受主体的预制性倾向,使对文化传统的客观分析成为教育的逻辑起点。人们生活在密匝的关系网络结构中,以自己为中心,由近及远,从最简单的家庭关系进至社区邻里关系,再推延至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不同的关系属性,具有不同的角色期待和权责要求;同时外推的关系圈的大小和远近,反映了个体德性上的层次与境界。我们的公民教育应该从公民最切近的关系圈开始,首先使人们成为合格的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使之关注私人德性;然后渐渐过渡到关系圈的最远端,使人们成为资质合格的现代社会公民,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使人们将狭隘的家庭的爱扩展为对家乡社区、对国家社会的大爱,从作为家庭的“私我”进至作为社区的“群我”,最终提升至国家社会的“公我”;[12]从而将公民教育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引导人们在遵守起点准则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如果将这种秩序错位了,那么公民教育的效果就要受到挫折。
3.公民教育的设置要以文化传统的本源性为基础。文化人类学者E•泰勒将文化经典性地定义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其他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必须具有的能力和习惯的总和。”[13]钱穆先生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说到,“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不是指每个人的生活,也不是指学术生活,或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它是一切生活的总体。英国人有英国人的生活,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生活,印度人有印度人的生活,……这个生活就是它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表现就成为它的文化”[14]13。无论是泰勒还是钱穆,他们都强调了理解文化的“总体性”原则。这种作为“总体”形式存在的文化在时间的长河中积淀成传统后,就成为一个民族、地区或国家的人们生存的“基因密码”,潜在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对于文化积淀成传统所产生的预制力,钱穆先生的这段话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本源二字是中国人最看中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大生命,生命必有本源。思想是生命中的一种表现,我们亦可说,思想亦如生命,亦必有它的一本源。有本源就有枝叶,有流派。生命有一个开始,就必有它的传统。枝叶流派之于本源,是共同一体的。文化的传统,亦必与它的开始,共同一体,始成为生命。”[14]77
公民教育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其内涵所及与包容的是一个变数。从文化传统的预制性出发,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关系本位的文化传统预制了“公民”在中国语境中不会完全等同于西方世界的“公民”概念,决定了中国公民教育价值取向的特殊性,从而使得公民教育的设置要以文化传统的本源性为基础。从价值层面而言,我们之所以重视文化传统,乃是因为它表达了文化领域中一个历史—现实—未来的连续性;它代表着或象征着不同文化的特征,消解了“传统”,就消解了不同文化的个性。从工具层面而言,脱离了本民族文化传统根源性的公民教育,实效性往往更低,因为它难以获得民众的发自内心的接受与认同,也就难以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成。例如,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的“遭遇”来看,固然有许多具体的原因,但“文化传统”预制性是个重大而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章里说到,“孔夫子的教导和耶稣的教义看来都是建立在规劝的基础上,他们的教义被表达和传播是为了整个人类——异教徒和基督徒的改善。我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的生命是被抛到英国、法国或美国的话,那么我也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基督教是这些国家的宗教,一个人要是这样安排生活,那他就会免遭麻烦且受到尊敬。他不会想到孔夫子,因为孔夫子及其教导他是一点不需要的。在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情况相反”[15]。
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的公民教育都无法摆脱其植根的文化土壤(传统),它具有极大的惯性和文化的拉力。“尽管充满了变化,现代社会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6]2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中;传统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的生活、教育等都具有某种先在性的影响。公民教育的定位必须审慎处之。
参考文献:
[1] 李萍,钟明华.公民教育——传统德育的历史转型[J].教育研究,2002,(10):66—69.
[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12.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4] 李萍.现代道德教育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5]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7] 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99.
[8]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65.
[9] 洪明,许明.国际视野中公民教育的内涵与成因[J].国外社会科学,2002,(4):42—46.
[10] 朱小蔓,李荣安.关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对话[J].中国德育,2006,(5):30—36.
[11] 刘志琴.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51.
[12] 王巨光.公民共和主义:平教总会公民教育的思想特色[J].高等教育研究,2007,(4):84—91.
[13] 周大鸣,乔晓勤.现代人类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6.
[14]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15] 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3.
【李萍,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童建军,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275】
The Prefabrica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Li Ping& Tong Jianjun
(School of Educ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Abstract:Cultural traditions potentially influence peoples existing styles and thinking modes of a certain society, and have profound function of prefabrication. The so-called prefabrica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s refers to the potential, preexisting and innate restriction and influ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al tradition that have been manifested on human existence of reality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Such prefabrication c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sources, peculiarity and exis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t must be considered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should make it as the premise.
Key words: cultural tradition, prefabricati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责任编辑/赵 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