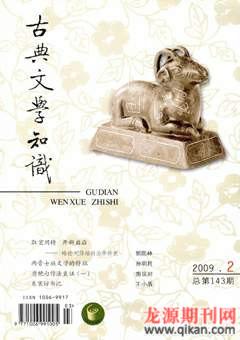《诗言志辨》导读(下)
邬国平
下面逐一介绍《诗言志辨》四篇论文。
三
《诗言志》是全书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是《诗言志辨》一书其它三篇的核心。作者称它为“开山纲领”,固然是因为它产生早,同时也与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性密切相关的。
《诗言志》一文由“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部分构成,“献诗”、“赋诗”二部分以诗乐合一的先秦时代诗歌为主要考察对象,“教诗”、“作诗”二部分以诗乐逐渐分开、诗义更受关注时期,特别是汉代以后的诗歌为主要考察对象,作者由此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诗言志”的涵义及其发展的史迹。
在“献诗陈志”部分,作者先引用杨树达的意见,肯定“诗”即“志”,它们最早是一个意思;又引用闻一多古文“志”字有三个意义,其三是“怀抱” 的说法,从而说明:(一)“诗”字出现比较晚(朱自清认为大约产生于周代),意思与“志”相同;(二)根据“诗”、“志”语源上的一致,“诗”本来就是被人们用来写“志”唱“怀抱”的;(三)《今文尚书?尧典》“诗言志”这句话是对人们有关诗歌的这种认识的记录。
朱自清引用《左传》、《论语》一些话语,认为当时人讲的“志”或“言志”,是与“礼”相联系的,他们所抒发的怀抱,或关个人修身,或关国家治乱,都与“政治、教化”(简称“政教”)分不开。他又引用《诗经》表述诗人何以写诗的句子,说明相关诗歌的“作意”不是“讽”就是“颂”,而且“讽”比“颂”多,从中也可以看清楚“诗言志”究竟是指什么。他又从古代诗乐不分家的角度分析“乐语”,指出与“乐”合一的“诗”是“礼乐”的一部分。所以朱自清认为,“诗言志”其实就是指抒发与政教意识相关的“怀抱”。公卿列士将抒发这种“怀抱”的诗歌献给帝王,或者唱给帝王听,以达到“讽、颂”的目的,这就是献诗陈志,或者谓之“歌谏”。朱自清认为史籍中记载的献诗制度并非是后人托古的空想,而通过对“献诗陈志”的研究,他指出这类归结在于政教的诗歌与“非讽非颂的‘缘情之作”是不同的,说明“诗言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
在“赋诗言志”部分,朱自清从士大夫借用诗歌(即赋诗)的角度考察“诗言志”的含义。他指出,“赋诗言志”与“献诗陈志”有三点不同:(一)“赋诗”者只是“借诗言志”,他们不是诗歌的作者,而“献诗”者往往本人就是该诗的作者;(二)“赋诗”者使用作品往往是“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献诗”者所献之诗却“都有定指,全篇意义明白”;(三)“赋诗言志”颂多于讽,“献诗陈志”则是讽多于颂。尽管如此,“赋诗”者将诗歌当作特定场合中酬酢的工具,言他们心中之所想,具体来说,或者“言一国之志”,或者“流露赋诗人之志”,表白“他自己的为人”,这些都是为了“表德”,让听诗的人通过这些诗句了解他和他所代表的国家,也就是所谓“观志”。从这个方面来看“诗言志”,依然与政治、道德相关,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抒情。
在“教诗明志”部分,朱自清从居于上位者将诗歌施加予下位者角度考察“诗言志”的含义。他指出,“献诗陈志”是指“由下而上”传述讽旨,“赋诗言志”是指“在上位的人”互相称颂“表德”,而“教诗明志”则是指统治者利用诗歌自上而下对人民实施教化,引导风俗。“教诗明志”四字,是朱自清根据《国语·楚语上》“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一语概括出来的,侧重在受教诲人的志。朱自清指出,孔子所谓“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诗大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种种说法一脉相承,都高度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在上者“教诗明志”,就是将诗歌作为道德的载体,让人民接受这些诗义的熏沐,归向于善。受这种认识支配,从民间采集的一些缘情诗,其原先缘情的性质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成了人们观政令之善恶的材料,“那么‘缘情作诗竟与‘陈志献诗殊途同归了。”朱自清通过对“教诗明志”的考察,从在上者推行诗教的意图来证明他们所理解的“诗言志”主要是关系人心、世风的善恶问题。
在“作诗言志”部分,朱自清考察了写诗者个人与“言志”的关系。以上“赋诗”、“教诗”都是说明用诗者的诗歌观念,“献诗言志”虽然是从诗歌作者角度说的,可是诗歌直接陈述的是关乎国家的事情,不是作者一己的事情,献诗以讽谏为目的,重点在听者,不在诗人自己。“作诗言志”则不同,诗人表达个人的想法,为自己而写诗。朱自清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开始歌咏自己的”是屈原为首的辞赋作者,到东汉五言诗逐渐发达以后,抱这种写作态度的诗人更多。然而,这些“歌咏自己”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者讲述个人的穷通出处,或者吟咏他们所理解的人生义理,比如出世观和入世观,以这些为“诗言志”的引申义,其实也都没有离开政教。由于诗人开始注重为自己写诗,诗歌中个人的、抒情的因素渐多,“缘情”说便被提了出来,即使如此,重视政教的“诗言志”传统仍然“屹立”不倒,依旧给诗歌创作以深刻影响,只不过这以后“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乃至出现后人用“缘情”诠释“言志”的状况。朱自清通过对诗人“作诗言志”的考察,勾勒出诗歌史上“诗言志”由讽、颂本义逐渐被人们引申、扩大的演化轨迹,以此说明它的核心内涵依然在文学批评史上得到了贯穿。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可以将朱自清得出的主要结论概括如下:“诗言志”谓表现怀抱,其本义是讽颂,反映的是一种政教意识;诗人言个人的穷通出处或人生义理,是其引申义,依然与政教相关;利用诗歌移风易俗,是将这种政教意识普及到民间。这种以政教为核心的“诗言志”也可以称为“以诗明道”,与“因文明道”没有不同,所以“诗言志”与“文载道”是一致的,不构成思想的对立。诗人纯粹为表现个人感情、无关政治教化而创作诗歌,这形成了“诗缘情”的观念。“诗言志”与“诗缘情”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与政教相纠缠。与“诗缘情”相比,“诗言志”显然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更加深刻、悠久的传统,这也表明中国文学的政教化特征。
四
《比兴》篇实际论述的内容包括赋比兴,所以论文最早在《清华学报》发表时题目为《赋比兴说》,结集时作者将它改为《比兴》,而赋比兴三者中,兴义又最微妙,《诗经》毛传只对“兴”作提示性的标注,对赋、比不作提示,就是因为“兴”义隐微,赋、比之义显明,后人讨论赋比兴,实际上讨论的焦点也是集中在兴上面,他们往往“比兴”连称,而连称的“比兴”其意思大致接近“兴”。朱自清这篇论文也沿袭了历来的研究习惯,在赋比兴三者中主要讨论比兴,在比兴中又主要讨论兴。论文四个部分的标题分别是:“毛诗郑笺释兴”、“兴义溯源”、“赋比兴通释”、“比兴论诗”。朱自清研究赋比兴,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点意见:
(一)他认为,《周礼?春官?大师》称风、赋、比、兴、雅、颂为“六诗”,而《毛诗序》改称它们为“六义”,这反映了我国诗歌由重声时代转入重义时代的变化。他在参考逯钦立《六义参释》一文基础上,也肯定风、赋、比、兴、雅、颂在很早的时代,“似乎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风、雅、颂表示音乐,这自然不必多言。他推测赋比兴在早期的含义也与音乐有关,“大概‘赋原来就是合唱”,“‘比原来大概也是乐歌名,是变旧调唱新辞”,“‘兴似乎也本是乐歌名,疑是合乐开始的新歌。”只是后来诗歌的义越来越受人们重视,赋比兴才逐渐被解释成为只是与理解诗和写诗有关的概念,他说:“《诗大序》改为‘六义,便是以义为用了。”对于早期的赋比兴含义,由于资料极少,研究非常困难,但是,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朱自清认为赋比兴是“乐歌名称”,这虽然仅仅还是属于一种猜测,缺乏论证,证据也显薄弱,无疑对于人们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会有所启发。
(二)他通过将《毛诗》和《左传》作比较,提出《毛诗》“比兴”说诗的方法,受到了《左传》赋诗引诗、断章取义做法的影响。《左传》记载赋诗引诗的例子很多,其中有些就是后来被称为“比兴”的诗,赋诗引诗人多是使用诗句的喻义,取其能够表明自己真正想传递的意思,这与“比兴”的性质相似。据朱自清统计,《左传》“赋诗显用喻义的九篇,有七篇兴诗。引诗显用喻义的十篇,有五篇兴诗。”他举“《左传》明言喻义而与《毛诗》相合”的五篇作品(《湛露》、《鸿雁》、《黍苗》、《葛藟》、《桑柔》)为例,认为《毛传》作者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与《左传》赋诗引诗人对它们的引用义互相一致,所以,应当承认这是《毛诗》本于《左传》的事实。朱自清由此得出结论,“《毛诗》比兴受到了《左传》的影响”。同时,他又指出,尽管《毛诗》作者解说诗旨受了《左传》赋诗引诗人的影响,二者的差异也很显然。他说:赋诗引诗人“是引诗为证,不是说诗;主要的是他的论旨,而不是诗的意义。”而听赋诗引诗的卿大夫对于《诗三百》“大约都熟悉,各篇诗的本义,在他们原是明白易晓,……他们听赋诗,听引诗,只注重赋诗人的用意所在;他们对于原诗的了解是不会跟了赋诗引诗人而歪曲的。”然而《毛诗》解释诗歌却不如此,“到了他们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取义为全章全篇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令人觉得无中生有”。在这方面,郑玄与毛传作者的态度虽然略有区别,本质却无不同,“《郑笺》力求系统化,力求泯去断章的痕迹,但根本态度与《毛传》同,所以也还不免无中生有的毛病。”在《毛诗》研究中,“比兴”说诗这一方法的来源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尽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有多种答案,朱自清认为《毛传》是受了《左传》的影响,“比兴”与春秋时代赋诗引诗的风气有关,这种解释也是有一定道理,而了解二者之间存在这层关系,对于人们认识“比兴”说诗的特点自然也是会有帮助。
(三)他给什么是“兴”,“比”与“兴”的区别是什么,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提出了一个容易掌握的区分标准。他说:《毛传》使用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如果只是单纯的譬喻,不是出现在诗歌发端的位置,就不能算“兴”,而是“比”。前人关于“兴”与“比”的区别已经说了很多,能道明其中究竟的极少。有的人不承认“兴”是譬喻,认为这样就与“比”没有区别了,然而《毛传》对于“兴”句的释义,往往使用“若”、“如”、“喻”、“犹”等字,分明是将“兴”作为譬喻对待,可见,否认“兴”有“比”的含义,并不符合《毛诗》的实际。可是,“兴”与“比”具体的所指又确实不同,否则没有必要将它们分开。“比”、“兴”含义纠缠,人们长期以来难以对它们的区别做出明确的界说,原因在此。朱自清以“譬喻”解释“兴”,又以这一类诗句是否处在诗歌发端的位置作为与“比”相区别的标志,这都是得要领的。
(四)他指出“比兴”作为一种譬喻,具有二个特点,它“不止于是修辞,而且是‘谲谏”。也就是说,“比兴”将诗歌的艺术手法和政治道德观念合而为一,二者如形影相随,这决定了它与单纯的修辞手段“譬喻”不同,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意念,“比兴的缠夹在此,重要也在此。”这一说明同样简单明了,准确妥当。这对于理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源远流长的“比兴说”十分关键。古人强调取譬引类,主文谲谏,温柔敦厚,不直斥其言,这是“比兴说”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表现。而在开展文学批评,解说诗歌旨趣,分析作品意义时,“比兴说”又成为支持人们触类旁通,即兴引伸,自由演绎作品政治和道德主题当然的理由。朱自清在文章中主要对用“比兴”的方法开展文学批评谈了看法。他并不一概反对这样做,然而又提醒人们,这样得出的认识“是读者的受用而不是诗篇的了解”,如果将读者的感兴当成了作品的本意,那就越出了界限,以至造成文学释义批评中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弊端,对此,他给予严厉批评。为了克服“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朱自清先生对待诗歌多义的情况,主张应当采取如下态度,“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才算数。”
五
《诗教》一文论述中国诗教传统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它发生的广泛影响。文章分三部分:六艺之教、著述引诗、温柔敦厚。在历史上,诗教与礼教、乐教互为一体,互相配合,共同体现出儒家教化文化的价值内涵,历来受到高度重视,朱自清这篇文章较早对诗教进行了一次现代的检讨。
《诗》教与《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并列,共称为“六艺政教”(郑玄语),董仲舒称为“六学”(《春秋繁露?玉杯》),深受汉人重视,体现了他们宗经的观念。朱自清指出,诗教在六艺之教中地位与其它五家相当,甚至在阴阳五行说极盛的时期,《易》、《书》成为显学,《诗》的地位相对还有点低落,这说明在“六艺”中,诗教在当时并没有特别受到重视。可是,因为“诗语简约,可以触类引伸,断章取义,便于引证”,《诗经》这种“富于弹性”的特点,又帮助了它流传,所以从社会流传、应用的广泛程度而言,儒家其它经典“到底不如《诗》”,这也使诗教的影响得以扩大。
朱自清从汉人在著书立说时喜欢频繁而广泛地引证《诗经》,考察诗教在汉代的成立;又从他们引证《诗经》的内容,考察诗教所关涉的主要方面和核心。本来,引诗以助言语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这在《左传》多有记载,但是那与汉人以宗经的态度引证《诗经》还是有不同。朱自清将汉人引《诗》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类是关于人事的,包括德教、政治、学养,其中以涉及德教的引用数量为最多。第二类是关于天道的,第三类是关于历史、制度、风俗的。汉人如此地喜爱援引《诗经》,或者据以立论,或者据以判断,这既说明他们对《诗经》非常熟悉,也说明诗教深入人心。朱自清认为,在以上三个方面中,诗教这一意念的“核心”是“德教、政治、学养”,“温柔敦厚”四字就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集中了诗教的精粹。
本文最主要的内容是第三部分对“温柔敦厚”诗教本身的分析。朱自清首先说明诗教与乐教的关系。他认为,诗教与乐教各司其责,反映随着诗乐为一到诗乐分开,《诗经》逐渐从“以声为用”过渡到“以义为用”的变化,“《诗》教究竟以意义为主”,发挥其“美刺讽谕”的作用,这是它与乐教最显著的区别,然而,“‘《诗》为乐章,《诗》乐合一是个古老的传统,就是在《诗》乐分家以后,也还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诗教毕竟还伴有乐教的身影。由此,朱自清得出结论,“‘温柔敦厚该是一个多义语;一面指‘《诗》辞美刺讽谕的作用,一面还映带着那‘《诗》乐是一的背景。”其次,他从以义为主,诗、乐、礼互为其用的角度,阐明“温柔敦厚”诗教的基本精神,是“和、亲、节、敬、适、中”,是儒家重中和之道思想的表现,《经解》所谓“《诗》之失愚”,“愚”的意思“就是过中”,偏离了“温柔敦厚”。第三,以“温柔敦厚”为标准开展文学批评,这种风气在汉朝最盛,汉以后诗教的传统则“大减声势”,不过诗歌仍然以“优游不迫”为尚,所以“还不失为温柔敦厚”。到了宋朝,以说理为诗,风格朝散文化发展,离开“优游不迫”、“温柔敦厚”越来越远。虽然这遭到一些人批评,想“重振那温柔敦厚的《诗》教”,但是,单单重复汉人的调子“已经不足以启发人”,于是对诗教的解释发生了改变,那就是更强调以孔子“思无邪”一语为教,比如吕祖谦和朱熹就是那样主张的,虽然“思无邪”与“温柔敦厚”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毕竟包含了更多道学的眼光,同时,也反映了诗歌创作“尽向‘沈着痛快一路发展”的现状。朱自清将唐以前和宋以后诗歌风格的变化置于“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变迁中加以考察,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比较新颖的,可惜后人再没有沿着这样的思路去继续探究唐宋诗所以异样的原因。
六
《正变》是作者《诗言志辨》四篇论文中最晚完成的一篇。内容方面,根据朱自清自己在《诗言志辨·序》的说法,《正变》的归结虽然也是在于“政教”,不过它直接的意义是有关于理解诗歌的一种“方法”,它是“纲领”之下的一个“细目”,与另外三篇有明显不同,这同时也说明,他随着对古代文学批评意念研究的逐步展开,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也在不断扩大。
朱自清在《正变》篇研究了古代文学批评的变化和发展的观念,主要涉及其中“变风变雅”和“新变”二个概念。他认为,“变风变雅”的“变”,是指“政教衰”、“纪纲绝”,着眼于“时世由盛变衰”,是强调时政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诗歌出现变化;而“新变”之“变”则是人们因为求新生异而使诗歌体裁、诗歌风格发生改变,主要不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是诗歌发展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一种现象,因此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变化观念。这基本概括了古人关于诗歌变化和发展学说的主要内容。
“变风变雅”由《诗大序》作者提出,经过郑玄《诗谱序》、孔颖达疏层层阐述发挥,借助经学的声势而成为一种权威的诗论,对诗歌创作和批评产生广泛影响。他们解释说,《诗经》一部分作品产生于治世,故是颂美之声,为“正风正雅”;一部分作品产生于乱世,故是怨刺之言,为“变风变雅”。根据这种观点,诗歌的正体和变体是社会政治、礼教、风俗盛衰的必然反映。虽然正、变二类诗歌本身无所谓优劣之区分,然而持这种“正变”论者,很显然是由衷地向往产生“正风正雅”的时代,贬斥“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诗大序》)的社会。所以,“变风变雅”论者对社会的关注远在诗歌之上。朱自清分析道,这种“正变”论是受了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影响。他还指出,“变风变雅”说带有宣扬天人感应、天象正变的阴阳五行学说的色彩,在郑玄《诗谱》中这种特点尤其显著。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也比仅仅以风衰俗怨解释“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见解深刻。朱自清又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种“变风变雅”论,是郑玄的一种“创见”,与《诗大序》说的“变风变雅”含义不同,《诗大序》所说的“变”并无政治上的“微言大义”,这是二者的显著差别。其实,郑玄诗说是对毛传和《诗大序》的具体化,他们对“变风变雅”的认识是互相贯通、前后一致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过于强调郑玄《诗谱序》与《诗大序》思想的区别,并不符合实际。
《正变》篇的“诗体正变”部分,是论述古人关于诗歌一般的变化和发展观念。朱自清说,文学批评中这种一般的变化观念,源自《易经》“变”的哲学。事物在变化中存在,文学也是如此,《易经》尚“变”的学说对文学新变构成支持。另外,《易经》论“变”,有终而复始的循环论特征,古人的文学通变学说也近于这样的循环论,这也表明它受到了《易经》的影响。朱自清指出,这种与“变风变雅”不同的文学一般的变化和发展观念,在六朝和隋唐之际的文学批评中开始被普遍采纳,以后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变风变雅”说。尽管如此,六朝以后持这种一般的变化观的批评家,他们论“变”也都是“隐含‘正义”,所以,这还是“从风雅正变说推衍而出”。由此可见,“变风变雅”和“诗体正变”之“变”含义,仍有一致之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