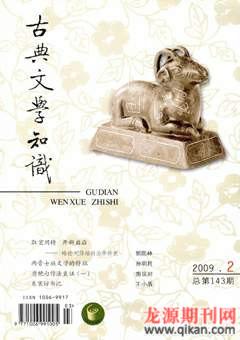取宏用精 开新启后
郭院林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盫,江苏仪征人。他以短暂的36年生命从学从政,留下了七十四部著作,这些著述不仅涉及经学、小学、校雠学等传统国学领域,而且还包括体现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政治、经济与教育,采取近代西方的学术方法与体系研究中国学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认为当时50年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黎明时代,而“此黎明运动中之刘君(师培)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可见其对刘氏的推崇。刘师培力图重建国学,为学界引进了西方的理论,并使其与中国国粹融为一体,对即将面对世界潮流的中国民众,开新启后,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刘师培的通达的治学特色、治学领域的开拓以及学术地位进行论述,以窥其博大精深。
一、 会通学术分歧的努力
作为“扬州学派”的殿军,刘师培以“绍述先业,昌扬扬州学派自任。”(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兼有吴、皖两派之长,既能确守汉诂,条源析流,又能辞外见义,学求致用。刘师培的知识结构不局限于儒家的经典,对经、史、子、集、道藏、内典以及西学均有涉猎。刘师培论学贵“通”,他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他试图纠合传统学术的分歧,进而达到发扬国粹,建设民族特色文化,恢复国民信心的目的。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经学史、文学史、文字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有导夫先路之功。他不仅要打通经史,平分今古文经学,而且还要调和汉宋,沟通中西。
1. 等视经子
与今文经学家一味强调经史之别不同,刘师培在经史观念上比较通达。他继承龚自珍的学说,从学术起源的角度论证六经皆史,认为 “六经皆周公旧典”,“成周一代之史,悉范围于六经之中。”西周时“史官记言记动,仍仿古代圣王之制,故《易经》掌于太卜,《书经》、《春秋》掌于太史、外史,《诗经》掌于太师,《礼经》掌于宗伯,《乐经》掌于大司乐”。“《春秋》者,本国近世史之课本也。”“若孔子六经之学,则大抵得之史官。”“六经本先王之旧典,特孔子另有编订之本耳。周末诸子,虽治六经,然咸无定本,致后世之儒只见孔子编订之六经,而周世六经之旧本,咸失其传。班固作《艺文志》以六经为六艺,列于诸子之前,诚以六经为古籍,非儒家所得私。”因此他再三申明“六经之书,确为三代之古籍典章”(《刘申叔遗书·经学教科书·古学出于史官论》)。
基于六经皆史的观念,所以他以六经为史料,研究历史,以之“考古代之史实,以证中国典制之起源,观人类进化之次第”。成书于1905-1906年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其史学代表作,该书体制上仿照西方历史作品的章节体,纵向上按照历史进化次序划分阶段,横向上按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军事经济等分类叙述,加以分析,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界可以稍明”,进而扩大了“六经皆史”的涵义,认为“上古时代之学术,奚能越六经之范围哉?”
刘氏撰史期于“繁简适当”,内容力求简明,在体例上仍不脱“以经证史”的模式,参考资料仍以经学古籍为主。而且,从其思想来看,也是从经学中汲取民族革命的要素进行鼓吹反满革命,终极目的在于发扬国粹以保种保国。刘师培倡导“六经皆西周之史书”,发挥经书中华夷之辨,目的最终在于进行民族革命。
2. 平分今古
刘师培首先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经学的产生,而且不承认有所谓今古文经学的说法。他认为今古文师传相同,都是诠释《春秋》的,“《春秋》作于孔子,三传先师持说实同。”“《春秋》三传,同主诠经。”(《刘申叔遗书·春秋左氏传例略》)古文经源于孔子六经之学,三传相通。“孔子之以六经教授也,大抵仅录经文以为课本”,“弟子各记所闻,故所记互有详略,或详故事,或举微言……然溯源流,咸为仲尼所口述,此《春秋》所由分为三,《诗经》所由分为四也”。(《刘申叔遗书·汉代古文学辩诬》)他取消今古文的区别,认为“近代学者知汉代经学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吾谓西汉学派只有两端:一曰齐学,一曰鲁学”“然鲁学之中亦多前圣微言大义,而发明古训亦胜于齐学,岂可废哉?”(《刘申叔遗书·国学发微》)这就是说,所谓的“微言大义”并非今文学家的专利,而是今古文所共有的。
通过学术史考察,刘师培指出:“《春秋》三传其分歧始于汉初,汉代以前同为说《春秋》之书。治《春秋》者或并治其书,以同条共贯。”今古文的区别仅在文字不同,“今文者,书之用汉代通行文字者也;古文者,书之用古代文字者也。”(《刘申叔遗书·汉代古文学辩诬》)这就证明今古文经没有根本区别,有的区别仅仅是外在形态而已。即使到了东汉之时,“经生虽守家法,然杂治今古文者亦占多数。”“无识陋儒,斥为背弃家法,岂知说经贵富乃古人立言之大公哉?”(《刘申叔遗书·国学发微》)同时又指出:“且当此之时,经师之同治一学者,立说亦多不同。”这就是刘氏站在通儒的立场,抨击固守家法的做法。
3. 持平汉宋
汉学与宋学是儒学中的两大派别,汉学侧重儒家经典的训诂考据,而宋学则注重儒家经典的“义理”,两者各有师承,各有渊源。刘师培认为:“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卿皆传六艺之学者也,是为汉学之祖也。”(《刘申叔遗书·国学发微》)孔子均具师儒之长,所以汉学、宋学都渊源于孔子。这样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历来汉学与宋学的“道统”之争,汉学、宋学都是得孔学之一端发展而成,都是孔学“道统”的继承人了,几百年来汉宋之争原来本一家。他认为门户之见都是可笑的,“但以合公理为主,不分汉宋之界”。
汉学与宋学的差异在于“汉人循律而治经,宋人舍律而论学,此则汉宋学术得失之大纲也”。汉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夫汉儒经说,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或出入老释之书,故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是在学者之深思自得耳。”(《刘申叔遗书·汉宋学术异同论》)
刘在《国学发微》中提出了对汉宋学术进行“以类区分,稽析异同,讨论得失”的主张。他首先揭示了汉宋门户之见遮蔽了对汉宋学术作客观的认识,“东原诸儒于汉学之符于宋学者,绝不引援,惟据其异于宋学者,以标汉儒之帜。于宋学之本于汉学者,亦屏弃不言,惟据其异于汉儒者,以攻宋儒之瑕,是则近儒门户之见也。然宋儒之讥汉儒者,至谓汉儒不崇义理,则又宋儒之忘本之失也”。
4. 会通中西
刘师培素有深厚的旧学根柢,但是他并不排斥西学。他试图会通中西,或者藉西证中,从而达到树立民族文化的信心。从1902年《江南乡试墨卷》第三题《中外刑律互有异同,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应如何参酌损益,妥定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权策》来看,刘师培对于当时世界形势颇为了解,所以才能得到考官评语“论治能识欧亚”。刘师培有关史学的著作深受当时西学新潮的影响,尤其显著为对“进化史观”的认定。刘师培曾作《读天演论》二首,通过描写景物的季节更替,“感此微物姿,亦具争存志”,表达对《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思想的理解。刘师培对西学也十分看重,并深以自己不通外文未能及时获得新知为撼。他有诗曰:“西藉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甲辰年自述诗》)
刘师培运用进化理论和西方社会学、考古学、文字学知识,对上古社会作了探析。《古学出于史官论》发挥其考据学之长,以简明而又坚实的证据论证了己之所见,语虽扼要但殊少纰漏。《周末学术史序》分学术为16类,《经学教科书》已经运用了经学研究的新方法。用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界定中国古典学问并以此分类为体裁撰著学术史。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界定中国古典学问,则完全是刘的独创。(李帆《论刘师培学术史研究的地位与特色》)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部公认为以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新型历史教科书。为了使“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他认为书写中国历史应该注意,“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这些都反映了进化论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此书除征引中国典籍外,并参考若干西籍,目的尤在使“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
在接受西学的出发点上,刘师培是借西学佐证中学,甚至与“西学中源”有类似。刘师培的新学结构以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为骨干,谈不上成体系地了解和接受西学,尚未做到圆融贯通的中西学交融,刘师培吸纳西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在中学。刘师培在历史、思想、学术诸方面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照,然后试图会通。但是他自小受国学熏陶,国学始终是他立命之本,他甚至没有象王国维等人理性上趋于西学,而情感上却依然顾念中学的心理分裂,他不过是借西学来为中学开辟道路,所以他对中国前途充满乐观。要而言之,刘的“中西观”,虽然主观上要求“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只能做到“会”的层次,对中西学术进行简单的附会,而不能真正做到“通”的高度,对中西学术的认识未脱晚清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窠臼。由于时代原因,刘还有保存国粹,与西学一争高低的企图,不免存有意气之争,这也影响到了刘对“中西会通”作进一步的探索。
二、 研究领域的开拓
1. 道藏研究
刘师培从小就博览群籍,“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清末宣统庚戌年(1910年)孟冬,刘师培旅居白云观,披阅《道藏》,对37种道经加以勾玄提要,随笔记录,计37篇,录成一帙,名曰《读道藏记》(未完)(《国粹学报》第7卷,第1~5期,第七十五至七十七、七十九期。1911年),是为近现代最早的《道藏》提要。该《记》又被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以及丁福保编《道藏精华录》、胡道静等主编《道藏要籍选刊》等书中。在后来的《读道臧记》的序中,他叙述了这段经历:“迄于咸、同之际,南《藏》毁于兵,北《藏》虽存,览者逾勘,士弗悦学,斯其征矣。予以庚戌(1910)孟冬旅居北京白云观,乃启阅全《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法国汉学家施舟人评论道:“(中国本土)第一位比较科学的研究道教的人是刘师培(1884-1919),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刘毓松(1818-1867)的后代。1910年,他在北京白云观读《道藏》。”(施舟人《中国文化基因库》)
2. 敦煌学研究
刘师培有幸亲见早出的敦煌材料,并且迅速的着手进行研究,开敦煌学之滥觞。1909年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侍读学士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敦煌学》)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篇。刘师培以当时他能看到的伯希和供应的少数材料为依据,撰写《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篇,1910年11月21日开始连载于《国粹学报》第七十五至八十二期。这是对传统的“四部书”残卷进行的最早的深入研究,以考订写卷年代、进行文字校勘、评定写卷价值等为主。极为精审扼要,可称典范之作。开创敦煌研究之先声。(白化文《中国敦煌学目录和目录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刘师培已于1911年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辛亥第四号)中,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太平寰宇记》,考出了《贞元十道录》的名称和作者,对地志类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并指出了该卷与传世史志的异同。
3. 神话研究
1905年10月20日刘师培《国粹学报》上发表的《读书随笔》子目有《易言不灭不生之理》、《山海经不可疑》。在《〈山海经〉不可疑》一文,据“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的新知识,再引汉武梁祠所画证明“《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他接受“地球之初,为草木禽兽之世界”的观念,视“西国古书多禁人兽相交,而中国古书亦多言人禽之界”的现象为“古之时人类去物未远”明证;则“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既如此,此书所言自不可疑。(《刘申叔遗书》第1950页)就史学方法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提出:后人对所不及见之事物,“谓之不知可也,谓之妄诞不可也”。这正是后来的趋新疑古派与旧派正统学者相近之处,两者皆视其未见之古事物为不存在,所异者一以为“伪造”,而一以为“妄诞”也。另外刘氏对《穆天子传》、《楚辞》、《列子》等包含丰富的神话文献进行了研究。
4. 金石研究
刘师培的父亲很重视石刻文献的收集,自己也能灵活的运用金石材料进行研究。1909年为端方考订金石,称为“匋斋师”,撰有《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晏子春秋补释》、《蜀中金石见闻录》一页等专文,另外零散的见于各种文章。如:“其旁订金石文字也,于虢盘正月丁亥以三统术推之,定为三日。”(刘师培《先府君行略》)重视金石材料对于考古的价值(《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研究范围包括钟鼎、宋砖、汉碑、残砚、画像等等,凡有益考古之金石,刘氏皆能为己所用。利用金石证明的问题也很广泛,不局限于清儒的文字考据,而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如《中国古用石器考》一文证明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由石器-铜器-铁器的发展,可谓新天下耳目。《唐张氏墓志铭释》考地理,《周代吉金年月考》考历法,涉及内容广泛全面。惜乎天不予年岁,系统难成。
三、 “二重证据”之滥觞
在近代,学术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完善,一些大家纷纷提倡新方法,发掘新材料。刘师培也提出了独创一格的见解,成为日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滥觞。刘氏对“考古”的概念理解比较开阔,在《古政原始论总论》中,他主张运用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的方法,再借以西方社会学所得出的定例检视之,即可以考究“古代人群之情况”。他认为,考迹皇古,“厥有三端”:一曰“书籍”,五帝以前无文字记载,但“世本诸编去古未远”,此外《列子》、《左传》、《国语》、《淮南子》等书,其“片言单语,皆足证古物之事迹”;二曰“文字”,中国文字始于久远,“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深浅(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但刀币鼎钟,于考古都“珍如拱璧”。(《古政原始论·总论》)刘氏意识到外来的新知与固有的材料两者参证对古代史的研究的进展很有意义。他所谓的书籍、文字、器物这三种材料,如依其来源和性质区分,则可归纳为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二种。他虽未明确提出这两种材料互相释证的具体方法,但却已注意到其间颇具互补性,因此主张引进西方田野考古学,发掘地下遗物。这两点见解均体现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从中可以看到日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滥觞。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故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之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杨向奎先生对此补充修正,他说:“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史讲双重证据,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鉴于中国各民族间社会发展之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据代替了过去得双重证。”在这一方法体系的发展上,刘氏不能说不具有先锋开导之功。
四、 国故整理之先行
刘师培率先清醒的意识到保存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终其一生为国学发扬不懈努力,为后来胡适的国故整理导夫先路。
1904年刘氏即发表《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等文,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澄清学术真相,表明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他认为“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1905年刘师培又积极参与国学的保存与重建工作,刘氏担任国学讲习会正讲师,该会以国学为“立国之本”,保存国粹。刘氏编有五种讲义:《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1905年创建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就是以刘师培、邓实、黄节个人藏书为基础,初约6万卷,后扩充至20多万卷。在《国粹学报》的82期中,其中80期刊有刘师培的文章(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三两期没有),刘师培著述在该刊中连载过的就有33种,在该刊部分发表五十余种。(郑师渠《晚清国粹派》)1913年7月,刘师培在山西创办《国故钩沉》杂志,发表了几篇文章。该刊仅出一期即停刊。1919年1月26日,《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屠孝寔、林损、陈钟凡出任特别编辑,其中马叙伦、吴梅、黄节三人为南社社员,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十名同学出任编辑。
整理国故这一发明权应归于刘师培,而胡适的所作所为,只是对刘师培的回应。(朱维铮:《失落了的“文艺复兴”》)刘师培在这方面的努力确实率天下先,而且与后来的整理国故相比更具特色与深刻性,它是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国粹派之所以为国粹派,不仅在于他们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而且更主要还在于,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他们提出了“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大声疾呼:爱国之士不仅当勇于反抗外来侵略,而且当知“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的道理。(《国学保存会小集序》)刘氏决不是一个纯粹埋头于故纸堆里腐儒,而是具有满腔爱国之情的学者。
(作者单位:新疆石河小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