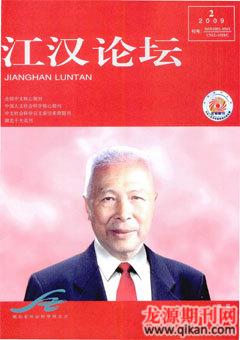论王维山水诗空灵清远的意境
陈金刚 李 倩
摘要:王维山水诗的最大贡献,在内容上是诗与禅的融合,在创作方法上是诗与画的融合。由于这两种融合,他成功地创造出空灵清远的艺术意境,在中国诗歌史中,他是独树一帜的。如果说佛教传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化的禅宗,那么王维的山水诗,便是禅意的诗化。
关键词:王维;禅宗;山水诗;意境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2-0095-05
谈王维山水诗“空灵清远”的文章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外在样态上的描述,缺少对其“空灵清远”独特性所在的阐析。笔者认为,王维山水诗意境的审美特征是空灵清远,而本质问题则是画境与禅境的圆融一体。这是他与其他诗人的不同之处。大体说来,谢灵运山水诗的风格虽然也具有空灵清远的外在表现形态,但他主要是以“玄”学眼光来观照山水,是诗学与玄学的合一;陶渊明的作品自然清淳,风格与王维亦有类似之处,但诗中却缺乏浓郁的禅意。王维的山水诗涵永清悠,诗境虚清空灵,风格清丽淡远,在“以画为诗”的画境中,蕴含有浓郁的禅意,通体折射出浓厚的佛性之光。
一、王维山水诗:画境与禅境的圆融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自己也曾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所以他的诗歌创作,能够融入绘画方面的种种技巧与观念,使得他的山水诗呈现出“诗中有画”的突出特点。但“诗中有画”只是王维山水诗外在样态上的审美特征,画境和诗情中所含蕴的质核是浓厚的佛学意味和佛性之光。正是这种画境与禅境的圆融,才构成王维山水诗具有中国诗史上“这一个”的特性。
根据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略作统计,在王维各类诗体中出现“空”字大约有90次,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语符,在诗中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如“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以上诸例是王维诗中常见的主要用法。这些由“空”字修饰的意象群,在营造诗歌清幽冷寂的意境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一“空”字意象群是属于王维所特有的。王维在诗中用空字,并不是语汇的贫乏,而是有意在写景时以“空”字点化,把人们的思维引向静寂悠远、澄空净滤的禅境中。其所造成的意象与佛理禅思有着直接的关系。诗人善于把远近的景物重叠,营造一种奇特的空间感。如“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晓行巴峡》),“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在这里,空间不是用几何的形式堆叠而成,而是以音乐的方式呈现、故一笔一划,一字一句,无不谱写着诗人画家的心灵律动。而他的“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田园乐》之六)则是通过时间上的一点,来显现景物(或事物)的空间结构和情态。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王维有意打破自然程序在异质的事物后面找到与情感同质的意象,组合成心灵的艺术空间。他的《雪中芭蕉》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创作,被后来“文人画”写意山水视为典范。他的名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所展开的画面只有寥寥数笔,却勾勒出一个广阔、迷漾、变幻虚无的空间,创造出空灵缥缈的意境,从中渗透出一种雄浑、壮阔、豪迈的感觉。由于王维善于以活生生的材料和活灵灵的感悟将禅宗理念与审美意趣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充满情韵的心理时空。他山水诗歌中的惮宗理念的表达,大都清淡隽永,回味深长。所以清人沈德潜曾说王维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指的是王维诗歌所构造的意象、境界隐寓着禅理,而他诗中的禅理就在那奇妙的心理时空中。
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比较,王维没有谢灵运那种因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和典丽工致的语言所造成的繁复深涩感,相反,他的语言是清秀流畅的。前人曾评其诗“诸词清婉流丽”,“辞情闲雅,音调雅驯”。被人们称赞不已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形象地勾画出了辋川积雨的景物特征,展示了清空幽美的境界,抒发了诗人清淡闲雅的情怀。诗中既有嫩绿秧苗与白鹭的色彩对比,又有浓绿树荫与黄鹂的色彩对比,而就整个画面来看,白鹭飞起的动态,与黄鹂鸣啭的声音,又形成了另外一种对比。其审美内涵十分丰富,是声色交融的典型诗作。从中我们更深刻地体味到杜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佳处所在。从而也才真正理解了王维诗中的色彩美及其清雅格调。此诗曾被清人赵殿成誉为唐诗的“压卷”之作。
王维的山水诗以清丽淡远取胜,因此,在他的山水诗中,大至山色江流,小至苔绿蝉音,远至天外,近至衣边,都作了精心的刻划。他喜用“远眺”、“坐看”将一切自然景色尽收眼底,而且使读者同样能感受到他所刻划的清新秀美、栩栩如生的景色。如《山中》、《辋川别业》、《春园即事》、《田园乐》的色彩都是很斑斓的,令人目不暇接。王维喜用青、白二色,给人以寂静、清凉的暗示。据统计,王维诗中出现的“白”色91次,“青”色62次,而且经常将“青”、“白”二色对举使用。从诗歌美学的角度看,“青”、“白”二色更能体现王维对萧疏清雅、闲静淡远的审美情趣的追求。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白石滩》),“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意境苍茫。中国古代山水画不注重明暗,而王维诗中则十分强调“明”、“暗”,从而使诗歌所引发的想象画面获得了如同油画和摄影的用光效果。如《辋川集》中的《木兰柴》一诗:“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这首诗先描写夕阳返照的余晖,在这柔和的光照下,飞鸟彩翠明灭,夕岚隐曜,深巷半显半隐,如同一幅幅水银灯下的特写。在寥寥20个字里,把光线描写得如此生动,真可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诗人以画家的创作方法,将绘画艺术引入诗中,使其诗具有不隔之美。诗人还善于经营布置构图,达到整体把握,重点突出,使之成为想象中画面的结合点。
在王维的诗中,除了如画的视觉形象,还充满了生动的听觉形象。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着风声、竹声、松声、泉声、虫鸣声和鸟声,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谷静秋泉响,岩深青霭残”(《东溪玩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为一体。《史鉴类编》称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宫商迭奏……真所谓有声画也”。
王维的山水诗格高调清,秀丽淡雅,充满了“空”、“寂”、“闲”、“静”的禅趣,他诗中的景物捕写,能够像绘画一样,注意山水景物的静态表现。一般来说,诗宜叙述动作,画宜描写静物。但王维山水诗却打破了这种诗与画的界限,
他着力描写和表现大自然中山水景物的静态之美,使其山水诗中的景物成为一幅幅清幽寂静的优美画面。即使其中也有动态、音响的描写,但根本的目的,还是为创造静的意境服务的。如“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送别》),这些诗中的景物似乎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是静止的,凝固的,呈现出一种静态的美。不过在他诗中更多的情况是通过动来写静的,用局部的动态描写来衬托山水景物的整体的静谧。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这里桂花飘落,本是极微小的“动”,月亮升起也是极缓慢的“动”。而这个极微小、极缓慢的“动”,却映衬出夜间山谷的幽静。王维在其山水诗中,生动地传达出了自己微妙的禅悟体验,表现了一种以静为终极目的的动静情致。如“山静泉愈响,松高枝转疏”(《赠东岳焦炼师》),“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这些诗句中的动静描写,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结构,“静”的永恒与“动”的虚幻相映衬,使意境中的禅趣表现得幽妙而深切。王维还善于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空寂的意境。如《辛夷坞》描写山中芙蓉花自开自落、《萍池》描绘春池绿萍反复开合,表现寂静。《鸟鸣涧》描写夜晚山中的鸟鸣声、《鹿柴》空山深林中的人语声、《竹里馆》月夜竹林中的琴声与啸声表现寂静。前两首从视觉的角度描写寂静,后三首则从听觉的角度感受静寂,然而不论是视觉还是听觉,诗人都不是描写死寂,而是以动作、声响衬静,表现了诗人对万物静中有动,虽动而常静的禅宗思想的领悟。
王维的《山居秋暝》一诗,犹如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卷,千百年来人们对它吟咏不绝,评叹不已。在诗中,他调动各种手段,诸如层次、色彩、光线、音响等描写山水景物:“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他将比兴形象和景物描绘融为一体,使意境空灵清远。涵泳在这美好、清丽、充满自然生机的世界,怎能不令人神往、赞叹!无怪乎《涛人玉屑》称王维诗为“清深闲淡”,殷瑶《河岳英灵集》赞美其诗“辞秀调稚,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从中我们也可看出,王维融画入诗,是经常放弃时间艺术在过程中展现事物的优势,采取描绘同一时间中各种景物以构成画面的方法,通过视点的转换,景物的剪接,把时间过程蕴藏在空间的转换之中,使诗画浑然不觉地结合起来。
众所周知,王维山水诗境的最大特点是空寂,而静则是这空寂的最大表现。动作为静的对立面在王维山水诗中是为静服务的。而且,动与静是产生艺术意境的重要途径。在王维的山水诗中,动与静的巧妙运用,对于表现禅宗理念起到了积极作用。宗白华先生曾说过:“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王维通过对禅宗理念的深刻领会,从静处去认识自然、人生、社会、历史,将内心追求在动静的变化中含蓄地吐露出来,从而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领悟和审美的愉悦,激起读者心中的共鸣,达到了对禅宗理念的表现目的,从而在其山水诗中更加自然地表现出禅的境界。
王维在其山水诗创作过程中,总是以超越的方式去审视自然,将心灵与世界融为一体。从观念上看,远离尘世是王维山水诗的主旨。如果将他的山水诗细分一下,其中经常出现的,大约有隐士、浣女、渔夫、樵夫;或者是自然景物、田园、仙境、佛寺或道师、僧人,对人世间的是非是闭口不谈的。他喜用静、空、清来描绘自然环境的静美,或展现自然环境下朴素人生的恬静。前者如《鸟鸣涧》、《鹿柴》、《辛夷坞》。远离尘嚣;后者如《山居秋暝》、《积雨辋川庄作》,毫无俗念。与宋代范仲淹相比,他显然没有“进亦忧,退亦忧”的感叹,而是寄情山水,完全忘掉自己,与自然合而为一,诚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说:“唯山间之明月,江上之清风,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虽然王维与苏轼生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崇尚禅宗、佛理的情趣不谋而合。
王维诗中的景物,并不是自在的自然景物,而是经过诗人感悟后的景物,也就是说,他是以情意为主导取象,景为情用,将自然景物(山水)作为自己的知心朋友,是倾诉衷肠的对象,是慰藉心灵的良伴,所有的离别之情、寂寞之情、惆怅之情、孤独之情等等在自然的怀抱中都冰然消解。甚至可以说,离开了自然(山水)他也不复存在。因此,他一旦离开自然,便有“惆怅出松萝”的感觉,回到自然则是“相欢语笑衡门前”。王维早在19岁时所写的《桃源行》,把陶渊明所建构的避世乐土改为超世净土,以及在《辋川集》中的许多诗篇中反复出现楚辞九歌的意境,并且加以渲染有如仙境的自然风光,暗含着他对游仙、长生的追求。在开元十五年左右,王维已“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并在《谒璇上人》一诗中表达了“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的决心,他在《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指出:“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直接将性空之理运用于山水自然的审美观照,在“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中明确地表达要禅心安定以制妄心。因此诗人面对绝尘离俗的净土,不断吟咏着归意:农夫樵夫的归、牧童猎人的归、采莲人浣女的归、友人弃官归山的归,都在其欣羡肯定的语调中生动地表达出来。如《渭川田家》:“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在王维的诗中“云”也是与归连结在一起的:“与君青眼客,共有白云心”(《赠韦穆十八》),“新买双溪定何似,余生欲寄白云中”(《问寇校书双溪》),“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山中寄诸弟妹》),云是诗人精神家园中挥之不去的情愫,诗人藉此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归隐的乐园。
二、王维山水诗禅意禅境的潜因
王维精通佛理,有“诗佛”之称。在他的山水诗中所表现出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与世无争的情怀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显然是遵循社会给定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模式,并没有自觉而持之以恒的人生目标。他虽然一生离不开政治,但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他学习佛学,根本原因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并没有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从政还是从佛,首先决定于他当时的外在环境。而非他内心自觉主动的追求,所以他的前半生处于矛盾之中,最后只有在佛学和禅思中了却自己的人生。他的以禅立意的山水诗,正是他矛盾心理趋于统一的表现。这与王维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的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维真诚信佛首先当推家庭对他深刻而直接的影响。王维生于一个佛学气氛十分浓郁的家庭,其母是一个诚笃的佛教徒,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臣之母故博陵县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同时,他的弟弟王缙也同样信
佛。《旧唐书·王缙传》载:“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加之他早年信佛,与佛教各宗派僧人也有广泛的交往。王维19岁时根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改写的《桃源行》:“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就流露出他羡慕归隐之情。他曾有诗云:“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戏赠张五弟三首》其三)《旧唐书·王维传》也载有:王维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他对佛教各宗派兼取所需,大致上前期主要受禅宗北宗影响,后期倾心禅宗南宗。
真正使王维体味到禅宗对自身的适用性,关键取决于他自身起伏的人生经历。盛唐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充满蓬勃向上、乐观自信的气象。处在这样一个充满蓬勃生机的时代,“建功立业”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崇尚并为之努力不懈的目标。无论是青年时代的李白,不惑之年的杜甫,还是众多的边塞诗人,都有一颗报国的热心,王维也是如此。王维早年胸怀大志,但他并没有将仕途看成与生命同等重要。他既没有李白“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命不凡,也没有杜甫“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志向,而是在这种主流的时代心理之外,又奏出了一种强有力的第二主题。因此,从他21岁(时为开元九年)中进士,到开元二十二年被张九龄“擢为有拾遗”十余年几乎是在平淡中度过,并未苦心钻营,以政治手段为自己谋求功名利禄,而是时时刻刻去追求寂静空灵、超然于世事纷争之外的理想国度。三年之后,随着张九龄的失势,他便离开了官场。这次挫折,使王维加深了对官场的了解,认识到了其中的倾轧险恶,在与那种永恒宁静的对比之下,王维更加深感禅宗理念对他的适用性。王维对世事人情的看法,于其《酌酒与裴迪》诗中可见一斑:“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革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于是,王维走向了隐逸,走向了对于禅的追求。他下朝后或焚香诵经,或与道友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以一种山水诗的形式去反映、折射心中的感悟,从山水、佛教中寻求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超脱,从而成就了其山水诗之禅的境界。
从王维所处的时代来看,王维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还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儒释道的共同融合,最后以禅宗形式表现出来。其实禅宗的许多思想与道家思想相通相融。如禅宗之“空”与道家之“无”、“我佛一体”的禅境与“天人合一”的道境相似。儒家思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将主体的人生价值消融于客体对象世界之中,主体价值由客体而得以实现的过程就是主体性失落的过程。而道家则是以“无为无不为”的消极思想去应对世事。长期以来,王维亦仕亦隐的生活方式,体现禅宗自性清净,顿悟成佛,修行不执着于外境与道家内冷外热。即既不放弃物质享受,又保持自身的清高的主张相融合。道家虚静的思想与隐逸的环境对王维山水诗空灵静寂意境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他最后走向禅宗的过程,实质上是他由儒到道,由道到释不断演变的过程。王维所追求的是高士风范,他希望在尘世纷繁复杂的斗争中超脱出来,必然要走中国古代许多士大夫所向往的隐逸之路。在这一点上,道和禅必然是他的最终选择。因此道、禅并用,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他的山水诗中,从而使他的山水诗具有了空静超绝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无穷的理趣。
朱光潜先生在其《诗论》中写道:“诗境与禅境本相通,所以诗人和禅师常能默然相契……禅趣中最大的成分便是静中所得于自然的妙语。”在王维的山水诗中,他之所以能够很自由地表现禅的意境,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诗与禅在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等各个方面有着极微妙的联系,即诗与禅存在着内在相通性。从价值取向来看,禅宗的基本宗旨是解脱人间烦恼。通过自性净心的发现而达到自由无碍的超脱境界。无论是打坐参禅、静观暝想,还是随缘任运、自然适意,都是以摒弃物质欲望和功名利禄的追求为前提的,亦即“四大皆空”。通过这一过程,使心灵得到了一种自由和超脱而进入禅的境界。而诗的核心是审美,作为一种直觉,审美本身是无功利实用目的的,其过程是一个暂时忘却自我、摆脱意志束缚,从而从意志世界进入意象世界的过程。因此,同一事物,可以是禅的对象,也可以是审美的客体,它能同时体现禅与诗的价值,它能同时唤起佛性的直观和物我两忘的审美感受。所以,当作为诗人的王维一旦从名利场退出走向禅宗时,其诗歌创作就更倾向于纯粹的审美,而不会有孟浩然诗歌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稀”的感叹。在王维看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他是用寂然之心去观照万物寂然的本质。王维的山水诗摒弃了现实生活经验而强调自然山水的绝尘超俗之美,也许正是人生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致使诗人把理想倾注于自然山水中。但他的山水诗也不只是清淡秀雅、闲远幽静一路风格,其中不乏诸如《终南山》、《汉江临泛》等雄浑壮阔的豪迈之诗。在那明朗优美、清新流丽的诗中,隐含着盛唐特有的健康、自然、向上的时代气息,其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仍具有多样性。然而,就算是雄浑巍峨的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浩淼的长江——“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在他的笔下,也都是不沾尘世的烟火气和庸俗味的。宋黄山谷《题摩诘画诗》称:“丹青王右辖,诗句妙九州。物外尝独往,人间无所求。袖手南山雨,辋川桑柘秋。胸中有佳处,泾渭看同流。”明吴宽《书画鉴影》:“右丞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沏,水镜渊停,洞鉴肌理,细现毫发,故落笔无尘俗气。”清施补华《岘庸说诗》(五十八):“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王维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内心的坦然寂静。
从语言表达来看,禅宗的语言与诗的语言也是相通的。禅宗以“言不尽意”为最高境界,真正的佛性是不可用语言表达的,而且往往是非逻辑性的。这种语言的非逻辑性恰巧又是诗歌语言的特点。诗人往往借助不规范的语言形态去表达心中的某些感触,并且多是以一些难以用通常的语言逻辑来表达这些感触。因此,有可能出现诗语中有禅意,禅语中有诗意的现象,正因为禅宗与诗歌相互融通,最终使诗歌体现出一种“思与境偕”的空灵境界。这也正是王维的山水诗得以体现如此自然禅境的重要原因所在。加之王维自身的素养高雅,于是在他的诗中就形成了一种空灵清远的艺术意境。
总之,对于王维山水诗空灵清远之独特性所在的阐析,远不止以上论述,然而透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王维山水诗艺术手段之高超、思想内涵之丰富、艺术风格与艺术意境之独特、文化底蕴之悠远深厚以及从中展示出的独具魅力的生命意识。王维的诗性直觉和禅悟感发是相通的,他正是利用这种相通去开拓山水诗的意境,使诗境与禅境达到自然圆融。因此,王维山水诗的最大贡献,在内容上是诗与禅的融合,在创作方法上是诗与画的融合。正是这两种融合,他成功地创造出空灵清远的艺术意境,在中国诗歌史中,他是独树一帜的。虽然王维没有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恢宏、豪放,也没有杜甫《三吏》、《三别》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然而在他的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兴象超远,浑然元气”,则正好体现出盛唐时期雍容典雅、温柔敦厚、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时代风尚,成为盛唐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清诗话》称誉其诗“浑厚闲雅,覆盖古今”。长期以来,提到禅宗对王维的影响,往往只强调其消极的一面,这是不了解作为超功利和无目的性的诗歌的审美特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有了佛教徒的王维,才有了澄澈清远的王维。如果说佛教传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化的禅宗,那么王维的山水诗就是禅意的诗化。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