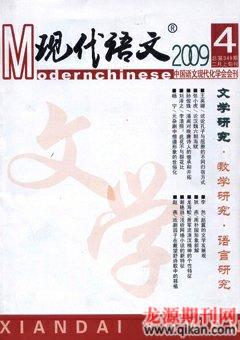苦难的存在
摘 要:在总结军旅文学的特点时,几乎所有的批评者都让视线沿着“英雄主义”的流变路线前进。实际上,如果仔细追究历史上与军旅有关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没有经历苦境的“英雄”是不存在的,而没有生产“英雄”的苦境却很多。本文选择“苦难”为线索,换个角度解读新时期的军旅人生小说。
关键词:军旅人生小说 苦难 军旅文学
一、军旅人生小说
首先,应当对一个新名词做出界定,那就是“军旅人生小说”。
这个说法来自李复威教授主编的《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中的一支——《军旅人生小说》。不过,作为一种提法,“军旅人生小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严格界定。但是,作为一种对于八九十年代军旅小说的一种相对概括性的提法,很明显,它的内涵一定与以《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小说”有所区别。但同时,它也依然属于“军旅文学”的范畴。
根据朱向前教授的“辩证”,“军旅文学”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80年代中期,“属于新时期中国军旅批评家的成功创造。”[1]由于“当代中国、尤其是近20年来的军旅文学,其描写对象更多的是相关的军旅生活而非直接的战争内容,套用‘战争文学一说,显然既不全面也不准确。”而“军旅”一词在解释上就灵活得多,既包含了历史题材的军事文学,又可以作“军人的人生长旅”解。
再结合《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2]所选的篇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军旅人生小说是以描写和平时期的军人的人生历程为主要题材的军旅小说,是新时期军旅小说的一个独特支流。
二、“苦难”三调
这里所说的“苦难”无疑与人们所熟悉的“苦难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主要由于我们对“军旅文学”中“英雄主义”传统一般化理解的遮蔽。我们在表层意义的层面上一直都很难将“苦难”与“军旅文学”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从传统、个人体验和写作资源这些方面来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军旅文学中的“苦难”事实上是全方位地存在着的。这在八九十年代诞生的军旅人生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一)“苦难”传统的嬗变
事实上,无论我们现在怎样竭力避免将“苦难”与“军旅”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却早就彼此“熟悉”了。
早在东汉末年,曹操的《苦寒行》就已经在为士兵们的苦难而叹惋了:“行行日以远,人马同时饥。”至于唐诗中的边塞诗,其中真正雄健激昂有盛唐气象的只是一部分,仍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征战和戍边的将士给予深切的同情的。对于当时的创作者而言,文学的传统恰恰促使他们把“苦难”和“军旅人生”联系在一起,在悲悯士卒们的同时将矛头指向好大喜功的统治阶层。在这里“苦难”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和当代的“苦难文学”一样极具批判意味的。所以,也并没有人讳言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这种苦难。
但是,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苦难”的意味却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作为表现革命军人“牺牲精神”或“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背景,军人所遭受的苦难被安置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在《金色的鱼钩》、《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中,作者通过表现这种苦难来震撼读者,感动读者;另一方面,又必须小心翼翼地限制对苦难的表现,否则,就很容易遭到《白任草原》那样的下场。
作为一种写作资源而存在的“苦难”。假如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苦难”与“军旅”的结合是为了批判的话,那么,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苦难”则成为了赞誉的手段。我们之所以能够一直认同这种手段,是因为中国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的经历本身就堪称传奇。所以,在当时的语境中,没有人会怀疑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在“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反应的“现实依据”是否充足。
但是,在军旅人生小说的创作中,由于没有“战争”的资源可供开掘,寻找作品的“现实依据”就成了一个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挖掘军人生活中“非常态”的部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变通之策。比如,《天天都有大月亮》中的鲁连军和其他驻藏官兵;比如《五一八二兵站》里的老郭和新兵李。他们在生活中的原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长年驻扎在远离现代社会的地方、自然条件艰苦、感情生活几乎成为空白。作为“非常态”的军人,在和平时期,他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并不亚于战争时期,所以他们的生活理所当然成了新时期的写作资源。
很明显,开掘这样的资源对于作家本人的个人生活积累要求很高。一旦个人生活积累消耗殆尽,或同类题材被过度重复,那么写作很快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所以,作家所关注的,也就渐渐由“非常态”的军人转向了军人这一职业本身的“非常态”。
作为一种体验而存在的苦难。尽管开掘日常生活中的军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旅人生小说”所处的时代使得写作的题材受到了限制。但是,当这种写作真正开始以后,很快就自觉地投入到“平民化叙事”、“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或运动中去了[2]。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旅人生小说”在写作上与“苦难文学”有契合之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苦难”与“军旅”相联系的文学传统在当代的进一步嬗变。
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在“苦难文学”中找到与“军旅人生小说”中的主题相对应的“苦难形式”。比如“农民式”的苦难和“知识分子式”的苦难。
(二)“此岸”的体验:“农民式”的苦难
无人可以否认,中国军人的主要来源是庞大的农村人口。所以,在军人形象的描摹中,“农民”的色彩一定会占到相当的比重。而在九十年代初的“军旅人生小说”中,的确出现了阎连科、陈怀国这样,在军旅小说的创作中以“农民军人”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作家。对于这种现象,朱向前教授称之为“农家军歌”[2]。
而这首“农家军歌”的基调既然是农民,那么在九十年代的背景下,农民出身的作家显然无法回避“农民”在“前创作”中已经开始被人“俯视”的现实,更不可能回避在中国社会中确实存在的农村相对贫穷的现实。这在创作中的表现就是“农民军人”无从逃避的许多“农民式”的苦难。
最明显的,莫过于陈怀国的《毛雪》。用朱向前教授的话说,“‘毛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军人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军人的新视角。”这个视角的新就在于聚焦了“农民”、“军人”两种身份交替前的短暂时间。让读者看清,到底农民军人是在怎样的状态下投入军营的。农民把军营当作“前程”。为了当上兵,在体检时就要经历一番“挣扎与苦斗”。无论是类似的内容起到的暗示作用还是作者在小说中对于小村贫困和蒙昧的种种正面描写(“爹”抽着旱烟、为了一个名额,必须四处运动……)事实上都可以纳入新时期文学中对于“农民的苦难的描述”范畴。与《毛雪》相呼应的还有阎连科的《和平雪》。二班副“老子快退伍了,党没入上、功没立上、钱没存上、老婆没讨上……”这样再明显不过的“此岸性”的目的,其实在从另一个向度上更直白地揭发了“农民军人”背负的重担。
《毛雪》中的农民贫穷,但并非革命历史小说里的“贫农”;《毛雪》里的农民算不上不高尚,但也并非韩少功笔下的“丙崽”。这种被称为“平视”的角度所体现出的是对农民境况的理解。这是只有“农民作家”才能够心无芥蒂地做到的。在“陈怀国们”的体验中,“农民军人”在以物质为主的“此岸”的生存困境是迫使他们成为行动者的根本原因。对于改善生存境遇的渴望高于“参军”本身。
同样,也正是因为这种“平视”的态度使得“陈怀国”、“阎连科们”过分地沉溺于对“苦难”的描述,因而减弱甚至掩盖了反思的痕迹。在《和平雪》中,连长、指导员、副连长三人中最具有军人气质的连长祁对诸如“走关系和被人走关系”、“扒阅兵台”这些他自己认为有损军人人格的事情的抵抗是微乎其微的。作者将内视点设在祁和老于世故的指导员杨身上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对这些事情的“原谅”态度。
毕竟,无论能否原谅这种退让,我们首先应该想到,“阎连科们”既是兵也是农民。
(三)“彼岸”的体验:“知识分子式”的苦难
和“农民式”的苦难相同,“知识分子式”的苦难实际上也建立在作家个人体验的基础之上。由于军旅人生小说的创作者一般同时拥有“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所以,较之一般军人或一般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军旅文学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重新定位问题拥有更丰富的个人感受——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知识分子,其原有的神圣地位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冲击和消解。两者在重新定位上的感受,可以说是相通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军旅人生小说中的一系列军人在自我定位时遇到的困境实际上就是军旅文学家在面对重新定位军旅文学时遇到的困境的缩影。
当他们在文本实践中导出这些感受的时候,往往形成这样一种形式:“理想化英雄的‘沙盘操作”,而这样的操作又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比如《枪圣》中的郑营副、《弹道无痕》中的石平阳。作者在着力塑造一个“纯粹的军人”形象,之后又无可奈何地以解甲归田的方式宣布了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环境中举步维艰。
在类似的“沙盘操作“中,走的最远的是涛涛的《寻找驳壳枪》。在这篇小说中,从始至终存在两个声音,一个描述在解放战争战场上所向披靡的英雄“林春和”;另一个描述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固执地恪守着军人传统而四处碰壁、最终精神失常,消失在一生中唯一一次为公众所承认的英雄行为当中的“林春和”。
与《群炮》乃至《枪圣》、《弹道无痕》相比,《寻找驳壳枪》中“理想化的军人”所要面对的困境是最为严酷的。在这里,从“革命历史小说”那里继承而来的“精神传统”被迫与世俗化的社会直接对抗(在小说中,这种对抗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林春和和聂小星身上),也因为象征着“革命精神传统”的林春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境地,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只是《军营股民》中所体现的世俗生活对于“军人精神”的蚕食和消耗,还有一种有意无意体现出来的对于军人精神在当下的生存能力的质疑:比如林春和在医院中与病友大聊军事史时,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军事知识竟然起到了“泡妞”的作用。苦心宣传尚武精神的结果竟然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反讽。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传统”和“世俗”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互抵”的。而这种无所适从的压力,无疑就构成了军旅人生小说中军人精神世界中的苦难的主要成分。
三、小结
“苦难”能够在军旅人生小说创作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一现实,除了与其特殊的写作对象和特殊的写作主体有关外,与整个文坛的“大环境”是无法分割的。
八九十年代产生的军旅小说中,个人的经历逐渐代替“历史事件”成为贯穿小说的主要线索。在军队体系中级别较低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代替高级指挥员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意识形态的目的渐渐淡化——即使出现,也包含在个人体验当中。
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相对于倾向于“史诗化”叙事的“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军旅人生小说”毫无疑问地沾染了“‘个人历史”[3]的气息。这体现在包括朱苏进、阎连科、陈怀国等一批作者在创作中,明显提高了个人体验在小说中所占的地位。然而没有八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开始在中国文坛日趋活跃这一背景,这一特点是无从想象的。
但是,由于种种特殊的限制,在努力突破“宏大叙事”的单维度叙事和“现实根据不足”的巢臼的同时。军旅人生小说依然在价值取向等方面作着一些保留。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常见的是“‘小写的历史和消弭了‘深度的历史,体现着作家在日常经验和价值虚无主义立场上悖离历史宏大诗学传统并‘自我型塑全新历史诗学的叙事伦理。”[3]其结果是:曾经的核心价值观必然承受消解。从而使得原本被遮蔽的一些情感线索能够“显山露水”,但却也很难说是否能完全取而代之。
在这样的背景下,“苦难”成为写作的元素之一,就成为了一个“生理现象”——即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要说,而比较少地承受什么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约束。
但是对于军旅文学而言,这样特殊的环境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军旅人生小说的描摹对象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无论在任何时期,社会都是报以正面的希冀。假如军旅人生小说不能调出“描摹当代军人风范”的固定框架,那么对于苦难的书写很快会被再次遮蔽。
注释:
[1]朱向前:《“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辩》,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10页。
[2]朱向前:《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军旅人生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张文红:《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李阳春:《由清唱走向和声的军旅小说》,衡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陈启明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