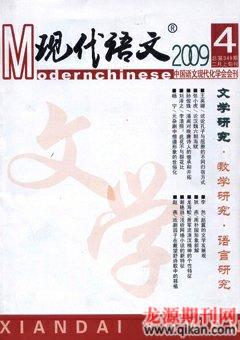赞德 鸣冤 抗争
张 强 陆 平
摘 要:《李将军列传》是司马迁倾注心血的名篇之一,在《史记》中地位独特。本文将立足原文,参照与之相关的《汉书·李广苏建传》、《太史公自序》、《卫将军骠骑列传》、《报任少卿书》等,对《李将军列传》的写作目的层层挖掘,展现太史公所要传达的志、冤、刺,从而体会史迁史笔,进入其内心世界。
关键词:《李将军列传》 李陵之祸 曲笔 无奈 抗争
梁启超曾批评“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独推重《史记》的“怀抱深远之目的”[1]。而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就是表现其理想、是非与褒贬。他虽守着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自称“述故事,整齐其列传,非所谓作”[2],但在史料的选择、编排上颇费苦心,故能成一家之言。这可以在《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3]中得到全面体现。
茅坤曾云:“(李广)乃最名将,而最无功”,然而在《史记》中,他却独受重视。
1.《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录了“其(卫青)裨将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而独“为裨将者曰李广,自有传”[4]。程不识与李广经历及地位均相当[5],但程不识只附于《李传》中简单提及其生平,与李广单独立传有天壤之别。
2.《史记》所载历代良将大都在篇题中直书其名[6],即使传主曾被封侯拜官,而以封号爵位为篇名,也在传文开首直呼姓名[7]。李广官不过前将军,而得传名《李将军列传》,且在传首被司马迁称为“李将军广者”,可见作者对其敬重有加。
3.李广与卫青都与匈奴作战,李广作为裨将,其传在《匈奴列传》之前,而卫青作为大将,其传反在《匈奴列传》之后,可见司马迁对两者的褒贬。
司马迁对李广如此青睐,有几层原因。究其最表层原因,或说司马迁能够也已经通过文字传达的,是他写作《史记》列传的总意旨。
司马迁自称他的这部著作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对人生的理解(天人之际)又在社会总结(古今之变)之先。并说要为“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立传,可见《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推崇人格美。《太史公自序》作《史记》篇目提要中云:“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这指明了司马迁为李广作传是因其仁、勇的为人,这与“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的徒为其战功大不相同。
司马迁曾在《报任少卿书》中表明他所推崇的人格美:“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李广作为武将,“善射”且“专以射为戏,竟死”,并依靠善射屡屡解困克敌,全赖“修身”之功;治军既宽缓不苟,又廉洁奉公,“得赏赐皆分麾下,饮食与士共之”,颇得“爱施之仁”、“取予之义”;杀霸陵尉,宁死不愿复对刀笔吏,有耻辱心,故有以寡陷众而不乱之“勇”;文帝为之哀,公孙昆邪为之泣,单于素闻其贤,“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立名于天下久矣。李广身兼五善,正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人格,难怪传末一连串赞词,无一字涉及其它。司马迁写《卫将军骠骑列传》,是因为卫青、霍去病的军功,而对于他们的为人,司马迁认为足可列入《佞幸列传》[8],只配列于《李传》之后,作为“忠心诚信于士大夫”李广的背景。
司马迁依五善取舍李广事迹,排列《李》、《卫》二传,是在形象化地言志,宣传自己与当权者不同的价值标准,为李广及自己的人格立万世名。
然而独此用意,虽然“太史公极力摹写”,也不至于“淋漓悲咽可泣”。在这敬慕之情下,还伏着“李陵之祸”的冤情。
“李陵事件”发生在天汉二、三年间,不在《史记》的范围之内[9]。然而如此大事,司马迁提笔作《李传》时怎能不激动呢。我们虽不能臆断司马迁是托李陵精魂于李广,但司马迁能把李广的生平写得如此生动感人,骨架来源于史料,血肉则融入了李陵的影子。故读《李传》不可不参照《汉书·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部分。现指明祖孙相同境遇如下表:

祖孙皆为武艺高强且善治军的名将,而作战遭遇的困窘如出一辙。原因则是当权者不合理的军力安排。《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就指出“诸将所将军马兵亦不如骠骑”。李广虽为宿将,但带兵不满五千,且非精兵。李陵向汉武帝求兵请战,武帝却说“吾发军多,毋骑与汝”,以至李陵以五千步兵对抗匈奴八万人马。尽管李陵与李广一样沉着勇敢,取得了巨大战绩,但李陵终无援兵,且已矢尽,最终兵败被俘。司马迁对李广的三次精彩战斗的描写,不仅集中再现了李陵兵败的过程,更突出了李陵兵败的原因。因此,《李传》在记录史实的表层之下,隐含着为李广不平、为李陵辩解、为自己申冤的不平之情。
当权者的失误造成了李广、李陵、司马迁的悲剧,更使他们及当时一大批文臣武将都经历着“不遇时”的悲剧命运。司马迁赞李广言志,借李广鸣冤,而贯之以“不遇时”三字。李广是“志”的形象,是“冤”的化身,更是“不遇时”的典型。
李广夺骑脱险以“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作结;对于右北平战左贤王以“广军功自如,无赏”作结。这两段都叙述精彩,大幅渲染了李广的勇谋,而结尾淡淡点名朝廷不公平的态度,使读者兴奋激动之后又深深惋惜,似烧炭入火,功业如烟散。读此如闻太史公英雄不遇之叹。
司马迁叹李广,也在叹自己,他与李广同病相怜。李广出生将门,司马迁出生史学世家,他们都有继承遗志、建功立业的志向。而李广虽善战,却因“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没有为自己争来侯爵,终因“迷失道”的失误,“不能复对刀笔吏”,含恨而终。司马迁仗义执言遭“李陵之祸”,因无人为其辩解,遭受腐刑。不同的是李广不愿“对刀笔吏”,甘心身与名俱灭。而司马迁忍辱苟活,“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寄托他的爱恨,夹杂对世态炎凉的社会的抗争。
司马迁遭受宫刑,更难忍的是精神上受到的侮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这是常人、哪怕是残疾人也难以理解的。这与后人难以体会阮籍身仕乱朝所发咏的忧身之嗟一样,司马迁的怨恨讥刺虽著之竹帛,也难免“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了。
如李广斩霸陵尉一节,历代都作“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10],大谬。司马迁时为“刑余之人,无所比数”,“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为世所不屑,比李广为霸陵尉所辱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情此境,纵为圣贤,能不生怨恨之心吗?李广对杀降一事颇多悔恨,知其非嗜杀之人,而不能忍以醉酒霸陵尉,只因天下多霸陵尉之徒,李广受诟已久,泄愤于霸陵尉一人而已。司马迁摘出这段史迹,更多地寄托了他对那些以地位论英雄的屑小们的报复,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垒!
司马迁不仅把小人们诛于纸上,还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而不能择贤给予讽刺。《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的顺序安排,就是对汉武帝不能择贤的批评。《匈奴列传》云:“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任将相哉!唯在任将相哉!”此正影射武帝不用李广而宠卫青。运用各种创造性手法构成讽喻环境与气氛,引人深思。
对于以上无声的讽刺,我们赞叹司马迁史笔曲折巧妙之余,更同情他如此用笔的无奈。对汉武帝的忌讳自然是一个方面,直书冤情难免使武帝大发雷霆,而抒写“不遇”的抗争之音更会招致杀生削书之祸。可除外势之外,更多的是司马迁的内情。“李陵之祸”,司马迁受的不止是刑,更是辱,刑在一时,辱则是终其一生。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反复提到“诟莫大于宫刑”,“最下,腐刑极矣”,“虽累百世,诟弥甚耳”。他可以通过《史记》写作来抒发愤懑,进行抗争,痛快骄傲地自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而当写到这篇触到他耻辱伤疤的时,“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又怎能平静地言之、辨之呢!且他认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强要言说,俗人未解其冤,反作笑柄看了,“只取辱耳”,故“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司马迁迂曲史笔与其说是为了逃避当权者的苛暴,不如说是在逃避自己内心的痛苦。所以《李传》在形式上,也是一场悲剧。
《李传》以赞德为肢体,以鸣冤为血脉,以抗争为精神,实是《报任少卿书》的注脚,《悲士不遇赋》的实证。“士不遇”是司马迁一生的主料,“李陵之祸”为它提了味。司马迁深味了这辛酸,用《李传》和盘托出,让后人品味。其实加了味的有何止这一篇,《冯唐列传》里,司马迁在赞中大呼“冯公之论将卒[11],有味哉!有味哉!”正是领我们去品味李广与自己,乃至皇帝喜怒控制下的一代士人的悲惨命运。
李广戎马一生,荣于身后,是得益于太史公的史笔呢,还是千古未断的士人们“不遇时”之缘,这些都值得后人深思。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61页。
[3]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4]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52页。
[5]《李将军列传》:“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尉卫,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尉卫”,“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将军屯”,“是时汗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魏其武安候列传》:“程、李俱东西宫尉卫,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把李广与程不识相提并论。
[6]《司马穰苴列传》、《白起王翦列传》、《乐毅列传》、《黥布列传》、《季布栾布列传》。
[7]“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淮阴侯列传》)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绛侯周勃世家》)“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卫将军骠骑列传》)
[8]在司马迁看来,卫青官至大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并不是因为他们过人的才略,而是汉武帝的私心。《佞幸列传》云:“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以才能自进。”王鸣盛云:“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子长措词如此。”
[9]《史记·太史公自序》:“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史记》中李陵事恐系后人窜入。即使司马迁后来添改,也当因此事敏感而不能尽言。
[10]陈寿:《三国志·王肃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4页。
[11]《冯唐列传》中,冯唐批评文帝对待功臣魏尚赏太轻,罚太重,“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4]吴汝煜.史记论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5]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张强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2;陆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