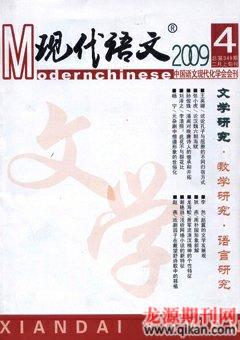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露才扬己”与“生态自我”
摘 要:《楚辞》是屈原缔造的一座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为后世学者所敬仰,成为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但是也有不同的评论,如班固的“露才扬己”说对屈原的自我形象的否定。本文以班固的观点为起点,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时代背景,进而从生态文艺学的角度重新对屈原的自我形象进行解读。
关键词:《楚辞》 屈原 班固 露才扬己 生态自我
诞生于《诗经》二百多年后的《楚辞》,因其开创“诗言情”的中国诗学观念,赢得几乎与《诗经》同等的历史地位,成为后人研究的中心。然而《楚辞》并未像诗经那样幸运,自汉儒肇始就有不同的评论,班固的“露才扬己”可谓首开先河。班固针对刘安、司马迁对屈原的高度赞扬,依经托义竭力贬低屈原,认为其人“露才扬己”,其诗多“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不能同风雅比美。
他在《离骚序》中写道: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竟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在今天看来,班固观点的出现不足为奇,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班固从儒家“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实用、功利诗教出发,评屈赋“露才扬己”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是其一;另外班固认为“君子道穷,命也。……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也。”即做人应该明哲保身,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班固否定淮南王刘安、司马迁给予屈原“推其志,与日月争光可矣”的远大抱负,因此在汉代就遭到王逸的强烈反对。
王逸《楚辞章句序》: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文章当中王逸对班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首先从屈原的人格方面有损其清洁、忠贞的形象;其次指出认为屈原“怨刺其上,强非其人”的不合理性;最后高度赞扬“屈原之词,诚博远矣”,“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笔者认为王逸的评价是中肯的,不仅有利于对屈原做出一个正确的评判,聊慰屈之在天之灵;而且会更好的推进学术界对屈原的研究,从而恢复了司马迁等人给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荣誉。
屈原为何会让班固产生“露才扬己”之想?除因前面提到的原因外,我们还可以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按西方现代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的观点,人类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智力”的或称“有指向思维”,和“无指向”的或称“我向思维”。前者是自觉地、理智的、有明确目标的追求,适应现实并试图影响现实。后者是潜意识的、非自觉的,所追求的和急于表白的,往往在理智范围之外,不适应于现实而欲创造一个想象中的美的世界,因此它更具有个人、个性的特征,并主要借形象、意象呈现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称“有指向思维”为“直接思维”,称“我向思维”为“幻想思维”:“第一种思维与现实密切联系并依靠现实而活动,后者却从现实转开追求主观自由”,它“不约束我们,它很快引导我们离开现实而进入过去和未来。这时,表现在语言中的思维停止活动,而想象纷纷聚集,感情生发感情”,这时感情是“依照它们自己的引力自由浮动、升沉”。[1]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屈原当时的创作心理的话,我们会发现屈原的创作思维是“我向思维”或为“幻想思维”。屈原在作品中使用大量奇特、绮丽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神话思维大胆的突破时空、地域的界限上天入地,让天上人间漂浮不定,但是诗人靠着“情感”这根主线把现实与理想紧紧窜连在一起。诗歌的发展是随着“情感”的起伏跌宕来谋篇布局的,所以有人说屈原的诗歌是意识流创作。而班固谓屈原“露才扬己”这是一种“有指向思维”,把屈原的诗歌当作沟通君臣,追求政治仕途的工具,以达到“怨刺其上”的目的。把文学的本性功利化,不利于我们正确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心旨意。
文学是审美化的“人学”,文学是艺术家体验生活表达于笔端的现实世界,在作品中必然要渗透艺术家本人的主观情感。当然作品也并不是艺术家生活的简单写照,而是通过凝练的带有社会普遍性又具有个性的社会生活。艺术接受者在阅读作品时又会生成一个形象,这一形象可能与艺术家表现的形象有距离,因为时代的变迁、生活的环境及个人的遭遇都会影响形象的再现。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如何评价艺术家的自我形象呢?这完全是由选择的角度所决定的。
就像今天我们从生态文艺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屈原的自我形象,也可用四个字“生态自我”来概括。生态自我是深层生态伦理学的一个概念,深层生态伦理学是一种生态中心论世界观。它的一条根本性原则,就是“自我实现”原则。实际上,人不是与自然分离的个体,而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自我实现的“自我”是形而上的“自我”。它的成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到“社会的自我”,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即“生态自我”。这里所说的“我”不仅包括一个体的人,还包括全人类,包括所有的动植物,甚至还包括森林、山川、河流和土壤中的微生物等等。“生态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超越整个人类而达到一种包括非人类世界的整体认识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扩大和加深,人与自然其他存在物的疏离感就会逐渐缩小,便能感到自己在自然之中。当人们达到“生态自我”阶段时,就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也能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2]
屈原在作品中是怎样实现自我的呢?屈原对于个性自我与社会自我关系的认识虽不能说具有完全的生态哲学思想,但至少在对于“自我”的认识上,已经表现出了初步的生态哲学思想。首先我们在阅读《楚辞》时,都能领会到屈原那种“发奋以抒情”的特征,当然就是我们浅层意义上所说的,屈原在诉说自己那坎坷的经历和表达他强烈的政治理想。但是我们就此狭隘的理解,整个《楚辞》成为了一部个人恩怨的诉说书,还有何文学价值呢?文学是客观与主观结合的产物,主客关系的转换以及主体化的升级,所呈现的生态性的转换,所构筑的艺术生态世界,必然是主体所理解、把握、体验的独特的生态存在系统。其生态性转换是由自然、社会到精神性体验的不断升级,是不断地由外向内的转换,同时,在转换中既体现了生态主体性的三重融入关系,也表现了主体生命活动的演历过程。
首先,自然生态关系融入
屈原在《楚辞》中描绘了诗意的自然,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成为诗人的衣食住行的依托。“扈江蓠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柴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帏,劈蕙榜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分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诗人以香草为伴,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诗意化、自然化。这既是诗人生活的优美自然的反映,又是诗人生命体验的超越。
其次,社会生态关系融入
屈原出生高贵,皇族后裔,“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前期是国家栋梁,仕途一帆风顺,直至左徒,深受怀王信赖与爱戴。然而,后期受谗被放逐,一落千丈,但是诗人忠心爱国、爱君的热情并未改变,思慕能够回到朝廷为国效力却未果,成为一个沦落才子。可想而知当时诗人的心理、精神是遭到何等打击,所以他处在一个极不平衡的社会精神生态关系之中。
第三,自我存在的生态关系融入
屈原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正如诗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可见诗人不仅品德高尚还非常注重个人修养的提高。同时,诗人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声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些诗句都清晰的表达了诗人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诗人坚定的人生信念,与至死不悔的人生理想溢于言表。他的这种强烈的、被激活的精神生态体验,是通过感受自身的生命景况来体验自身的生命自由精神。
所以,屈原在《楚辞》中为我们展示了“自我”的升华过程:即从“本我”到“形而上的社会自我”再到“生态自我”。达到了自然、社会与人生融合,《楚辞》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完美结合。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基金项目(YC08A084)。
注释:
[1]吕俊华著:《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7-118页。
[2]熊安沅,陈东:《生态自我的觉醒——解读多丽丝·莱辛的〈日出草原〉》,《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周秉高.楚辞解析[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2]盖光.文艺生态审美论[M].人民出版社,2007.
[3]余谋昌.生态哲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谢北方 抚州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 34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