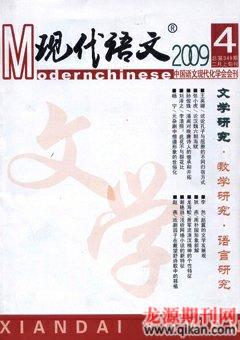从《蒙古秘史》看北方草原的民俗文化
摘 要:《蒙古秘史》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部草原文学巨著,它采用编年体和纪传体相结合的形式,成为记述蒙古族历史最早的典籍。而其中所涉及到的蒙古族民俗文化,如表现人与动物的依存关系;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游戏;与众不同的饮食文化等等,都成为了至今还在北方草原传承的宝贵精神遗产。
关键词:《蒙古秘史》 民俗文化 北方草原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是迄今为止蒙古族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这部书既是研究蒙古历史、语文的珍贵典籍,也是记述成吉思汗生平事迹的优秀传记文学。它是12—13世纪游牧民族罕见的第一部草原文学巨著,开拓了草原民族以文记史、文史结合的历史传记文学的道路。它熔民间传说、历史事件、人物活动于一炉,采用编年体和传记体相结合的形式,记述了蒙古诸部在北方草原上的纵横驰骋,以及他们的祖先起源传说、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心理、娱乐庆典等,组成一幅草原生活的历史画卷。作为一部蒙古民族的典籍,《蒙古秘史》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极其深广,内容涉及宗教、民俗、民谚、制度等各个方面,以下仅就这部书中所体现的民俗文化作一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自从蒙古族来到北方草原后,这里就成了他们世代生息繁衍的故乡。在生存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极为丰富和独特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前身是游牧文化,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游牧经济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慢,但是体现着北方骑马民族的心理素质、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的游牧文化却时有发展,乃至出现较高水平的文学艺术。游牧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升华为今天仍在北中国大地上独领风骚,为世人瞩目的草原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内容上,与畜牧业联系十分紧密。表现人与动物的依存关系,表现各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生态平衡,将动物人格化乃至神化等等,是草原民俗文化的普遍表达方式,并在草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身边最忠诚勇敢的英雄当推“四杰”、“四狗”。成吉思汗的三弟、勇猛无比的合撒儿,也是以狗的名字来命名的。为什么会将英雄们称为“狗”,汉族读者感到难于理解。固有的审美思维定式告诉我们,举凡与狗有联系的事物和词汇,负面远远大于正面,但在这部书中,明显是将其作为歌颂或尊崇的对象。如纳忽崖之战时,作者借札木合之口对诸位英雄的描画:“额如生铜般坚硬/舌如锥子般尖长/心如钢铁般无情/牙如钉子般锋利/四条吃人的疯狗/挣脱其钢铁锁链/欲吃我人肉尸骨/垂涎三尺狂奔而来/饮朝露捕飞禽/骑乘风暴疾如飞/射弓箭舞刀枪/素以战器为伴友/此来四条疯狗者/乃为蒙古大战将/者别、忽必来二人和/者勒蔑、速别额台也!”[1]再如著名的“感光生子”神话:“每夜,明黄人,缘房之天窗、门额透光以入,抚我腹,其光即浸腹中焉。及其出也,依日月之隙光,如黄犬之伏行而出焉。汝等何可造次言之耶?以情察之,其兆盖天之子息乎?”[2]汉族的神话中,也曾多次谈到降生非凡人物前的种种异象,如吞燕卵、踏足迹、菖蒲花吞、飞燕入怀等,但却从来与狗无关。阿阑豁阿不仅形容此神人“如黄犬之伏行而出”,且言“以情察之,其兆盖天之子息”,缘于何由?《蒙古秘史》开篇提到:蒙古人的始祖是孛儿帖赤那,即苍青色的狼。据学者分析:“他们以‘狼为部族名称,并以狼为兽祖。狗是由狼驯化而成的一种家畜。因此,越往遥远的过去追溯,狼和狗的区别越不明显。所以,以氏族制为主的原始社会里,作为图腾的狼和狗在一些场合里可以相通。”[3]这部书中以“黄犬”来预兆“天之子息”,是否在暗示它是“始祖”的化身?而以“狗”来比喻英雄,是因为他们既有狼的凶猛又有狗的忠诚,因而更得蒙古人的喜爱。即使到了今天,蒙古民族仍然有忌打狗的习俗,在他们看来,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尤其在游牧生活中,人和狗结成了密切的伙伴关系,狗是主人的好帮手,甚至被当作家庭的一个成员来看待。所以,蒙古人对狗充满了人性化的关爱甚至拿它来比喻英雄也就不足为奇了。
蒙古族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马”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作战物资和作战武器。《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先祖孛端察儿在兄弟分家时,“马群家资”俱与其无缘,只得到一匹被弃的“脊疮秃尾黑背青白马”,他行则骑乘,食则以其尾毛为套捕鹰而猎,逐渐生存了下来。幼年帖木真与孛儿帖订婚时,由于其父也速该当时并无他物,“遂赠其从马为聘礼”。马既然是蒙古人家资和财富的象征,许多战事便和马有了密切的联系。如《蒙古秘史》卷二记载:少年铁木真由于家中8匹骏马被贼人抢去,遂开始了平生第一次主动出击,不仅夺回了自家的财产,还结识了毕生好友、“四杰”之一的孛斡儿出。成吉思汗首次独立指挥战争的“答阑巴勒主惕之战”,是成吉思汗与其“安答”札木合之间的战争,起因正是成吉思汗手下与札木合胞弟之间的一场“抢马纠纷”。“纳忽崖之战”是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役,历来以其精密的排兵布阵之法而广受称道,殊不知这也与一场由“马”引起的意外有关:成吉思汗哨兵的瘦弱青白马被乃蛮哨兵夺取,暴露了兵力情况,为应对此变故,蒙古军队才采用了点燃篝火疑兵、“进入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4]的战略战术,从而大获全胜。可见,在蒙古人与草原之间,马是一个重要的中介。谈论蒙古人,评价蒙古族历史,解读蒙古族文化,都离不开马。马是蒙古人创造奇迹的最重要的工具,蒙古人对马有特殊的感情。他们爱马、敬马,把马当做自己不可须臾或离的忠实伙伴,进而引为自己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的象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赞美马、装饰马,并把这种感情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使之成为一种马文化风俗习惯。而这种马文化的形成,正是游牧经济生活作用的结果,也是草原民俗文化中精彩而有代表性的部分。
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代代相传着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狩猎技艺,就是利用鹰来捕猎野兽和飞禽。鹰是蒙古民族不可或缺的伙伴,更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捕猎工具。《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先祖孛端察儿被兄长遗弃后,无奈之下驯养了一只雏鹰,他靠这只猎鹰捕来的猎物维持生存。后来他的后代繁衍而成孛儿只斤氏,因此这个部落把鹰作为保护神崇敬了起来。从此以后,鹰既是蒙古民族特殊的捕猎方式,也是令人敬畏的神明的化身。德薛禅之所以给女儿与铁木真定下娃娃亲,与他“夜得一梦,梦白海青握日月二者飞来落我手上”[5]有很大关系,再加上传说当中猎鹰曾救过成吉思汗性命、蒙古人崇拜信仰的萨满教巫师又将铜鹰戴在神帽上来表示神鹰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鹰就成为蒙古人普遍尊崇的对象。
蒙古游牧社会天宽地阔,人烟稀少,因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蒙古秘史》几次提到了“摔跤”:成吉思汗之弟别勒古台利用摔跤的机会,杀死了主儿勤部的国手不里孛阔;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用摔跤的手段,报复了气焰嚣张的通天巫阔阔出;成吉思汗选定继承人时,长子拙赤又欲以摔跤、射箭来和察阿台一决高下。台湾蒙古族学者扎奇斯钦分析说:“游牧社会的日常生活是比较寂寞一些……为了打破寂寞,蒙古人常常唱歌,或是吹口哨,有时也只有对自己歌唱而已。”[6]而在此种条件下生长的儿童们,幼畜和小狗就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他们日常的玩耍也是以羊、黄羊、牛、骆驼的髀骨为主,或者是成人使用的武器雏形。《蒙古秘史》记载:当铁木真11岁时,曾与札木合结为安答,那时二人正在斡难河的冰面上玩击髀骨游戏,因此互送的礼物就是动物髀骨制成的精致玩具。一年后,二人玩耍时重新结为安答,互赠的礼物则是射箭用的箭器玩具。如今,摔跤、射箭和骑马成了那达慕大会的传统“好汉三赛”。可见其魅力之久长、影响之深远。
《蒙古秘史》所体现的饮食文化更是充满了草原特色:古代蒙古人多以捕獭儿、野鼠为食;春天的时候,阿阑豁阿母亲给孩子们吃的是风干羊肉;桑昆以婚礼上要吃“不兀勒札儿”诱骗成吉思汗前来,也正是利用了蒙古民族的古老婚俗。“不兀勒札儿”是动物的颈喉部,因其骨骼结构复杂,连接紧密而被用来象征婚姻的牢固,至今在蒙古族的结婚仪式上还有让新婚夫妇共吃“羊脖骨”的习俗。
另一方面,草原文化也寓教于乐,往往能起到一般政治说教所起不到的作用。《蒙古秘史》卷一记载:阿阑豁阿母亲因为教育五个儿子要团结,先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箭命其折断,五人很容易就折断了;又将五支箭束在一起,令其折之,则无人能做到。因而母亲告诫他们说“汝等五子,皆出我一腹,脱如适之五箭,各自为一,谁亦易折如一箭乎!如彼束之箭,同一友和,谁易其如汝等何!”[1]“箭”是古代蒙古民族的重要武器,因而也是权威的象征,“折箭训子”的教诲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和不团结的危险性,故事本身虽带有神话传说色彩,但却显示出民俗文化的巨大意义。《蒙古秘史》卷六:成吉思汗派人去劝说王罕时作了这样的比喻“夫两辕之车,折其一辕,则牛不能曳焉,我非汝如是之一辕乎?两轮之车,折其一轮,则车不能行焉,我非汝如是之一轮乎?”[7]这种来自草原生活的新颖贴切的比喻,在这部书中俯拾皆是。它不仅为草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强化民族意识,唤起民族感情的极为有效的方式。
从《蒙古秘史》所体现的民风民俗中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的社会行为,都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化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但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同时从其深层来讲,文化体现着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形成人们的潜意识,形成支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一种习惯定式、群体崇尚和民风民俗。文化对于社会的意义和作用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它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但又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注释:
[1]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蒙古秘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2][4][5][7]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第188页,第28页,第153页。
[3]那木吉拉:《犬戎北狄古族犬狼崇拜及神话传说考辨》,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49页。
[6]扎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7页。
(王素敏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014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