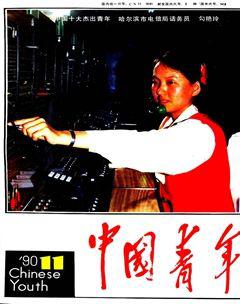妥协和吃饭
艾丰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在各地吃饭,偶尔也有机会出国吃几顿洋饭。吃饭的基本作用是解饿,但吃饭也是一种文化。吃饭常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这里想说说吃饭引起的对妥协的联想。
我出国的时候,最担心的总是问题之一,就是吃不惯外国饭。回国之后,朋友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常是:你吃得惯外国饭吗?老实说,外国饭是吃不惯的。出国时,吃外国饭,一是不得已,二是为了尝尝新鲜。但总有吃不饱的感觉。为了保证有充足的精力,我总是希望吃中餐,特别是到中国人开的中餐馆去好好补充一下。在中餐馆吃饭,饭后,店主人往往要问上一句:我们的饭菜是不是真正的中国味?我们大都回答:很好,是很地道的中国味!
我们这样说,其实有点客气,带有相当的妥协成分。因为考虑到是外国的中餐馆。严格地说,这些中餐馆的中国饭菜,其味道已经加入了相当多的西餐成分,因为来吃饭的顾客,中国人毕竟很少,多数还是当地的外国人。尽管这些人目的是想品尝一下中餐的味道,但是,店主人为了讨他们的喜欢,仍然不能不作一些妥协,加一点西餐味道。
这种妥协在国内也可以看到,现在许多大饭店,吃中餐的时候,常用分餐制。中餐原本是合餐制吃中餐用分餐制,不是对外国人习惯的一种妥协吗?
讲了半天吃饭,是为了引出一点认识:对妥协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看法。
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妥协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们认为,妥协就是“退却”、就是“怯弱”、就是“无原则”、就是“和稀泥”,甚至认为妥协就是“失败”。他们还认为,讲妥协的人,是“圆滑”、“世故”、“没有革命精神”。这大多是由于幼稚产生的一种片面认识。
妥协,其实包括着很复杂的情况。有消极的妥协,也有积极的妥协;有不必要的妥协,也有必要的妥协;有无原则的妥协,也有原则的妥协;“有不正确的妥协,也有正确的妥协……针对一概反对妥协的思想,也许我们该多讲讲妥协的作用和在许多场合下的必要性。
在社会上,人和人之间要相处、要交往、要共事,谁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愿完全强加于人。你强调主体意识,人家也要强调主体意识啊!这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有人说,一点都不妥协,再情投意合的夫妻也要分家、打离婚的。这并非戏言。因此妥协包括着一种对人尊重的意思。
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对我们来说,都存在着利和弊两个方面,我们只能权衡利弊,取利大弊小者,而不可能幻想百利而无一弊,这不也含有妥协的意思吗?在决策上,尤其是政治决策上,这种情况尤为多见。不是有“小不忍而乱大谋”的说法吗?“小忍”者,妥协也。外交谈判当然是一种斗争,就其现实目的来说,实际上双方都是在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妥协。妥协在这里又成了达到长远目的的一种手段。善于争取到对自己最有利的妥协,成为外交艺术。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任何理想的实现,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因此,在实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在实际步骤中,即使是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但在每一步上,我们又不得不容忍一些不符合我们目标的东西存在,不得不向现实条件妥协。改革是一种革命。但改革的过程中也充满了妥协。许多价格明明不合理,可一时就是解决不了,“脑体侄挂”的问题要改革,喊了多年,成效并不大。面对这些问题,如果一点不容忍,一点不妥协,又将如何?急于求成的思想已经害得我们好苦!
妥协,有时甚至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创造,起码是一种灵活运用。北京卖的担担面,没有四川的担担面那么辣,它是向北京人口味的一种妥协,其实也是一种灵活运用。日本人学西方,并没有完全抛弃从中国学去的传统文化,而是从日本的实际出,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就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来讲,也是一种相互的妥协,但这种妥协产生了新的东西。
上面的这些话,简直成了“妥协颂”了。不过我认为,鉴于我国过去多年片面地讲“斗争哲学”,“分的哲学”,“10亿人口不斗争行吗?”多说说妥协的这一方面,恐怕是必要的,特别是对年轻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