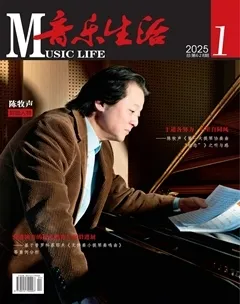与君相惜 与众同行
当下,音乐艺术审美活动已然成为雕琢人格之美的关键路径。追溯中华传统文明的深邃轨迹,孔子这位标志性智者及其哲学理念,无疑是中国古典审美思维领域里,首屈一指地重视并推行美育以塑造人格的光辉先驱。孔子的“忠恕”[1]哲学与“仁论”中的“意象”精髓,深刻铸就了华夏子孙绵延不绝的共情基因。这份共情,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下,逐渐蜕变,与艺术等多元领域交织,共同孕育出独特的审美思维传统。这一传统,紧密融合时代变迁、环境风貌与族群特质,彰显了艺术审美活动的教化力量与实用价值。其背后,是坚韧的审美意识框架,映射出入世、在世的哲学观念。这种既内省又外拓的情怀,凸显了中国古典文人“儒风”的非凡魅力。它使艺术人格在无声无息中,顺应社会规范,焕发出盎然生机。孔子的智慧,犹如一股甘泉,润泽着华夏儿女的审美天地,让艺术之美与人格之善,在历史长河中交相辉映,璀璨夺目。
一、“忠恕”意象中的艺术审美规定性
孔子在其思维意识上的瞄准姿态与尊崇品格,本质上客观地构造了中国古典艺术审美思维的规定特质,这已集中地体现在艺术审美立场、艺术审美标准、艺术审美旨趣等方面的意识确立与规约缔造之中。他的“尽善尽美”“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审美命题的提出以及褒扬正统并贬斥偏俗、积极发扬“兴”之审美手段、细腻省察艺术家主体审美意趣等审美态度,均使其哲思学意本身具有着诸多的思辨力道与智慧闪光点——通过整合艺术审美范畴并使“美”范畴拥有了学理独立性[2];通过塑造艺术审美立场与审美尺度,通过言说与表达艺术审美好恶,通过强调主体审美活动(特别是欣赏活动)对于审美主体性的艺术激励、艺术净化与升华功能,通过融汇主体间性在艺术审美过程中具体化的创演实践与接受品鉴,通过内在认知与宣化情感方式,通过承继古典永续与适度弥新张扬,通过艺术感性与艺术理性共在共存,通过审美个性自我与社会性存在方式互恰等……让渗透于社会文化生活当中的艺术审美问题最终达成了主体统一。
这种具有审美能动的哲思情势所形成的艺术审美能力、赏析判断与认知能力以及艺术审美诠释能力都是极为强大的,它让这位距离当代人太过久远的、积极整理华夏优秀典籍、述而不作并致力于恢复周礼的孔子思想意象,能够不断地为后世发散出意义深远的哲思影响力,助力于后世的接受主体的艺术人生观的合宜养成。从艺术哲学的本质思考层面上说,正是因为在孔子的这种充满了开明、新兴、儒雅、稳重等人文情怀与精神隐喻的古典思维意识中,在其外在与内里都表现为一种非特意化的、非刻意化的、非强势概念类型的思辨方式存在策略,就相应地摆脱了所谓僵硬、决绝、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陷入概念的旋涡等认知误区。由此这种包含了中国古典意境生命力的孔子意象存在策略,显示的则是上古时代的那种独特的、积极的、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处世风度,这在中国古人思维意识的智慧“宝山”中,就必然闪现出如何适度构建主体化的人性自觉、如何积极建设照亮型人格并观照到内心需求目标的审美频率上,从而发出柔和的、温暖的、宏毅的、朴厚且持久的美学光芒!
也正是因此,作为审美接受主体就不难理解审美历史上为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历时性的审美标签刻度——1. 南宋理学大儒朱熹评价孔子时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喟叹意味以及何以用情至深来颂赞的主体缘由。2. 船山先生何以在《薑斋诗话》中以排比长短句形式做出审美品评与论证姿态,深究其“兴观群怨”论为基准并以此搭建逻辑交缠、往复叠加所形成的“兴可观”“观可兴”“群而怨”“怨而群”等复合审美判断之样貌,并进而引发出的令人拍案叫绝的逻辑序进能动,也即更进一步地在逻辑层面上构型出了的“深兴”“审观”“不忘怨”“益挚群”等特质。3. 中国近代求创新图进取的革命先驱、新儒学肇始人之一的康有为,何以能够积极地评价孔子思想之恒道,并凭借其本(仁)、理(公)、法(平)、制(文)、体(明)、用(易)维度的反复阐发而得出时代条件下思维新意的具体缘由。4. 世世代代的接受主体何以能够不断地履行由礼而德、由德而人、由人而国、由国而天下的修身养性、心怀天下之全然路径……这些审美标签刻度般的经典品鉴言说,对于接受主体在审美意识中积极明确孔子“忠恕”意象的哲思本质规定性,是有着积极的参照价值的。
二、“忠恕”意象在自我和他者审美关系建立中的独到之处
能够以审美意象的本质推动力来完善自我与他者的审美关系建立问题,对于笔者而言这意味着某种极其睿智的哲思意识的存在方式。在孔子“忠恕”意象为整体处世原则及人文背景的相应举措上,阐明这个层面的问题思路首先体现在艺术体察方式与观照角度等艺术实践行为的深刻性之中,由于孔子提倡的是在艺术本真的追求路途上应当恒久地坚守某种姿态——去实施直观的、感受性丰富的、朴素又具体的艺术行为,同时能够直陈所见地而非论证化地、辩护化地、歧义阐发化地外播主体的审美感受性体验,因此这样做的审美结果便是以此获得对主体间性审美共识的最直接、最本然、也最善意的方向性指示;审美思路其次体现为在审美活动的具体化过程中,在各自环境、群族、时代条件下的审美主体可以不断形成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具体实现状态,也即对一种应当而作、理应而为的审美品格的切实贯彻,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自我激励方式,是在拥有了中国古典的审美敬畏心的前提下,所倡导的主体审美能动方式,这种方式也必然拥有着自主性、自发性与成就他者的审美主导性情势,这种情势继而能够很好地克制非自主的客观性境遇,以仿佛“无目的的合目的性”[3]之哲思原则来达成中国古典意趣的“追寻真正之必然”的果效,并最终成就了审美观照境遇中的己身。
因此《论语·述而》篇里所讲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审美命题,或是《论语·泰伯》里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具体化审美观念,都可以理解为是由于孔子思想的“忠恕”意象发挥了根本的哲思推动力,其作用是独到地显现为——在自我与他者的审美关系建立中,对于上古礼乐的必然确立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意识,这同时也就自然地应和到了已故的李泽厚先生在其《华夏美学》专章中所写就的审美观念——尤其是对“游于艺”“成于乐”等艺术论域而言的一种主体人格完成的标志之说[4]。这个被大哲学、大美学、大批评界普遍诠释的审美论域,不仅对相应研究领域的审美学理意义重大,更是对于音乐艺术审美活动、特别是艺术哲学视野下的音乐美学原则的更新、音乐批评策略的理路优化等,也是同比有效的,尤其对于接受主体如何能够在审美感兴之中不断萌生出合理的、适度的、可阐发的、可外播的艺术审美体验问题等,会给予温良的意识根基构建。
由此而言,自我与他者在艺术审美的具体过程中,其审美关系的建立类型将主要聚焦于:合于本然之度的审美意识的指向性;艺术审美心理的本真伦理感;艺术审美目标的可持续、可进化的包容性;艺术审美素质在主体反映理论与实践环节的完备或全面状态(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六艺之功等需求);艺术审美行为方式引发的高品质的审美愉悦感;艺术审美底蕴中对于古典仪式之美、古典形器之尊、正典的服饰纹华之全备化的纯然接受;艺术手法与修辞策略的规范化与纯熟度;合于社会普适审美追求又兼具个性化艺术审美特质的艺术本位状态;审美外化形式上的合宜的艺术审美主体姿态,等等。而这种实则全面化、系统化、高端化、规范化的艺术审美综合体的存在方式,彰显出的有可能达到的主体间性的审美愉悦公约度是可期待的,更是不言而喻的。因其在必然的合乎古典艺术本质规律、尊重传统艺术创演天然本性的过程中,所触及与所言说的,亦会是作为社会价值属性的审美主体的人之常性,这种审美主体常性是充分勾连了自我与自我之外的一切可能性(并极其突出地勾连了同为社会人的他者)在审美共性中驰骋而出的愉悦之感,因此这种主体间的美好关系的构建思维意识,是卓越且优化的艺术审美人格的体现。
三、“忠恕”意象相关的艺术审美经典案例枚举
正如孔子的哲思言行是与其身心所在之环境、群族、时代及其社会文化生活密切隼接的情形一样,构成的是一种主体化体认中的切实有效的审美感悟力,因而有关其“仁论”宗旨的“忠恕”意象也是与孔子生命历程中那些具体化的方方面面融合一气的,而“孔韵”十足的艺术人生观则渗透于孔子艺术生命的审美实操行为之中,这些艺术行为又鲜活地构建了感人至深的古雅韵味和传统古典情结深重的社会文化事件,特别是对音乐艺术以及更为广泛的艺术论域而言,仿佛来自千年前的音乐前辈的言语身心,在审美情境中身体力行地告诫着、劝慰着在乐言乐者该如何面对音乐世界一样,能够跨越时空地依旧发散出雄浑的艺术人文光辉一般。笔者谨在此罗列一些经典例证共勉于读者,并致以对上古贤君艺术人格的敬意。
首先,是其“贵士”的艺术格调。众所周知,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为了能够让他心目中的礼、义、仁、智、信获得真正长久生命力的可能性,为了痛惜“礼崩乐坏”的审美初心,他恭敬地去请教同时代的老子对此的想法,他常年奔波于诸侯列国中渴求治划方略上的根本认可,他大力呼吁社会对礼乐思想的重视度,他倡导“箫韶”“大武”等正统之乐并提醒人们避免接触那种失份、失当或仅能达到人的感官本能层面上的欢愉之乐……这种深厚的主体化反思力度之行为背后,其不可小觑的哲思意味会指向到一种微妙的“贵士”隐喻度。“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应可有泛指、特指的各自涵义——“士”可泛指时,可以笼统地将上古时期具有先进思想力、革新力度的先贤们全部纳入其范畴,也即上古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人文的身份代称;特指的“士”则是规约到当时“无故不下琴瑟”的末流的贵族阶层,他们代表了一种懂得乐律、精通演奏、深谙赏析之道的广普情怀的文化者。无论泛指、还是特指,“士”的艺术与文化属性的确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主体人格的文明属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贵士”的哲思本质意义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重视礼乐教化、尊崇古雅正典之乐)的一种主体情感的倾向性表现,而孔子自身的主体性及其人格魅力在本质上也隶属于古贤之士气,因而他的“贵士”意识在根本上也是其同时正视自身、尊重自身的某种别致化表达,由此意义上说,笔者追索孔子思想在音乐艺术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现,理应从他本然状态的“贵士”情愫中来探赜一二。
其二,是其“依乐而不自陷”的艺术情致。这是针对孔子与其爱徒能够于人生困顿之中以声、以音、以乐为乐且为藉,并不自陷于陈、蔡之窘境的豪迈情状而言的。熟悉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人都知道“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这个经典的以乐励志的故事,人们固然会从《庄子·杂篇·让王》的精彩记述中被深深感动,但孔子在这个经典案例上除了体现出伟大民族教育家的风格之外,更是展现了上古时期具备优秀音乐文化修养的一种主体人格魅力。他在特殊的环境中体会了苦中作乐、自奋自强的豁达姿态,他使用枯槁之木虽然敲击不出合乎音律要求的节律,但其内心中的律动在这种生命境遇的至暗时刻已然焕发出人文精神的隽永光华;他在无饮食而导致肌体羸弱的生命气息中慨然长歌,在可以想见的困窘条件下全情唱和出大我生命样态的庄严之感、存在之境,这种主体艺术行为不仅激励了其自我之信心,更是为追随他的学兄子弟们释放出了深刻的、坚定的艺术主体信念,艺术审美能动的神圣性、抽象性以此便焕发了巨大的生机,让孔子毅力超拔的、乐观且积极的“不自陷于困境”的人生态度,映射出了孔子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必然显现的对于艺术理念的坚定价值立场,它不仅对上古时代、也对后世乃至当下艺术世界的艺术生活观念,均有着人文引领、推动主体审美修为的积极意义。
其三,孔子艺术实践行为之更甚者,是其“托意幽兰以象品节”的艺术家风范。孔子在区分美与善、分别好与恶、辨析得与失的审美过程中,不断地体悟、体认并构建着艺术审美标准下的圆融旨趣,他运用自身具体的主体化在世体验,巧妙地嵌合到“空谷幽兰”的意象审美对象之上,凭借古琴曲创、古琴演奏、古琴品鉴的三位一体的艺术家全能素养,偕同他自身广博的知识分子内在贵气,展开了对幽兰独茂于野、幽兰惟香予王者、幽兰怅然似有所思等审美意象的艺术刻画[5],凸显了“忠恕”意象核心命题对于神奇的命运、现实的人世间、本真的自我与熙熙攘攘往来奔赴的他者所进行的别具生面的审美隐喻——即便是处于尘埃之境也要以有度(即不为过犹不及)、有量(即从事物两端的平衡之处来着眼与着手)的内在塑造力去超然自我,这种品格的艺术实践所成就的则是一个中国上古时代卓越知识分子无限喟叹生命本质、感喟生命意味的活生生的审美意象图示。可以说,无论是在东汉蔡邕的专文记述之中,还是在当今审美接受主体的感悟力之下,孔子的这种意象美感的深刻性,都在无尽地延续着其可旋变更新的生命动力。
其四,是其巧妙采用了老子的生命本体论智慧。作为中国古典思想儒家文化的开山引领者,孔子虚心好学的状态体现出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他在问道老子之后、盛赞老子为人文意义上如“龙”一般的存在价值之后,又从言行本质上策略性地体用了入世豪情中的合宜的道之言说,这在笔者看来其实是他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大隐隐于市”“和光同尘”的人生定位,这也势必为孔子生命中的艺术人生观在属于儒家“仁论”思想风范的学理包容度和实践能动性上,勾勒出了一种别样的哲思底蕴感与意象思维色彩,这种底蕴与色彩也将更加助力于孔子艺术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具体化艺术人格。因此,孔子可以从一而终地去执行“天”“地”“人”合理共在的艺术生存之道,将艺术审美的诸种可能性尽力地实施为普适美感的现实性价值,从审美范畴的独立化过程中来探究审美真理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可以使得人类在命运共同体进化的过程中,将本能层面但又惯常的(自我与他者)的排他性状进行强有力的价值扭转,从而实现与建立了主体间性中那些良好的社会性征,这对于独特性、抽象性意味强大且深远的音乐艺术而言,是尤为珍贵与重要的。
在本文即将结尾思绪的地方,还想分享一个宝贵的治学心得——在2024年10月26至27日的第十三届全国音乐美学年会上,作为分会场参会、听会主体之一的笔者,有幸听到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教授主旨发言中引论《史记》“礼书第一”的精彩见地,他阐发而说的“礼者,养也”的道理,令笔者的意象神思与艺术观体悟问题进入到豁然开朗的新阶段。由于孔圣思想中倡导符合纲常伦理的端然之乐,因此“乐者,正也”的跟进意识是审美逻辑自洽的!这让笔者本文的标题——与世间的君子(有知识修养,懂音乐艺术)相惜、与人间的大众(尊知识教养,爱音乐艺术)同行、塑造具有传统古典继承性和当代审美意识有效性的艺术人生观,仿佛就有了可展望的本真愿景。在前文已罗列记述的对孔圣相关审美印象的基础上,再如果说,孔子所遵循的礼乐之道拥有着“礼”是一种“养”的审美内涵的话,那么礼乐的意象本质在笔者看来则是——在孔圣“忠恕”意象核心前提下的一种主体间性的“养正之气”!这一理解中的孔子思想意象之艺术人生观,应该说是笔者在长期精读叶朗先生《中国美学史大纲》[6]的过程及基础之上,获得的可喜增量。
注释:
[1]有关“忠恕”的解析义涵是笔者参照了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的观点,“此一贯原则便是仁,亦即忠恕”。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上),中华书局,2017年第1版,第12页。
[2]古代先贤让“美”范畴获得独立意义的理解是笔者参照了张前主编的《音乐美学教程》中的观点,“明确区分了美、善,肯定了美的独立意义”。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4页。
[3]这是康德审美价值标准在审美判断力建立过程中的重点命题之一。
[4]李泽厚先生的治学在其不断的反思能动形成了哲思观念上的时期化调整,在涉及社会学意识的审美批判思维中具有一定的合理言说的逻辑强力。
[5]具体的艺术事件情状可见蔡邕《琴操》中记载孔子创制《猗兰操》的经典书写。
[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武文华 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
兼职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