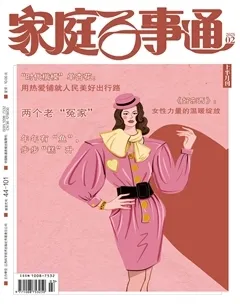年年有“鱼”,步步“糕”升

儿时的记忆里,有一道菜,每年都会准时出现在年夜饭的餐桌上。它形似豆腐,方方正正,但因其四周镶嵌着一道金边,又比豆腐好看,它还比豆腐好吃,清香滑嫩,入口即溶。
20世纪90年代,农村的物质生活还不算宽裕,这道被年幼的我称为“豆腐”的菜肴,并不是饭桌上的家常菜,只在过年时才吃得到。因此,吃“豆腐”成了我对过年最大的期盼。
后来我年龄大了些,才知道这道菜叫“鱼糕”。初次闻其名,我颇为震惊。按理说,凡带“糕”字的,大多为桂花糕、绿豆糕、云片糕之类的甜点小食,实在不明白为何一道菜也叫“糕”。
直到又一年的年夜饭上,爷爷频频给我们几个晚辈夹菜,慈爱地说:“孙儿们,多吃鱼糕,年年有余,步步高升哩!”我恍然大悟,原来“鱼糕”谐音为“余高”,这朴素的菜名中,蕴含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祈愿。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腊月做鱼糕。原材料优选野生青鱼和草鱼,用它们制成的鱼糕软绵中又带着韧性,让人回味无穷。我的家乡湖北,有“千湖之省”的美誉,湖泊星罗棋布,淡水资源丰富,盛产野生青鱼及草鱼,具有制作鱼糕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我们当地人把做鱼糕称为“打鱼糕”。将买回来的活鱼,去除鳞、头、尾、鳍和内脏,一刀刀刮下鱼肉而不留鱼刺,再切成小片,放到清水里漂洗到无油。
然后是剁鱼糜。这是个力气活儿,父亲是我们家的“掌刀人”。他操着刀,在案板上施展“功夫”。只见他双刀飞舞,案板上发出“噔噔噔”的声音,时而急促,时而缓慢。不一会儿,片状的鱼肉开始逐渐萎缩下去,变成越来越小的丁状,又变成更小的粒状。父亲时不时停下刀,加入一些肥膘和葱姜末后,再奏响他的“剁肉进行曲”。就这样不停地剁上数小时,直至肉糜均匀细腻。
剁好的鱼糜被放入一个搪瓷缸里,母亲掺入适量淀粉、鸡蛋清、精盐和味精搅拌均匀后,再把鱼糜平铺在蒸屉里用旺火清蒸。不用多久,一股香味从蒸笼里溢出来,像鱼香,又像肉香,让人馋得不行。
大约半小时后,母亲揭开蒸笼。“熟了吗?可以吃了吗?”我迫不及待凑上去。母亲笑道:“还没有,还需要‘画龙点睛’哩!”原来,在鱼糕蒸至七八分熟时,要在表面抹上一层蛋黄液,又以食用红色素作为点缀,再蒸五分钟,才算大功告成。
母亲像切蛋糕一样,把出笼冷却后的鱼糕先切成条状,再从条状切成片状。这样,一块块形似豆腐的鱼糕就可以食用了,肉有鱼香,鱼有肉香,回味悠长。
如今,在我们荆州一带,逢年过节、喜庆宴会,鱼糕早已成为宴请宾客必有的一道硬菜,并有“无酒不成宴,无糕不成席”的说法。清蒸鱼糕、鱼三鲜锅、鱼糕滑炒时蔬等,老百姓创造出许多关于鱼糕的新吃法、新花样。这道家乡菜,演化为人们体现喜庆、表达美好祝愿的重要元素和载体,是荆州八大菜肴之首,更被列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一种味道,它贯穿一生,连同记忆里劳作的身影、四周的空气,以及土壤与草木的呼吸,形成一种微妙的感觉,中国人把它称为“家乡味”。家乡的食物中,有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还有时间和人情的味道。这些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头。让人几乎分不清哪一种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对我而言,鱼糕就有这样的味道。
编辑|龙轲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