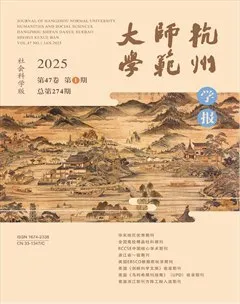洪深早期话剧《虹》中的士绅、家国与救亡
摘 要:洪深留美期间以英语创作的《虹》是其早期话剧尝试之作,具有新旧过渡的特征。全剧围绕山东一个士绅家庭与战争的关系展开,集中呈现了“一战”大历史中中国人的世变遭遇、赴欧牺牲及其纠缠的思想和情感反应。在《虹》的家庭故事和绅民关系背后,隐含了由家国伦理向现代政治、由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转换的思想难题。
关键词:洪深;《虹》;“一战”;士绅 ;救亡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5)01-0062-06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5.01.006
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用较长的篇幅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所造成的危机,以及在此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逻辑。洪深将现代话剧的开端设置为“一战”爆发,这种叙述不但明确地强调现代话剧与传统旧戏之间的断裂,而且也力图撇清与文明新戏之间的联系。洪深强调话剧与以上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写实主义,即戏剧要描写和表现人生、富于时代性,“戏剧家负有重大的使命,就是将他观察与阅历人生的结果,采取有意义、有关系的一片段,编成一节有趣味的故事,用日常人生的动作,(不外乎衣食住)搬演出来,使观众看时受重大的刺激,欣然愉快,过后留有刻深的印象,幽然深思”[1](《导言》,PP.65-66)。在回溯“戏剧的人生”时,洪深提到了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创作,他曾创作多部英语话剧,其中至少两部与“一战”有关,一部是讲述“一战”火线后情形的独幕剧《回去》( The Return ,1918),另外一部是《虹》( Rainbow ,《虹》又译《东方明兮/东方明矣》,1919)。洪深后来曾多次讲起《虹》,且立意颇高,可见这部剧在洪深的话剧道路上具有重要的起始意义。作为洪深早期话剧的尝试之作,《虹》已经具有了以上洪深所说的“使命”和内涵,但是又不尽符合新文学的变革性要求,在话语、情节模式和人物设置上具有诸多新旧过渡的特征,与《导言》中求“新”的叙述不尽一致,该剧以家国传统为内核的文化主体精神在跨国传播语境中反倒获得了有益的凸显。
一、本事、异文以及“失地”经验
在《戏剧的人生》中,洪深是这样介绍《虹》的:
欧战的第三年,美国加入了英法方面;美总统数次宣言,态度忠诚,理想远大;什么“民族自决”,什么“废除秘密外交”,什么“议和不必有战胜者”,什么“为了永久消灭战争而战争”,什么“必使民主主义在世界上安全”!我辈青年人,热怀着多少希望,发生过多少幻想!我虽不曾正式的充当兵役,但很起劲地受了军事训练;也穿过士兵的衣服,当过工程队员,在戴登地方,帮着测量过军用飞机场。到了一九一八年,大战停止了;次年巴黎和会,竟议将青岛及胶济铁路等划给日本。全中国的人,都愤慨极了。我写了一部三幕英文剧, Rainbow ,中文名《虹》;这是我的抗议。
……
这出戏里所叙的事实,没有一件无根据,没有一件无来历;明显地是对美国人的一种宣传,一种抨击。那年美国各地中国学生会采用这个剧本上演的很多,但在美国人看了,自然是不十分痛快的。[2](PP.16-18)
该剧英语全本未见存世,其情节略记最早以《东方明兮》为名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1920年春季第1号上。全剧围绕山东一个士绅家庭与战争的关系展开,集中呈现了“一战”大历史中中国人的世变遭遇、赴欧牺牲及其纠缠的思想和情感反应。依照《留美学生季报》的情节略记,该剧以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设置了三个场景:第一幕(1917年夏)发生于美国对德宣战之后,居住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某城的刘姓老翁(刘绅)目睹日兵“所过皆扰”,劝慰愤怒的百姓“以忍耐待时为戒”,其子“刘公子”经老翁同意作为华工队长赴法,亲戚高公子(复仁)同行;第二幕(1918年冬),此时欧战已停,和议未开,刘家欣喜地备办了酒席准备迎接刘、高两位自欧洲返乡,却意外得到刘公子战死的噩耗,喜事变丧事的情节急转也为下一幕中国人对巴黎和会由希望而绝望的转换构成铺垫;第三幕(1919年夏),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国人出现或悲观或反动的“危险心理”,周围民众“因华工伤亡之多,及日人凌虐之痛,愤激思报,转恨刘绅”,聚众闹事,欲焚其屋,置身此种境地,刘绅却展现出英雄式的清醒判断和孤绝勇气(“有英雄无所谓悲剧”)。[3](PP.209-215)从传播和接受语境来看,该戏剧主要是面向在美中国留学生和美国民众演出,具有特定的教化(对留学生)和宣传(对美国人)功能。
据洪深所述,他于1919年夏天开始创作此剧,当年9月5日、6日即在美国中西部地区中国学生联盟第十届年会正式公演,洪深自己担任男主角[4](P.63);这部剧的创作时间非常短,但是演出效果相当不错,“寻常编剧、最少须六个月,此剧在六星期内编成,故多有未妥之处,开演之夕,幸未失败。则因一切演剧办事人,肯吃苦、肯牺牲,一片血诚,故能感动人也”[3](P.215)。10月10日由美国中国留学生会在爱荷华大学演出,观众超过八百人。[4](P.65)全剧“本于事实”,材料是根据上海《时报》、北京《顺天时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美国《新共和杂志》《国是杂志》,及在华传教士之通信与他种日报杂志等。[3](P.215)如其所说“戏里所叙的事实,没有一件无根据,没有一件无来历”,可以看出洪深创作该剧经由时事报刊所获得的“本事”,未尝不是一种叙述形式,在被认为是“事实”的叙述与戏剧文本之间存在着饶有意味的“间性”关系。洪深通过一个华工家庭串联欧战、威尔逊主义及巴黎和会所引发的风波,并不一定是时事报刊所给定的叙述逻辑,或者说,作为戏剧叙述的故事使家庭和个体在战争中被放大,从而凸显了生命、情感和思想的维度。
围绕家庭来讲故事,原本是文明新戏惯常的做法,在这部戏中洪深是把家庭戏和时政内容做了很好的结合,以家庭来呈现时事。当然,洪深在剧中对家庭人物的设置,究竟多大程度上突破了文明新戏的世俗性和市民趣味,进而抵近“人的文学”,也是一个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由于英文剧本的缺失,我们无法从语言现代性的角度来准确把握该剧的“新质”,而从情节略记所提供的基础框架来看,《虹》中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仍具有浓重的旧式言情的味道,因此与那种倾向于展现人的内面性的新文学似乎还是有不小的距离。在作为《五奎桥》序言的《戏剧的人生》中,洪深对《虹》的情节复述稍有偏差,他将赴欧参战的两个年轻人记成了山东某县某读书人家的“两个儿子”,而且都在欧洲战死了。这些构成了1919年版情节略记的异文,在洪深的回溯性观照之下,《虹》的政治功能更加凸显,而原来传奇和言情的风格则有所减弱,或许对于洪深而言,角色的细分可能仅仅是服务于戏剧的趣味性考量,相对于戏剧的政治功能来说仍然是属于第二位的要求。
在作为政治事件的“事实”之外,洪深还有着深切的个体经验隐伏在这部戏剧的后面,除了《戏剧的人生》中提到的在美参与军事训练的经历,他在留学期间应该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战争以及“山东问题”的信息。洪深和晏阳初、林语堂、傅葆琛、傅若愚、陆士寅、全绍文等赴欧进行华工教育的留学生一样,都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尽管他没有去欧洲战场,但是基督教青年会内部应该有相关的信息网络使其详细了解华工招募和工作的情况,而他提到的“在华传教士通信”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当时在华传教士广泛参与了华工的招募,对华工来源、家庭状况都有颇为具体的了解。“一战”期间英法招募了大约14万华工到欧洲西线战场从事战地后勤工作,这些华工中的大部分是从山东特别是在胶济铁路沿线招募的。剧中情节如刘公子参加航空队、亲戚朋友携手同行赴欧等,大都有现实原型,非向壁虚造。
而另外一个隐匿的经验背景,则是洪深曾居青岛的经历和“失地”的经验。洪深曾说,“我每次到青岛,也许我是太以‘生的门得而’(笔者注:sentimental)罢,总得设法到南九水去探视一次。去时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多;我轻易不敢对人家说,我才是这屋的真正主人;人家也不晓得我还有这样一块‘失地’”[5]。1913年,洪深的父亲洪述祖因涉宋教仁案离京来青岛避难,不久即在崂山的南九水修建了名为“观川台”的洪家别墅,洪深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常来南九水度假,经历了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后,征用了洪家别墅,这段“失地”经验后来也出现在了洪深创作的电影《劫后桃花》 洪深创作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发表于《文学》第2卷第1、2期,同名电影于1935年底制作完成并上映。电影中的花园别墅事件与洪深的家庭经历非常相似,这个故事将国家的屈辱历史透过一个家庭的劫难来呈现,其间穿插言情与传奇,具有鲜明的洪氏戏剧风格。中。对于洪深来说,“失地”首先关联的是“失家”,与其跌宕飘零的身世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使得他对时局的变动有着更为痛彻的体验。贯通来看,作为《五奎桥》序言的《戏剧的人生》在欲说还休之间显露出“失地”与“国耻”“家恨”情感缠绕的草蛇灰线,这或许就是隐匿在洪深话剧创作背后具有原型意义的“心结”——一种切身而浓烈的家国情怀。
1919年4月5日,洪述祖被处绞刑,刑前洪述祖留遗嘱要求归葬原籍五奎桥茔地,并转告洪深不必因此废学。受此家庭变故的影响,洪深放弃实业救国的思想而改习戏剧,决心以戏剧为武器唤醒民众,“第一,我这一辈子决不做官;第二,我决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了基础的”[6](P.11)。春季学期结束后,洪深即决定中止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化学陶瓷专业,转学报考哈佛大学“英文47”(戏剧编撰),按照报考要求,洪深给哈佛大学投寄了自己创作的三幕英文剧 The Wedded Husband (《为之有室》)和英文独幕剧 The Return (《回去》)。此间国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当时似乎并没有给青年洪深留下太多的印记,到了1919年夏天,他就开始创作《虹》——这可以看作另一个版本的“五四”,它们共同指向“一战”所引发的主权危机,但是对于洪深来说,他可能更关注刘绅这样的思想道德精英对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应,而不完全是走上街头的民众,这显示了其与庶民政治潮流的疏远,甚至呈现出一定的保守性。1933年,带有独特家庭印记的“五奎桥”成为洪深代表性剧作的名字,在《虹》中即暴露出来的绅民矛盾在他的剧作中被进一步放大。
戏剧中所呈现的家庭既是故事展开的场域,也是一个稳定的伦理—情感发生装置,在这个家庭中,家长(刘绅)与子辈(刘公子、女儿和儿媳)之间有着和顺孝亲的关系,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民族大义与家庭伦理之间又产生了同构性连接,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现代版本的毁家纾难的故事。家庭虽然并不等同于家族,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嵌置在宗法伦理中的基础构造,显然我们还不能简单用今天核心家庭的概念或者西方观念中作为“自然现象”的家庭来理解这一文明性的对象。回到一百多年前伦理革命的时代,尽管家族制度已风雨飘摇,但仍在现实实践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文化能量。在《远东评论》的一篇报道中,作者根据经验观察,特别强调了华工中“尊敬老人和爱家庭的尤其占极大多数”,华工应募出洋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家庭考量,英国人则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工资拨付制度(即将大约一半的工资汇给华工家庭)实现了华工招募的极大成功。[7]尽管一般华工在出洋前并不一定能够具有清晰的国家意识,但是华工所抱持的孝亲、顾家的观念却在无形中构成了战时国家动员的重要发生基础,这就是具有原型意义的家国一体的深层文化传统,能够构成原型的经验或传统,往往是塑造戏剧模式的最深层的心理动力,这也决定了洪深戏剧回应战争、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基本方式。
二、古今接续与士绅救亡
值得注意的是,洪深在《戏剧的人生》中并没有突出《虹》的主人公刘绅的士绅身份,而将其“误记”成“读书人”,但是在1920年版的情节略记中则明确指出刘绅“曾任民政部尚书”。“民政部尚书”是晚清政改的产物,官从一品,因此在早先的版本中刘绅这个角色应该是有功名的乡绅,即由“官”而“绅”,显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洪深在剧中亲自扮演刘绅,可见这个人物是他特别用心塑造的角色,某种意义上也是洪深假托的思想载体。戏剧的风格、趣味与作者、演职员以及接受者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相关记载,洪深在美剧作的演出者“大部分由中国政府派往这里。所有学生在美国学校学习五年后将返回中国。其中几个在化工系、采矿系和艺术系注册的学生,多数来自政府要人家庭,或是军政官员或名人的儿子”[4](P.68)。在这样的演出和传播环境中,戏剧故事的表达会受到某种阶层认知和思想层次的规定。洪深先祖为洪亮吉,尽管洪家到洪述祖这一辈已经基本没落,但是洪述祖毕竟曾出任袁世凯的高级幕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洪深多少也会有一些世家大族的情结。在剧中,刘绅作为前“民政部尚书”,一方面在面对民众时保持了道德精英的色彩,另一方面又与政界人士密切往来且有政见交锋,这种角色的阶层身份显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甚至不排除有思想界的原型根据。
写出《戏剧的人生》的1930年代,正是文化界普遍向左转的重要时期,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丁玲的《水》、王统照的《山雨》都是反映这种转变的文学创作,此时的洪深也推出了以《五奎桥》为代表的“农村三部曲”。在《五奎桥》《香稻米》中,绅民关系所反映的阶级矛盾急剧恶化,土豪劣绅已然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剥削压榨乡民的反动阶级的组成部分。但洪深在《戏剧的人生》中看似无意的改写使得作为异文的《虹》避开了与《五奎桥》中相似的绅民矛盾,而只是保留和强化了民族矛盾及主权危机。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戏剧的人生》却没有按照时代观念的规定“后设”地强调《虹》中也具有相近的冲突呢?或许与《青龙潭》有些类似,这种欲说还休、言犹未尽的叙述方式可能延续了洪深对于士绅群体矛盾的态度。
救亡危机是贯穿《虹》全剧的主题,也是刘绅面对的现实难题。戏剧开场所展现的胶济铁路、日兵骚扰以及国人纷乱的背景,都指向了“一战”所引发的救亡危机,刘绅派自己的儿子作为华工队长奔赴欧洲战场是回应这一危机所做的家庭牺牲;他一改中立立场、极力宣传对德宣战则是回应这一危机的政治决断。反观周围,“其时国人心理纷乱已极”,“大多数莫知所措,惟素敬刘公正直公平,虑远知大,将视刘公之趋向而定和战”[3](P.210)。在民智未开的背景下,刘绅对周围的民众还残留着士人精英所特有的政治公信力,能够纵横决断、引导舆论,民众也曾经目睹刘绅一家所作的牺牲,“集资造匾,以音乐爆竹送呈刘宅”表达对刘绅的爱戴。然而到了《虹》的第三幕,民众却“因华工伤亡之多,及日人凌虐之痛,愤激思报,遂转恨刘绅,责其故愚国人,对德宣战”[3](P.214)。刘绅与民众关系恶化甚至对立的根源似乎在于刘绅主张对德宣战,民众以为刘绅和那些政客一样在欺骗和愚弄大家,才导致危局的出现。其实刘绅所主张的对德宣战并不是山东主权丧失的原因,与民众的判断恰恰相反,对德宣战正是解决主权危机的努力。如果没有对德宣战,山东问题甚至可能进不了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也不是因为战胜了德国,而是中国虽名为战胜国却无法在和会声张利权,最后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的抗争具有正当性,然而迁怒刘绅则又表现出斗争的盲目性。这个情节隐含着复杂的政治意味,回到“一战”的具体舆论空间,主张对德宣战却被指责卖国,是曾经的确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因为对德宣战主要是段祺瑞势力的主张,参战问题不但引起了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的闹剧,而且更受到南方阵营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不过是军阀扩张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游走政学两界的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因为支持北京当局对德宣战一度面临南方阵营追讨,研究系重要成员汤化龙更是遭遇暗杀喋血加拿大维多利亚街头。战后主权危机激化虽然与战中状况不尽一致,但是政党纷争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民众的判断仍会被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攻讦的纷乱舆论裹挟,这恐怕才是戏剧所依托的真实的政治语境,也是戏剧借以展开思想论辩的场域。“一战”背景下的刘绅尚不属于土豪劣绅,他既为官绅,又为学绅。从家庭方面来看,刘绅似乎仍然残留着宗族权威的一些传统做派,但从战事前后的几场辩论来看,我们又可将其视为从士绅中分离出来的具有一定世界眼光和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这个人物有着新旧混合、古今接续的特征。
刘绅不惜“牺牲自己之地位及前程,牺牲爱子,牺牲友谊,所为何事?曰‘民治主义战胜,中国或可不亡于日本耳’”[3](P.211)。由此可以看出来,刘绅关于战与和的判断并非完全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而是笃信“民治主义战胜”,这也是他接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参战主张的重要思想原则。戏剧中所展现的反差和矛盾可能正是面向美国观众所追求的戏剧效果:刘绅不过是个替罪羊,刘绅之罪在于替威尔逊背书,这其实是将批评指向了言而无信的威尔逊。在乱世危局中,刘绅不但要面对政客名流各种版本的“速亡论”,而且还要面对民众盲目的集体暴力,自己也从笃信威尔逊“民治主义战胜”,最终堕入到巴黎和会的大失望中,使得这出剧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层次,且因其悲剧性而强化了政治批判性。面对“居民数千人,破门而入,且有纵火焚屋之号”,刘绅没有逃跑,也没有接受高公子递过的手枪进行自卫,而是坚信“天理人心”,并选择走向民众进行“说理”。依从“天理人心”来确立道德实践的行为方式,明确地体现了刘绅所秉持的士人精神传统,这既是塑造刘绅人格品质与精英主义式的德性伦理的根源,也是制约其现实政治能力的传统界限。在儒家传统中,天理是世界观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经过宋明理学不断在主体实践的层面进行理与心的辩证,这构成了中国人德性政治的核心。借由“天理人心”来面向民众“说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固然仍有实践的可能,但是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与国际秩序大变动,尤其是救亡的难题,刘绅所代表的士绅阶层必然面临着主体再造与实践方式(国民运动)的巨大挑战,置身历史的关口,不免歧路重重。汪晖认为:“作为一个道德/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天理构成了‘前西方’时代中国的道德实践、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概念,而以此为核心的世界观的解体意味着在漫长时代里形成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及其认同感正面临危机;作为这一解体的结果的公理/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标志着原有的认同形态已经难以为继。”[8](P.47)刘绅所遭遇的士绅救亡难题从根本上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旧的德性政治范式的危机和认同断裂,在《虹》的家庭故事和绅民关系背后,隐含了由家国伦理向现代政治、由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转换过程中的思想难题。
罗志田用“权势转移”来把握近代以来士绅文化权力的变化,他将变化回溯至1905年晚清废除科举制度对传统“由教及政”观念的巨大冲击。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身为楷模的士人观念对追随的大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世人推崇的“知识”对老百姓未必很实用,却得到他们的承认,因而也具有影响力。[9](P.96)从中国社会的基层来看,士绅权力不是简单的依附性政治权力,而且还具有深厚的政教传统,而近代以来绅民矛盾恶化的根源既包括士绅阶层的分化(土豪劣绅化),也包括民众教化渠道的断绝,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被视为阻碍个体解放的牢笼,传统共同体的根基受到极大动摇,传统士绅与民众所共享的政教伦理由此逐渐崩解。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中,陈独秀所指的“政治觉悟”就是要民众放弃“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幻想,而追求“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伦理觉悟即是以自由平等独立的现代主体原则反对传统的名教纲常秩序,并将其代表的东西文化冲突视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激烈程度不亚于现实中发生的大战争。[10](P.2)但是随着“一战”战事的推进,对战争的反思也愈发深入,近代以来由竞争进化论所主导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思想界的广泛质疑,有学者甚至将军国主义和战争观的根源追溯到了尼采的哲学,认为“权力意志”极易走向民主的反面,并且成为强权逻辑和各民族间不平等的辩护理据。剧中绅民关系的恶化与威尔逊主义的破产预示了自由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的巨大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即使不再笃信传统的天理世界观,也不能完全信服强权胁迫之下的公理可以重建天下秩序。
在新文化运动庶民化政治转向的巨大洪流中,具有本土特征的天理和作为新的合法性原则的公理这两种话语处在紧张、不稳定的竞争关系之中,天理世界观并没有完全退场,传统的德性伦理借助东西文化论争、科玄论战又进入到新的群己公私的国民政治建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讲他在欧洲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
的老师普陀罗、社会党人士交流的体会,说欧洲人战后相当推崇中国的思想文化,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兼爱非攻,可以作为新的天下关怀,开出“文明新境界”。《新青年》群体尽管主张反传统,但是高一涵等人在主张个体解放的同时也强调自我的利他性,试图以此建立具有责任感的群己关系,通过伦理自觉而摈弃政党政治、启发更高层次的政治自觉。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新儒家则认为儒家传统中本来就存在着构建现代群己关系的可能;陈嘉异则更强调国家的伦理之维,认为国家非单纯的政治组织,而实为社会组织。在这里“国”中有“家”,“家”中有“国”,由修齐治平的立身实践联通“世界的国家”和“社会的国家”,其本在于各个人之一身。[11]这种由古代的君子和士人转化而来的新的国民主体带有强烈的伦理特征,它一方面坚守儒家伦理中个人的尊严与自主性,反对国家和集体对于个体的过度压制;另一方面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责任,其展开方式完全不同于扩张的个人主义。
三、余论:跨国语境与文化自觉
一百多年前,置身“一战”所引发的国际大变局,洪深通过《虹》这出戏直面国际观众,艺术性地呈现、回应了中国人所遭遇的政治和伦理难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高度紧张性的思想及文明议题。在中美之间不平衡的文化关系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双重坐标系之下,洪深这部剧不但要追溯国家危机的根源,而且还要回答中国人如何才能自救的根本挑战。刘绅的遭遇,实际上隐喻了中国面临的政权失能、基层失序和国际霸凌的极端危机处境,刘绅的反应也悖论性地显示,在新文化还没有充分发育的时候,传统文化仍然承担着对话传播的功能,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对话、反向“说理”的路径,与新文化运动中占据话语主流的公理论说在逻辑起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它更接近“东方文化派”的思想方式,可视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洪深这部海外剧作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个难得的思想标本,这也让我们看到早期话剧在复杂的国际语境中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独特回应形式。刘绅对战争以及威尔逊主义的认知转变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体现了更深层次的危机判断和文明性思考,主人公最后所言“有英雄无所谓悲剧(To the hero there is no tragedy)”[3](P.215)显露的不仅仅是孤勇者的德性光芒,更重要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精神和文明韧性,我们也看到,在中国20世纪民族解放、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这种文化精神没有随着一个阶层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而是潜化为现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传统;这种文明韧性也体现为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文化机制——一种极力在现代个体、家庭和国家政治之间达成同构和统合的新“家国主义”。该剧英文剧名为 Rainbow ,译作“虹”,“取意虹见则风雨已过,不久必可天青日白”[4](P.59),另一中文译名“东方明兮(矣)”则出自《诗经·国风·鸡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两个译名都寄寓了“中国不亡”的历史理性和文化自信。戏剧在一个由刘绅面向民众“说理”所构造的开放性场景中结束,这似乎又暗示了刘绅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与民众重新结合的可能,以及新的国民救亡运动的到来。
参考文献:
[1] 赵家璧主编、洪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2] 洪深:《戏剧的人生(代序)》,《五奎桥》,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
[3] 洪深:《东方明兮》,《留美学生季报》,1920年春季第1号。
[4] 洪钤:《中国话剧电影先驱洪深:历世编年纪》,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
[5] 洪深:《我的“失地”》,《太白》,1934年第4期。
[6] 陈美英编著:《洪深年谱(1894—1955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
[7] E. Manico Gull.“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r Corps:A Highly Efficient British Organization to Protect the Personal and Financial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Coolies Laboring Behind the Lines in France.” The Far Eastern Review , Vol.XIV, 1918.
[8]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9] 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第6号。
[11]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1921年第1-2号。
The Gentry, Family-State and Salvation in Hong Shen’s Early Drama "Rainbow
YANG Weij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Hong Shen’s "Rainbow , created in English during his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his early attempt at drama, characterized by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old period and the new one. The whole play revolves a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gentry family in Shandong and the war, and focuses on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such as the experience of world change, sacrifice in Europe and entanglement. Behind the family st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try and the people in "Rainbow , there are hidden ideological challeng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amily-state ethics to modern politics, and from traditional gentry to modern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Hong Shen; "Rainbow ; the Great War; gentry; salvation
(责任编辑:蒋金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