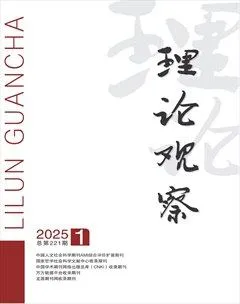“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现代创生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作为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精神财富。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有其生成与演进脉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有助于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功能。如今,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面临传承载体的缺位、传承主体的涣散以及传承情感的淡化等时代挑战。因此,有必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提供物质保障;重塑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文化滋养;强化“亲亲”思想和爱国教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支撑;拓展家国同构和“大同”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柱。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现代创生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25)01—0005—05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1]“第二个结合”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激发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新创造精神。但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仅被视为社会文化的附属示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3]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明晰时代挑战与传承难题,推进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
一、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生成与演进脉络
《说文解字》关于家的解读是“家,居也。从宀,豭省声。”从家字的结构来看,它的上半部分从宀,代表着房屋的结构,下半部分从豕,代表家人聚居的地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既是具体的物理空间,象征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又是情感依托的空间,代表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从文化生成和赓续的内在机制来看,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生成和丰富经历了以下演进过程。
(一)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脱胎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祖先崇拜
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聚居在一起,在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从图腾崇拜转向祖先崇拜。氏族内的人信奉自己的祖先是部落的守护神。人们逐渐建立祖庙,形成祭祀传统,表示伦理意义上对祖先的敬畏与感激。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家的整体性逐渐明确化、固定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关系越来越密切,祖先崇拜演变为家庭崇拜,传统家文化伴随着氏族的传承和延续而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伏羲氏、炎帝、黄帝等被我们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可以说,传统家文化在诞生之初就集祖先崇拜、家庭崇拜和宗教崇拜于一体,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二)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丰富于天道向人道的转变阶段
在古代社会,人们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对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做神学化的解释,认为万事万物都以天道秩序为法则。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尤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主体的形成,使得人们拥有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合力,逐渐形成突显人的主体性力量的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分工合作,使得家庭不再仅仅是血脉连接和情感交互的场所,它同时为社会关系的转变和发展提供空间。正如脱胎于氏族社会的奴隶社会形成了维护其私有财产的宗法制,古代社会结构和制度也被打上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家文化烙印。
(三)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拓展于家国同构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的一种扩大化,家国一体的思想贯穿于传统家文化当中。孟子在《离娄章句上·第二十七节》中将孔子在《论语·学而篇》的孝道扩演为国家治理之道,即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4]发展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5]周代殷祀之后,周人将人君的地位上升为天子,以功德为标准的祭祀让位于以血统为标准的祭祀。天子在祭祀祖先时开始祈祷国家稳定和社会繁荣。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家文化理念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
二、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
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是个体成长的摇篮和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有助于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功能。
(一)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和家庭结构在观念上的反映
古代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游牧经济为辅,逐渐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进而形成了重视集体利益的传统家文化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6]。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以封建大家族势力为依托,家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治权力的传承、官员的选任都是家族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形成了强调“家国同构”“天下一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家文化特征。这种结构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关系,也对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和交往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二)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是推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化延续的重要因素
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特质,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纳入中国传统社会整体结构中,才会发现其独特的价值功能。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促进了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7]传统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和品德教化,规定了人们在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和礼仪秩序,强调成员之间的合作与诚信,为经济活动的发展、政治活动的运行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在维系中华文化的连续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文学、诗歌、绘画等艺术往往是代代相传的家族遗产。家族中的智者借助家文化媒介将文学艺术的精髓传递给后代。这种非专门化的文化传承使得家庭成为文学艺术延续的重要载体,也在家族中培养了一代代的文化艺术传承者。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希望。
三、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时代挑战与传承难题
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嬗变历经了从封建社会“礼教等级的家”解体,到战争年代“革命队伍的家”兴起,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转变为“经济依靠与精神寄托的家”。[8]目前,宗法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作为传统社会价值链中的公私纽带遭到冲击。个人与家庭、家庭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失去了原有的缓冲地带。这不仅遮蔽了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价值功能,也给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当代传承带来了三大时代挑战。
(一)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传承载体的缺位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传承载体正在逐渐消失。家谱记录着家族的起源、世系和重大事件,村志记载了村庄的历史、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特有的人文信仰,祠堂是家族祭祀和文化传承的场所,它们是传统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传统的乡土世界逐步城市化,这些传承载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意义。许多村庄和家庭不再重视村志和家谱的编纂,许多祠堂面临维护困境。如今,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看似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但却筑起了人与人心灵之间的藩篱。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传承载体不足导致其在家庭教育中以文铸魂的教育功能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传承主体的涣散
在中国传统大家庭结构中,族中耆老在家庭中具有天然的权威地位,履行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责任。族长作为乡土世界的代理人,对乡村的治理和地区的稳定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宗老们陆续离世,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结逐渐变得松散,传承主体也慢慢退位。伴随着大家长乡村话语权的弱化,其在家庭内的权威也不断受到挑战,使得积淀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不断遭到质疑。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传统大家长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与基层治理有机融合,如何在新时代家文化传承中建构起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合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传承情感的淡化
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使传统家庭生产方式逐渐式微,家庭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市场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扩大了社会分工,人们更多地从事专业化的工作而不是传统的家庭生产。这种专业化生产模式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削弱了家庭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性。市场经济的崛起使消费主义有所抬头,人们更加关注物质享受,而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方面缺少足够的意愿、情感和行动自觉。此外,西方错误思潮借改革之机渗透国内,封建腐朽思想打着传统文化旗号企图卷土重来,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不断受到侵蚀。受利己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等观念影响,家庭道德观念淡化、社会道德行为失范、意识形态信仰危机等问题日益严峻,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面临失去原有的情感认同和影响力的困境。
四、“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现代创生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9]。将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底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养料和价值支撑。
(一)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提供物质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型,在物的丰富性基础之上构建起自身内容的丰富性。
其一,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必要条件。传统家文化虽然源自于私有制家庭,但在历经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漫长发展中积淀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和弘扬作为上层建筑的优秀传统家文化,必须要筑牢涵养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传统家文化的传播创设充足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和修复古文物与古建筑、古籍家谱等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技术革新,它可以为传统家文化传播提供更多的物质载体。例如,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将传统家文化资源数字化,使其更加便于普及和推广。此外,生产力的进步可以促进人的解放,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现代创生工作中,进而锻造出一支符合传统文化现代传承要求的人才队伍。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这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也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中。
其二,完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必然要求。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关系到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化,还牵涉到对传统优秀价值观的传承。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过程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增殖过程。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仅没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反而带来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只有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使人成为生产的主体和价值实现的对象,让每个人共享发展的果实。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只有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弘扬。
(二)重塑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文化滋养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10]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借助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合理内核为养分,强化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一方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理论创生,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重要思想资源。首先,创新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中家祠家学家规家训,是培养公民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要善用符合时代要求的家文化知识和立足于历史发展趋势的家文化观念,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发挥广大青年挺膺担当的作用,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其次,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中的家庭美德,是培养公民高尚品格和良好公德的优选手段。传统家文化强调人们在家庭中相互关爱,在社会中遵纪守法。要吸收其中独特见解和人生智慧,培养具有同理心、善良心和悲悯心的公民。最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中家教家风,是培养公民道德实践和文明践履的关键抓手。要利用好家教家风的熏陶功能,发挥好家庭模范的榜样作用,帮助家庭成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社会发展提供道德引领。
另一方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实践创生,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多元途径。要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家文化资源馆,突破传统家文化载体的时空局限性。这不仅为个体提供了更加灵活、便捷的文化体验方式,也为人民提供了更加开放互动的学习平台。此外,要将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融入到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全过程,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11]要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责任,可以通过设置校本课程、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等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融入到教学实践的具体环节中。政府可以通过制订政策法规、提供经费支持等方式,开展多样的传统家文化教育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把公民塑造为具有良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勇于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三)强化“亲亲”思想和爱国教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中强调的“亲亲”思想和爱国教育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助推剂。
“亲亲”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亲亲”既是长辈对晚辈的伦理原则,也是与自我相关联的亲属之间的亲情关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是家庭的延伸和扩展。要不断创新传统家文化传承载体,通过修撰家谱、编纂村志等集体活动宣传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进一步提升家庭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定期举办宗亲会、寻根问祖研究会,把个体生存与他人发展联系起来,把“亲亲”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置于整个社会层面,形成和睦的民族氛围。在西方哲学中,个体通常被强调为独立的、原子化的主体,而忽视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和责任。这种思想容易导致个体主义的盛行,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矛盾。“亲亲”思想对于消解西方“他者”哲学带来的个体之间的对立和争斗,弥补“个体-主体”哲学的欠缺而导致的孤独和虚无,帮助现代人“归家”具有重要意义。
爱国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3]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中的“孝”超越了家庭的界限,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这种强调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国家繁荣复兴的目标联系起来,把家庭中的“小爱”扩展为国家中的“大爱”的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中华儿女的血脉基因。文化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载体,电影、广播、书籍等传统媒体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宣传作用。例如,影片《流浪地球》展现了独属于中国人的“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而《满江红》则激起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拳拳之心。要继续深入挖掘传统家文化中的爱国元素,借助间接的隐性的教育方式对民众进行思想引导和爱国熏陶,让每一个个体自觉地将自己的利益融入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中,进而增强人与人之间联结的粘性,形成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拓展家国同构和“大同”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柱
“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是地缘与血缘管理的交叉融合,直至后来形成了‘家国同构’‘家国天下’的政治特色和心理结构。”[1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人类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
一方面,家国同构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对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是家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更进一步地突出了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联,强调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共赢,体现了一种更加宏大的家国同构思想。当今世界,民族宗教冲突、地缘政治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频发,归根到底还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世界需要中国方案,人类需要中国智慧。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实践,为破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提供了新思路,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新时代新征程,要进一步建构国际合作新模式和全球对话协商新平台,赓续中华民族秉持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美好理念,增强“家—国—天下”大和谐观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大同”思想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在现代社会中,“大同”思想可以被重释为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共处、互惠共赢的价值理念,它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诉求。其一,弘扬“大同”思想中的和谐共处理念。“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各国之间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共建和谐地球村。其二,弘扬“大同”思想中的永续发展理念。当前,全球性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共担责任,共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三,弘扬“大同”思想中的“和合”共生理念。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在160个国家(地区)建设498所孔子学院和773所孔子课堂,这对于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强调的人类情怀和大国担当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为全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保驾护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家文化建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绝不是搞文化复古主义,而是要采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历经几千年的传统家文化去芜存菁、去伪存真。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紧抓历史机遇,“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5],守好马克思主义“魂脉”,筑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9.
[2]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18(2).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6.
[5]曾振宇.孟子新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7.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9.
[8]何丽野.“家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中的嬗变与展望[J].浙江社会科学,2013(7):12-21+155.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求是,2021(14).
[10]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
[11]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6(2).
[1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1).
[13]曾振宇.孝经今注今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4]代生.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与“两个结合”的文化底蕴[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79-89.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4.
〔责任编辑: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