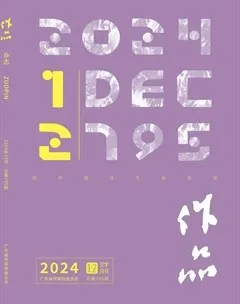卡珊德拉的预言(外一篇)
南瓜灯博士就是南瓜灯先生。
美国作家查理德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里面的小说《南瓜灯博士》,主人公是一个从乡下去城里念书的性格孤僻的小男孩。
南羽很喜欢这个美国作家,他买了查理德耶茨的所有著作。当时他受困于二十多平方米的公租房,为了把《革命之路》也一齐买上,他花光了自己的生活费。大葱拌豆腐,真是一穷二白了,甚至没有想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呵,不就是一个月面条吗?一个月后又是好汉。阅读查理德耶茨就像和老朋友在一个宁静的音乐酒吧相聚,听着民谣《安河桥》,微醺恰好能够袒露胸怀,说些后悔的事。
《安河桥》?是那个前奏一响狗都会流眼泪的《安河桥》?南羽打开网易云,很快找到了它,强烈的欲望迫使他又为自己的情绪投入了十几块钱。
真是铁打的会员,流水的钱。为一首歌开个会员值不值得?
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时的冲动总是迫在眉睫。
话说回来,《安河桥》治好了他的失眠。戴上耳机,他可以在极度孤寂的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回音,如同灵魂出窍一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摆脱了疲惫、麻木的躯体,在真空中生活,那里不存在病变。
南羽爱上民谣与他爱上查理德耶茨几乎是同时的,艺术说到底都是殊途同归。
南瓜灯先生起初是南羽的网名。由于他立志做一个出色的作家,因此成了他的笔名,笔名公开亮相是在一本著名的文学杂志上,内容是阳光大道上席地而睡的货车司机。他每天下班回宿舍都经过阳光大道,其实那并不是阳光大道,那是工业大道,一条只有大货车经过并且没有路灯照亮的宽阔的沥青路,周围是一人高的芦苇和不知名野草,月光锋利,十分幽深而昏暗。
雨又来了。
他更加坚信一件事:不管科学多么发达,都无法征服自然。是的,科学无法预测天灾。这场雨对他来说莫过于一场灾难,他出门从不习惯带什么东西,包括伞。
雨水很快占领了乡贤文化公园以及那里的亭子和亭子里的棕褐色长凳。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不是不可能。雨下得南羽心情有些烦躁,他的心事太多了。
碰碰车摊主以为用绳子沿着路灯的分布把广场中心区域围起来就是他的天下了。的确,绿色显眼的绳子为他的生意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其他人都绕道而行,仿佛广场真的就是他的一样。
南羽不乐意这样的行为,因为广场是所有来这里的人所有,他不应该圈起来。他不说话,在亭子里往乡贤文化公园的牌坊望去,摊主正慌乱地把碰碰车推到牌坊下面。那是一条三层翘檐式牌坊,面向北位于永顺路的一侧,面对宽阔的永顺路显得极其狭窄。摊主独自撑着伞,没有离开一步,连一个和他打招呼的人都没有。
南羽看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说晴天会持续到下午四点钟,四点钟那一刻他正坐在一家咖啡馆喝着咖啡,强烈的感官刺激让他想到一块水豆腐馊了,不可思议的是他放进了冰箱,中途他去参加了一次约会,便忘了吃。
一块馊了的水豆腐。它足够坚强了,持续三四天持续被人忘记,拿出来的时候浸泡豆腐的水体变得有些浑浊,隐隐发绿。咖啡异常苦涩,直到舌根才有了一些甘甜。太阳照耀在重叠的云层上闪闪发亮,此刻云层低得出奇,正缓慢地朝着咖啡馆移动,南羽坐在四楼,从落地窗中能窥视到城市和在这里翱翔的鸟儿。
砰砰砰……撞死一两只后,鸟儿们在落地窗前不知所措地用翅膀拍着,它们想扑进来。并没有什么诱惑性因素,它们单纯地想进来。这里有什么好?
全是无事可做,消遣时间的客人。南羽有时候也想让它们进来吧,风餐露宿不完全都是好的,但是他无能为力。
今天笃定不会下雨了,除非勃南大森林会移动。
他为了让少有的闲暇时间更有兴致,决定起身出去散步。沿着圭江走,河堤多树木,疏影错落有致。偶尔凉风带来快意,他把这种不确定看作是一种反叛,和突如其来的暴雨别无二致,说不上来其他的。
南羽想一直走下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直到夜幕降临,圭江北上的尽头会多一个男人的背影。
天变比翻书还快。云层叠得越走越厚,遮住了太阳,愁云惨淡,雨就哗啦啦下了。南羽脑子里还是那片勃南大森林,《麦克白》中的桥段已在他脑子里消失殆尽,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女巫为麦克白提供了三次预言,因此麦克白杀了国王邓肯、班柯,女巫还告诉麦克白永远不会被打败,除非有一天树林向高山移动。
那么森林移动了吗?
麦克白要杀的还有麦克德夫。王子马尔康最后回来了,麦克德夫也在其中。森林怎么会移动?王子马尔康带领军队砍下整片森林作为掩护,草木皆兵是吗?
他已经来不及思考更多了。他开始往回跑,并在途中扫了辆共享单车,到达了乡贤文化公园的亭子。到达公园前,雨不是最大的时候。雨滴在他白色长袖衬衣上划过长长一段,沿着布料的纹理发散开,并没有湿透,反倒像长满了羽毛。
他感受到雨滴的温度,这个温度正好,吹一吹就干了。
那次约会坏掉了一块豆腐。南羽本想做芥菜豆腐蛤蜊汤,一定要放白胡椒和姜丝。
至于那次约会,没什么特别。南羽在一处网咖度过了整个晚上。其实他早就知道钥匙会掉,准时赴约让他感到有些紧张和压力,本该拥有一次愉悦的心情。
他有轻度的强迫症,每次强迫症犯的时候总会带着一些疏漏。他站起来抖了抖衬衣,用手按住不停跳动的左眼皮。
回想起来,他总埋怨左眼皮在那天跳了一整天。但是他无能为力。
在九月见面
终于他们又见面了,南羽和他的女朋友语莺,在北流步行街的一家餐厅。
北流步行街是北流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维多利亚时代的仿古路灯和门店灯牌把夜空点饰得恰如其分,黑铁的灯座和精致的雕刻让这个夜晚分外典雅。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他们开口说话。
浪漫永不落幕。
许个愿吧。语莺虔诚地双手合十,紧闭双眼。睫毛的影子照映在墙上,纤长、卷翘,墙上是一幅壁画,绿色的青蛙。
干杯!
干杯!
在语莺的生日晚餐过后,南羽决心在这里住上一阵子,他回绝了一些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工作。如果遇到辗转反侧的失眠夜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
别在晚上做决定。
为什么?
晚上只适合做梦。
晚上只适合见你。
但愿吧。
他们心不在焉地笑了。共处对于刚结束异地恋的情侣来讲是多么难得。不过世事难料,就像语莺毕业就到了北流,而南羽花了两年。如果在生活中事事都如人所愿,又有什么深刻呢?
南羽比语莺高两届,南羽大四,语莺大二。一定是上天给他的恩赐,他很庆幸。年轻人们把校服被婚纱代替看作是一种幸福的仪式,相当神圣的仪式。
可是一纸凭证从来不是那么轻飘飘的,结婚也不像婚纱的裙角随风飘摇。不管怎么说,付诸行动比承诺更重要。
他一时间辞掉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在一家国有企业做文字秘书,一份是高中教师。
南羽收拾好行李,上了火车,黑色行李箱容量太小,除了一些衣物和日常用品外,再也装不下一点东西。分期付款的空调和热水器还不完全属于他自己,在宿舍顶楼只有源于九月的温热是完全属于他,且不由他选择。
上了火车。出发前,别意唤醒了他对使用多年的行李箱的爱意,因此他买了新的行李箱提手进行更换,黑色的喷漆足够让一个生命重焕生机。
那是夏天余热蔓延的九月,人们称它为“秋老虎”,一只充满野性的猛虎是多么贴切、生动。
四百多公里后,他进入了玉林地界。各地的文旅宣传工作做得很详细也很及时,短信送达手机时发出阵阵振动,他的心跳也是如此。
他鼻子尖儿酸酸的,但仅仅是鼻子尖儿。终于与语莺又见面了。
此后的一年里,他还在忙于考试的时候,总有许多人替他惋惜,比如提前到来的雨季。
没什么后悔的,人总要有些缺憾才算完美。他大学没挂过科,年轻时也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他曾经以为那是最好的结局,可结果恰恰相反。他毕业两年后回到北流时,才意识到这一点,其间并不是一切顺利。
缺憾和完美是个永恒的辩证命题,永远无法谈到一块去。就像爱与被爱,很多时候不能画等号。等号不适用这个世界,南羽用绝对来形容它,没有一件绝对的事。
所以他接受了一切缺憾。
步行街的石板路没有想象中的平坦,电车驶过它会发出清脆的砰砰声。
就像世界上没有一处没有一点瑕疵的街道一样。他对语莺说。
他说的话语莺也许没听进去,但是墙上的影子记录下来了。南羽与这家店逐渐熟悉起来,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带着语莺来到这里。
这家店主要是卖蛙的,是煮熟的蛙,当然还有其他的许多美食,酸辣小皮蛋、去骨鸡爪和爽口鱼皮。两人餐一次一百五十八,要比桂林贵得多,不然怎么说各有各的不同呢?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
吃过蛙吗?
没有。这是第一次,说实话我还没做好准备。
这里的紫苏蛙最好吃。
真好吃。
南羽爱上吃蛙了,就在这家店。
什么时候开张的?
不清楚,我没在这里吃过。
看样子有几年了,我为什么没发现?
现在的店面都特别注重形象,随时都在更新,很难看得出来它的年龄。
那倒是。
我真决定在这里住下来了。
别在晚上做决定。
我说真的,以这杯酒为证。他倒满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
你嘴角漏了一滴。语莺说。
没关系,再来一杯。他果然再来了一杯,一滴不漏地喝下了。
你不是不喜欢喝酒吗?
现在我心里有棵火苗,一不小心就会蔓延成火灾。
与他工作时完全不同,他和你说过他不喜欢喝酒。
所以需要浇灭吗?呵呵。好了,没问题,如果你能找到安稳的工作的话。
南羽顿时有些语塞。他咽了咽口水。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他们就这样度过了一次美好的晚宴。当晚他们去了银行附近的一家酒店,因为还不满足住在一起的条件,他们还没有住处,除了自己的家。
那时语莺刚毕业不久便到北流的一家银行上班,她打算搬进职工宿舍。但是今晚还不行。职工宿舍是一栋老楼,它为银行服役了近三十年。原来没有生命的楼房也会衰老,这就对了,一切都有使用周期,只不过它缺少一张说明书和在墙体喷上保质期限。
确实够乱的。墙体光滑的石膏偶尔脱落一块,老式绿色防盗门开关时稍微用力就会哐哐响,屋子里堆满了杂物,灰尘覆盖厚厚一层,蜘蛛网见证了这里的冷热。
南羽时常看见壁虎。语莺说壁虎是益虫,它会吃蚊子和水蚁。
下雨前夕你就知道了。她说,成群的水蚁在窗外聚集,它们会想方设法从窗户的缝隙中钻进来。
飞蛾扑火,你见过吗?
见过。
那没什么说的,一样的原理。
晚餐过后,他们还不想回家,往陵宁路的一头走去。北流就像一个球,无论走哪条路都会走到家。
九月晴天居多,仿佛秋老虎治愈了所有眼泪。
责编:胡破之
——他者形象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