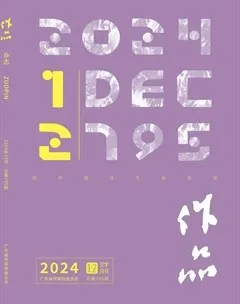虚浮的概念
在翻阅完广奈的这几篇小说之后,我立即找了后续的几期关于广奈小说的评论文章。读到那篇《用广奈体小说回赠广奈》时,我会心一笑。先澄清一下,评论中将这种写作手法归于“碎片式”叙事手法,不太严谨。“碎片式”写作手法的核心,是将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切成碎片后,用增加探索成本的空间障碍打乱叙事的时间线。这是一种在探索解密游戏中非常普遍的叙事技巧。在另一篇评论文章中,作者本身是个电子游戏爱好者,他强调广奈小说中的“致幻性”,对于这种小说风格的接受度就比另外两位要高得多。
其实这种“致幻性”小说,我最初是在二十年前抽屉写的《比爱更喧嚣》里接触到的,那是在青春文学最繁荣的时期;紧随而来的网络文学发展初期,也有像冥灵这样的作家在奇幻作品里选择这种风格。总体来说,与很多人面对这样的文字还颇感新鲜不同,我却觉得这样的风格让人颇有怀念之味。
但真要说起来,广奈的文字比起上个“世代”的作家,更有些当下的风味。当今的国内网络游戏世界构成中,广泛而普遍地使用这种写作手法——将通俗的东西用读者(绝大概率)觉得陌生的词汇替代,构造一种新的“概念”。为什么是新的概念而不是替换的概念呢?因为这样的替换是非原物的。这样的替换手法在早期的奇幻文学里其实还不显,因为奇幻文学抓住的是神话与历史文学的延长线。这样灾难性替换的开端更多地体现在“科幻”题材里。因为科学词汇天生就具有精英化的性质,最方便地适用于营造陌生感的条件。(顺带一提,当今短视频信息流推广中,最重要的就是利用这种“陌生”感取得听众的信任。)在“泛科幻”题材作品里,扭曲科学定义下的某物概念成为普遍现象。当“光锥”“原石”“坍塌”这样的词汇,被包裹在精心包装的所谓“世界观”中,作者赋予它们新的定义后,它们原本科学上的定义将不复存在。这是我读到广奈的《弹射》,看到里面不严谨地利用曲线、线段、质量、坍塌等数学与物理学概念之后想到的,大概严谨了之后,它可能会是一篇科幻小说。
而说到广奈的《我们如此热爱飞跃》与《“石头剪刀布”虚构史》的时候,我不禁要感慨,“谁家的游戏文案把设定稿搬出来了”。这大概更能体现我上文说的“当下的风味”——文章在用编史的手法构造世界的风貌、构造游戏的规则(当然这其中包含我上文提到的大量的替代式新概念)。这样的叙事是绝对性浓缩的,而不是展开的。它在行文中必定抹去了世俗的情绪和传统叙事——我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些“老掉牙”东西的偏爱,但是也不爱看到它们是这一切浮华概念包裹的世界之内展露的本核。但是精雕玉琢的场景建模终归只能提供有限的场景叙事,作为主角的玩家如果不踏进来,一切意义都不复存在。
所以在我看到《恐龙拼图》的时候,我以为终于要有一些值得抚慰阅读情绪的“老掉牙”的东西的时候,文章却在回忆录式样的时间线(Timeline)里又重走了“概念化”的老路。在文章中,“他”的消亡与恐龙的复活是必然的,在叙事上,“他”的消亡与“概念”的浮起也是必然。或许要说,“他”在整个过程中经历了坎坷、困境,也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很可惜,恐龙与拼装的“概念”夺舍了“他”的生命力,在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
说了那么多,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恶意,我只是觉得,在面对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小说”这一概念无法完全地包容它。它毫无疑问是文学创作,但是当以“小说”的概念去看待,这显得有些奇怪。当下的文学作品追求一种新意的时候,最激进的保守派也无非像我这样将它们作为点装天空的气球,它浮于空中之美,用近乎密码的含蓄文字包含着一段等待发掘的“黑幕”。然而当它作为主菜被端上桌时,与当今很多网络游戏叙事选择的一样,“概念”夺舍了全部,吸引了眼球,人们在赋予词汇以新的意义中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