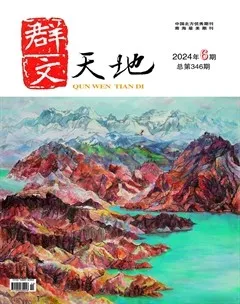声声“曲儿”流淌心间


如果有人让我选择一种声音去代表青海,那我一定会选青海地方曲艺。时代的车轮不断滚滚向前,从温饱得不到解决的贫穷年代,到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被青海人亲切地称为“曲儿”的青海地方曲艺,如一条声音的河流流淌在青海人的心间。追逐着这条声音的河流,青海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祖祖辈辈,生生不息,见证这片土地的变化与发展。
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到中心广场漫无目的地闲逛,走到一条板凳前坐下来,将要西斜的阳光暖烘烘地晒在背上,我打起了瞌睡。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段唱腔,就像在广袤的黄土高原听到了信天游,我下意识判断这声音一定属于青海,顿时睡意全无。我起身循着声音走去,远远地望见一座亭子下,有一位白胡子老者坐着马扎,手拿三弦,正在声情并茂地弹唱。他的前面不远处放着一只大碗,里面零零星星放着几张钱,亭子周边围着十几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我在那个大碗里放了5元钱,也悄悄加入了听者的队伍。
天空湛蓝,阳光温暖,一群鸽子撒欢般掠过头顶。长长的声线飘荡在耳畔,深情婉转的悲伤中又有一些铿锵。一时间我有些恍惚,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在外公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同样的声音。我猛然想起,外公把它叫作“曲儿”。这时老者一曲唱罢,我突然有些激动,忍不住凑上去与老者攀谈。短暂的谈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老人说,他从二十几岁就靠卖唱为生了,如今已经78岁了,唱了大半辈子。本来有几个同伴也在这里一起唱,但都相继去世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人。他告诉我,他唱的是贤孝,是“曲儿”里的一种,传统的曲本都在他脑子里,客人不管点什么曲目,他都能唱,只是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少。看着老者骄傲的神情中透着一丝忧伤,我心里隐隐有些难过。几年后,我又到中心广场找过他,可是他已不在那里了。现在想来,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看过的坐唱表演。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才知道“曲儿”学名叫青海地方曲艺,常见的有青海平弦、青海越弦、青海道情、西宁贤孝、打搅儿、倒江水、太平秧歌等多个曲种,它们各有各的特色和味道。青海平弦被誉为青海地方曲艺中的“阳春白雪”,素有“十八杂腔”“二十四调”之称,曲调优美典雅、委婉柔情;青海越弦是青海平弦的“姊妹”艺术,又被称为月弦、月调、背调、越调、座场眉户等,曲调旋律流畅爽朗、刚柔相济、节奏紧凑、轻重有序;西宁贤孝是广受当地百姓喜爱的曲种,它的曲牌丰富且特色鲜明,唱词质朴平白,故事情节生动感人,具有教化功能;另外,青海道情、打搅儿、倒江水、太平秧歌就像各种“调味品”,它们的存在让青海地方曲艺的意蕴和味道更加深厚、丰富。
我以前全然不知其中的分别,后来在群众中调研时才发现,他们大多数人也只知“曲儿”不知曲艺,“曲儿”似乎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叫法。跟他们提及“曲儿”,他们会瞬间眼睛明亮地与你搭话,若跟他们聊青海地方曲艺,他们似乎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回答。这几年,我们经常到基层调研曲艺,对青海地方曲艺这样一种饱经沧桑的民间艺术和对那样一群矢志不渝支撑这门古老艺术不断前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汹涌心间而无法言说的特殊情感。
去年,我们去基层调研,有一个曲艺团队令我印象深刻。那天我们从西宁出发,不一会儿便拐到了一条狭窄的小路,这条路只能并排通行两辆车,路面有些坑坑洼洼。时值寒冬,车窗外的树都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片枯涩景象。窗外没什么好看的,我只好闭上眼睛睡觉。汽车在小路上呜咽着、颠簸着前行,我在车里睡了一觉又一觉,不觉间,时间已过去两个多小时。车辆行驶到了一个小镇东头破旧的二层小楼下停了下来。我们疲惫地下了车。只见几位老者等候在此,热情地招呼我们上楼。
我仔细打量,感觉这栋老楼像已废弃多年,墙体斑斑驳驳,楼梯破破烂烂。心想在这样一个条件受限的场所开展活动的团队会是什么样的呢?我边上楼边思忖着,不一会儿,我们便被引进了一扇门。然而,这扇门内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阵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在一个教室大的地方,足足有二三十人,看穿衣打扮大多是庄稼人。他们有的正在唱“曲儿”,有的正在弹拨乐器,有的正在喝茶讨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打动,这才是民间曲艺该有的样子嘛,好一派自由舒展的气质。一见我们到访,他们都安静下来了,坐着的人全部站了起来。只有几个人过来给我们打招呼,其他人都羞涩地在旁边望着。
这时,走过来一名四五十岁的妇女,短头发,戴着眼镜,衣着朴素,同样有些腼腆和羞涩。旁边有人介绍说,这位正是这支民间曲艺队的负责人。我们便与她围坐在一旁详聊起来。交谈中得知,她曾经是民办学校的教师,退休后凭着对曲艺的一腔热情,成立了这支民间曲艺队。没有场地,她就自掏腰包租场地;没有乐器,她就自己出钱买乐器。队伍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了五十几人,她也默默支撑和陪伴曲艺队走过了近10个春秋。其实,她的家庭并不富裕,曲艺队的经费一部分来自老伴营务庄稼,一部分来自儿女打工。好在家里人尊重她的选择,也一直默默地支持着她。当时,我突然对眼前这位长相平凡、不善言辞的妇女,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敬意和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动。在这样一个偏远的乡村小镇,一名普普通通的妇女,为青海地方曲艺的发展付出了这么多精力,却一直默默无闻地耕耘,她从不计较得失,而是一直为曲艺事业付出着,这在我看来不失为一种奉献。
回到单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在我们身边,还有那么一群可爱的曲艺人,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像播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反复闪过。他们当中有经营公司的老板,因为爱好曲艺,将自己的收入大半投在这项事业上;有曲艺非遗项目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经营着亏损的茶社;有长期给曲艺爱好者免费拍摄、制作视频,分享到媒体平台的人;还有一些人默默去乡村山区义务指导,扶持民间的曲艺团队成长;还有一些人把自己家当成曲友们的排练场地,经常做上一大锅面片让大家吃饱……正是因为有这样无数长期钟情于曲艺而无私奉献的人们,才极大地推动了青海地方曲艺在新时代的传播与发展。据一些长辈讲述,“曲儿”在以前只是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每个村里大概只有那么几个“唱把式”,而如今唱“曲儿”的人越来越多,这是青海地方曲艺之幸,也是老百姓之幸。
时代在进步,曲艺在发展,从坐唱表演的单纯质朴到舞台表演的华丽多彩,随着一代代曲艺人的不懈努力,青海地方曲艺从“曲高和寡”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而青海人心目中“曲儿”的本质依然没有变,它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在我心里,青海地方曲艺已不单单是一种民间艺术,而是人与人之间精神互动、传递温情的纽带,它带给了我们持续不断的精神鼓舞和生命感动。“曲儿”声声,诉不尽的过去,唱不完的未来,始终流淌在我们的心间……
(作者单位:西宁市文化馆)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