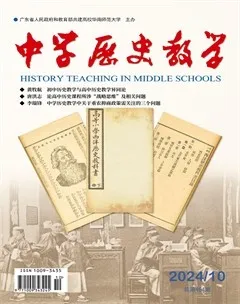明清时期的玉米、甘薯是否高产?
摘 要:高中历史教材《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一课就玉米和甘薯等外来作物对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作用作了评价。但在描述玉米甘薯的推广种植时间、“高产”性质以及能否“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三个方面,课文的用语存在着含混不清以及史实性错误。依据史料和农业史研究数据,可对以上问题进行勘误,同时也能为日后的历史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玉米 甘薯 农业史 《中外历史纲要》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5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评价玉米和甘薯对明清农业发展的作用:“明朝中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输入中国。其中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的推广种植,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总产量……”[1]
从课本的编排和与《中外历史纲要(下)》内容的一致性来看,此处关于玉米和甘薯的内容将中国的历史与世界联系起来,可以说明中国从来不是自闭地发展,而是一直与世界其他地区互动关联的。但是,课文的判断不够严谨。这种不严谨既体现在对玉米、甘薯等美洲农作物作用的判断上,也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而具体来说,课文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存在不当的判断。
一、关于玉米和甘薯引入中国和推广种植的时间点问题
美洲的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作物品种是在新航路开辟后输入中国的。从时间上来看,约1500年左右正是明朝的中后期,这里并无什么错误。可课文“其中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的推广种植……”一处似乎模糊地将玉米、甘薯等作物的推广种植归入明朝中期的时间段,这就是判断失当之一。af68e267d18123cc3f54b23325bc5136
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载:“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2]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只在“蜀秫”一条的注中写到:“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3]两者均为明朝后期对农作物有深刻了解的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了玉米在当时之罕见。根据程杰的研究,现存930多种明朝时期的方志里,只有7例提到了玉米,亦可见当时玉米的种植范围极为有限。[4]玉米逐渐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是在清朝的乾隆—嘉庆时期;而它在全中国范围内的铺开种植则要延至清朝后期、甚至是民国时期。[5]
同玉米的情况类似,甘薯或番薯的引入时间点和推广时间点存在时差。在明朝中期,甘薯首先传入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此后慢慢向西部、北部地区辐射传播。甘薯传入安徽、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时,也几乎是乾隆年间了。[6]这时与明朝中期已相距大致两百年,且当时甘薯在上述几个省份内都算不上大量种植,更不用说在中国的版图上广泛种植了。
二、关于玉米和甘薯的“高产”性质问题
在今天,粮食作物是对谷类作物即小麦、水稻、玉米,和薯类作物即甘薯、马铃薯等还有豆类作物即大豆、蚕豆、豌豆等作物的总称。它们为人类提供淀粉、蛋白质、脂肪等必须的营养素。不过,在明清时期,玉米和甘薯还没能成为小麦、水稻的替代品。
中国拥有悠久的水稻和小麦种植史,许多的考古证据表明长江中上游的中国先民在公元前七千纪就开始人工种植野生稻,小麦则大概在公元前三千纪从中亚引入中国。[7]
中国先民们选择稻、麦作为主粮有坚实的依据。首先,两者都能够在中国的大部分区域种植,北方能够种植小麦,南方则可以做到稻麦复种。其次,两者的产量相对高且稳定。以明朝为例,江南稻麦轮作能达到今每市亩288市斤,北方则能达到每市亩约产小麦145市斤。[8]更重要的是,小麦和水稻都是淀粉含量高、水分少的作物,能量密度高,且由于水分少,储存和运输都十分便利。这些优点使之成为中国人餐桌上恒久不变的主食。
玉米和甘薯同水稻、小麦比较,综合水平上并没有突出的优势。玉米和甘薯确实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可以在山地等难耕作稻、麦的地方种植,且亩产量不低。虽然明清时期没有对玉米、甘薯种植数据的记录,但民国时期有较为详尽的种植记录:从1931年到1937年,中国的玉米年单位面积产量平均为184市斤/市亩,甘薯为1027市斤/市亩,对应的,小麦为142市斤/市亩,水稻为331市斤/市亩。[9]
可需要明晰的是,玉米的重量里相当一部分是秆重,且玉米脱粒较小麦、水稻困难,故以上的数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食用的重量。再看甘薯,其含水量超70%,同重量下提供的能量较少且难以长期储存。1949年后,我国薯类折合为原粮的比例为5:1,如按此比例折算,依照民国时期的数据,甘薯的“有效”亩产应合当时200市斤左右,不及水稻。玉米的亩产则本来就不如水稻。更需注意的是,上述数据来自民国,明清时期的农业科技水平绝对是不如民国的。所以,明清时期的玉米、甘薯产量从大样本来说必然且远远少于民国时期的产量。因此,课文中评价玉米和甘薯是“高产”作物,这在明清时期是难以成立的。“高产”一词用在课文语境下是不够准确的,这是判断失当之二。
还需强调的是,水稻和小麦拥有种植史上的优势,它们早就成为了中国人的饮食日常。正如水稻引种到欧洲没能撼动欧洲人餐桌上面包的地位,作为后来者的玉米和甘薯要登上中国人的餐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明朝中期到清朝的三四百年是不足够的。如上文所述,玉米能够适应山区的环境,耐旱还耐寒,产量也相对不错;甘薯对土壤也不挑剔。可两者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玉米虽能适应山区的恶劣环境,但没有合适的水、肥条件,它的高产潜质不能发挥;甘薯则是典型的热带、亚热带作物,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适合在22—30℃的温度条件下生长。因此,在明清时期的环境、科技条件下,甘薯没法在北方推广开来,只能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温暖的广东等地区种植。玉米在南方平原地区竞争不过水稻,在北方则因为水肥条件不足还不能越冬而竞争不过小麦、粟、大豆。
三、关于玉米和甘薯能否“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问题
如果新引入推广的农作物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总产量,那么它一定有如下的特质:单位产量高;种植面积足够大。
单位产量高这一点,在明清时期的玉米、甘薯品种上是不存在的。虽然当前我国甘薯产量连年位居世界第一,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选种培优、精耕细作、科技进步的结果。根据上文引用的民国时期数据,明清时期的玉米和甘薯品种是无法达到绝对意义的高单位产量的。
玉米和甘薯的种植面积在当时也是不够大的。首先,上文已经分析过它们对种植环境的要求,因此,在明清时期的条件,农民们很难主动选择种植玉米和甘薯。传统农业讲究稳产甚于高产,因此农民们会追求多样化的、可持续的种植,规避单一种植的风险。何况,“玉米的抗逆性强,耐寒耐旱耐瘠,但……耐旱不如小米、耐寒不如荞麦”,[10]盲目地扩大种植只会带来损失,这对小农经济下的农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玉米在平原地区吃不开,只有在人口不断增长导致的明清人口大迁徙中,成为流民果腹的食物,随着福建、广东的移民进入江西、贵州、湖北的山区。[11]玉米在山区种植也有问题。山区土壤疏松,玉米却根系发达,容易加剧水土流失和土质松动,引起环境问题,这一点也不利于玉米在山区的扩大种植。
到嘉庆、道光年间,“番薯的集中产区仅限于东南地区……清代中期,山东仅有泰山山脉形成小规模的番薯集中产区,直到清末民国年间,山东半岛才出现环胶州湾集中产区”,[12]由此可见,甘薯虽可在山区、沙地种植,但其种植面积始终不大。此外,甘薯并不符合时人的饮食习惯。甘薯的口感并不好,淀粉含量高但蛋白质含量低,糖量偏高容易导致胃酸,还会引发胃胀气等问题,所以一般是底层平民无奈之选,常做救荒作物,与中国人长久以来的稻麦蔬菜饮食习惯并不契合。
同时,甘薯、玉米没有融入明清的赋税体系。中国传统社会的赋税体系是“钱粮二色”,作为“粮”的玉米和甘薯口感不好,价值不佳,不能作为地租上交,于是也更卖不出价格,难以换“钱”。[13]大量地种植它们对农民来说反而是一种经济负担。
因此,在课本所述的明清时期,玉米和甘薯既缺乏高单位产量,又难以大面积种植,也就不能“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这是课文判断失当之三。
另有一些研究数据可以作为以上论点的支撑。据吴慧估算,考虑玉米和甘薯的因素,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全国平均亩产从2.326石增加到2.44石,增长了4.9%,大概增加了17市斤。而与明代相比,由于玉米、甘薯和双季稻的作用,清代亩产增加了16.8斤。[14]可见,玉米和甘薯即使有提高粮食产量的效用,幅度d1UaixHzeLHAAfKMcN9sXg==也十分有限。再考虑到它们种植面积的相对狭小,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其真实效用还会下降。李昕升和王思明的研究则指出,1914年民国的玉米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4%,甘薯则占1%。[15]按照如上结果反推至明清时间段,玉米和甘薯的种植面积占比只会更小。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5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的第1子目《经济的发展与局限》中关于玉米和甘薯对明清时期经济的作用的判断不够精准。整句话如改为“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明朝中期,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输入中国。其中玉米、甘薯在明清两朝逐渐推广种植,对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做出了一定贡献。”这样能减少歧义,也会更忠于史实。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有一句名言:“历史对屠杀我们人类的战争大肆颂扬,而对使我们得以生存的耕作田园却保持缄默。历史知道帝王的私生子,却不知道小麦的起源。”[16]在大部分学生和教师的眼中,历史的学习是围绕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展开的,这点从课本知识点的分布上也能看出。虽然农业史、粮食史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看上去“热度”不高,但就笔者收集的资料来说,早在建国初期就有对各类作物的亩产统计,还有对中国古代农产的估算和分析,成果颇丰。而玉米和甘薯作为“哥伦布大交换”中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物种,对世界近现代史的影响深远,它们在全球史的研究中早被当作标志性物种研究透彻,结论已经十分普遍。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当前,党和政府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笔者认为,高中历史教育也必须跟进农业史、粮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向学生讲述正确的农业发展脉络。除了课堂教学,学校还可以开展田野教学,让学生实地体验粮食种植。此外,还可以设计对应的项目学习课程,结合语文、生物、通用技术等学科综合探索人类的农业种植发展。
【注释】
[1] 教育部:《中外历史纲要(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82页。
[2] 李时珍:《图解本草纲目》,西安:三秦出版社,2023年,第138页。
[3]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29页。
[4] 程杰:《明朝玉米传入与传播考》,《阅江学刊》2021年第1期,第125页。
[5] 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8—56页。
[6] 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6—38页。
[7] [美]罗伯特·N·斯宾格勒三世著,陈阳译:《沙漠与餐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04、184页。
[8]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第187—192页。
[9]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26页。
[10] 李昕升:《食日谈》,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第190页。
[11] 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第49—50页。
[12] 王保宁:《乾隆年间山东的灾荒和番薯引种——对番薯种植史的再讨论》,《中国农史》2013年第3期,第10页。
[13] 李昕升:《食日谈》,第179页。
[14]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207—208页。
[15] 李昕升,王思明:《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9页。
[16][法]法布尔著,鲁京明译:《昆虫记》(卷10),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83—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