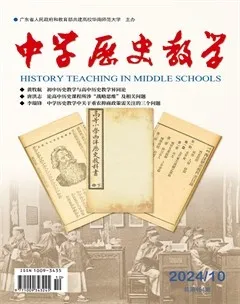中学历史教学中关于重农抑商政策需关注的三个问题
摘 要: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长期施行的经济政策,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历史概念。教学中,我们应关注重农抑商政策实施的一贯性与差异性,既了解其延续性,又关注其变化性;关注重农抑商政策的立体性与复杂性,从农民、农业、商人、商业与国家的关系来进行探讨;关注重农抑商政策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相背离的现象。
关键词:重农抑商 差异性 立体性 背离
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施行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对古代社会影响巨大,也是中学生学习古代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外历史纲要》将其散落在商鞅变法的内容中和明末清初思想家的主张中。基于该种呈现方式,学生掌握和理解重农抑商这类跨阶段的历史核心概念略显吃力。笔者结合近期高三教学工作,谈谈如何更好开展纲要体例下重农抑商政策的教学。
一、关注重农抑商政策实施的一贯性与差异性
任何一个跨阶段的历史政策,既有跨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一贯性,又存在具体发展时空的差异性。因此在具体教学中,我们既要明确这一概念内涵的一贯性和延续性,又要让学生了解这一概念外延的动态变化性。重农抑商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其一贯性主要是指重农抑商政策曾前后代代相承,几乎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差异性则指的是在共同的重农抑商政策框架下,历朝历代施行的细则、力度大相径庭。[1]
重农抑商政策,顾名思义,就是重视、鼓励农业生产与发展,抑制、阻碍商业的进步与扩张,这一政策几乎绵延我国古代社会。战国商鞅变法“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如此亡国则不远矣。”[2]主张重农抑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定为基本国策并刻在琅玡台石壁上,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汉武帝施行盐铁酒专营和“算缗”“告缗”政策,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抑商政策较之前朝更甚。隋唐初建,抑商政策有所缓和,安史之乱后,抑商政策又从紧。五代十国乱局,重农抑商成了当时统治者共同的选择。宋朝为解决“冗费”问题,“抑商”有所放松,但“重农”并未降低。元朝在对外贸易中较为宽松,但由于民族政策,中国的商业并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发展。明朝因对白银的需求而一度放松海禁,但关于抑商的条陈却从未中断。清朝重农抑商则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峰,此时不但工商业发展受到抑制,就连唐宋时期较为开放的国门也被逐步关上,直到19世纪中叶列强侵华,朝廷对社会控制大为削弱,重农抑商政策难以为继,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古代社会不同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施行的细节、力度却有很大的差异。整体来看,秦汉时期为稳定统治,对商业的抑制较为严格,中唐至宋末,抑商政策有所松动,明清前期对商业的抑制较为严格。其次从商业的结构来看,并非所有的商业都抑制,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专卖制度成为国策,加上之后的“漕运”“海运”等,说明官营商业是政府鼓励的,抑制的主要是私营工商业。再次,从具体抑商的细节来看,有些朝代从税收,如汉初的“重租税以困辱之”,清中的“凡出盐籍商于官,以配杂税而榷之”,从身份,如历代“贱商令”、汉初“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明初“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等方面对商人加以控制。从空间上来说,西周至中唐,严格的坊市制度中对私营工商业的抑制较为规范,宋之后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政府对商业经营地点限制逐渐减少,但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侵扰,政府逐渐加强对重要的海关、港口、边镇等地的商业管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重农抑商又由于其具体阶段社会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差异性。
由此,在具体教学中,针对一些重要的跨阶段历史概念,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儒家思想”“代议制民主”等,我们可以从一贯性和差异性两个角度来进行认识,既明确其概念内涵延续的一贯性,更让学生认识到跨阶段的历史概念在时空的变迁中会呈现出的差异性及动态变化。
二、关注重农抑商政策的立体性与复杂性
要对重农抑商这一重要经济史概念进行全面的学习和认识,单纯关注概念本身内涵演变还不够,还要关注其概念外延所涉及的其他概念,运用联系的方法,从其他关联概念出发,丰富这一历史概念。如从农民、农业与国家的关系,来探讨政府为何要重农?从商人、商业与国家的关系来探讨政府为何要抑商?从古代经济结构、及统治者对农商关系的认识来分析重农抑商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由此,关注重农抑商政策的立体性和复杂性。
从农民、农业与国家的关系来看重农如何成为社会的共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4]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于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在生产。”[5]因此政府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从维护国家统治基础的稳定和发展出发,要保护农民、保护农业,因此“重农”就会成为社会共识而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
从工商业、商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抑商如何成为政府的选择。战国时期,随着铁犁牛耕的使用,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各国变法逐渐强调“本业”为农业,有些国家开始对“商贾技巧”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事本禁末,逐渐成为战国时期耕战理论的核心内容。此时,多业并存已不是社会生存的必须,为争霸或强化集权的发展需要,“重农抑商”就逐渐成为政府的选择。秦汉以后,民间流传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谚语,[6]造成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荒芜;富商大贾“得管山海之利,……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7]大商人与豪强地主的结合逐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抑商成为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一项政治措施。同时国家依赖固定户籍进行赋税徭役的管理,而商人的流动性则使古代国家根本无法进行赋税徭役的管理。唐朝时抑商则和科举考试连为一体,抑制商人进入统治集团。宋朝时对商业态度有所改变,其主要原因是为增加国家收入,解决“冗费”和岁币问题。明朝时期抑商更多是因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倭寇”、西方殖民势力侵扰边疆,政府主要为抗击侵略,巩固统治。再加上“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8]“商人对于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9]因此抑商就成为统治阶级的理性选择,它构成了集权国家实现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既可以带来财政上的好处,又可以遏制贫富差距,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同时还可以将社会矛盾转移到商人身上。
从农业与商业的关系来看,统治者的认识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局限,认为二者存在对立关系。无论在早期人口不足时期,还是在人口过剩的康乾时期,“市肆之中多一个工作之人,田亩之中少一耕嫁之人”,统治者仍然认为从事工商业会威胁到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总量。因此,明清时期统治者刻意通过“农贵商贱”来调节农商从业比例,使农业容纳过多的劳动力;同时商人地位的低贱,更多人“弃商从士”,致使社会整体财富下降,造成明清时期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关注重农抑商政策主观动机与客观现实的背离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遇到主观和客观,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每项政策的制定都希望主观动机能在实践中获得良好的客观效果。但是,实际上却并不能尽如人意,[10]因为历史发展进程是立体而复杂的,社会状态是千变万变的,政策实施是有预期的,但政策实施的实践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11]
“重农抑商”作为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因其涉及朝代、地区、社会群体较多,更会呈现出“主观动机”与“客观现实”相背离的现象。如汉代官方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但仍出现商人“假二千石(官员级别)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甚至“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矣”等历史现象,[12]清朝作为“重农抑商”政策实施得最为严苛的朝代,区域性商人群体却逐渐壮大,“山右(今山西)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13]
当国家过分重视农业、采取固守农业的政策,也滋长小农意识和闭关自守政策倾向,使得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影响到整个社会。“丑妻薄地破棉袄”的意识长期存在,逐渐使得整个社会充满小富即安、安于现状的氛围。当明清时期的统治者刻意通过“农贵商贱”来调节农商从业比例,使农业容纳过多的劳动力;“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使得商业资本向土地资本转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施行,割裂了商人、资本和农民之间的联系,这样农民还是农民,商人还是商人,农民无法转换成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的近代意义上的工人,而商人尤其是手中有大量资本的商人更无法转换成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继而影响中国向近代迈进。
当我们将重农抑商这一跨阶段历史概念进行全面总结的时候,我们发现,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重农抑商呈现出一贯性与差异性特点。重农是一以贯之、抑商则一直有“抑商”和“重商”的争议,私商和官商政策的差异。从时空发展来看,重农抑商是古代社会占主导的经济政策,早期抑商主要通过严格的坊市制度,明清时期,政府开始逐渐强化对重要海关、港口、边镇等地的商业管理。从农民、农业、商人、商业与国家的关系来探讨重农抑商政策,可以发现重农抑商这一历史概念的立体化和复杂性。任何一项制度、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发生变化,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呈现“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相背离的现象。
【注释】
[1] 周惠懋:《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一贯性与差异性的分析研究》,《东方企业文化》2013年第24期。
[2] [秦]商鞅著,石磊译:《商君书·农战》,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47页。
[3][7][12] [汉]班固:《汉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7—164页。
[4] [德]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9页。
[5] [德]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8页。
[6] [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74页。
[8]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1页。
[9]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19页。
[10] 冯卓然:《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11] 孟聚:《论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兼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3期。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