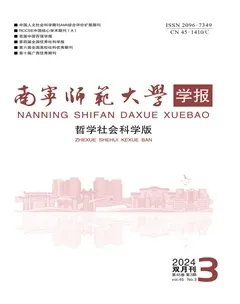天人之际:童年游戏的位置
[摘 要]童年游戏在人生历程的位置,不仅关涉儿童游戏的质量,也关乎游戏、学习各自独立地位的实现。文章从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出发,以天人之际为思想前提,审视童年游戏无位置的现实困惑,确立“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分析框架,围绕想象思想工作的核心要素,即“有我”与“忘我”共在、虚拟、惊异,以及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进行剖析论证。若以原始天人合一为思想前提,不讲“有我”之理性,则会沉溺于“无我”,不存在虚拟和惊异,造成童年游戏位置虚幻的结果。若以主客二分为思想前提,贬低想象忽视“忘我”,则会视游戏为实现“有我”之理性的手段,仅追求恒常在场的虚拟,只重视理性惊异,童年游戏只能获得虚假的位置。唯有以天人之际为思想前提,童年游戏才能生动展现想象的核心要素,精准表现出“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框架,从而实现童年游戏于人生历程的真实位置。
[关键词]天人之际;童年游戏;想象;在场;不在场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349(2024)03-0170-12
从个体一生发展而言,游戏不仅与人终身相伴,且高频率出现在学前教育阶段。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论,游戏是人与世界关系真实本质的现实表现[1]21-25,它将人引向人与世界本源意义的境域[2]72。当人徜徉于人与世界本源意义的境域时,就达到了精神意识发展的审美境界[3]。审美境界是冯友兰先生所指的天地境界,作为人生最高境界,它超越并包括了欲求、求实、道德这三个层次[4]77。审美境界因此成为教育目的的终极诉求。“一个人早期所受的教育与生活经历是审美境界形成的重要基础”[4]76,童年期高频率出现的游戏活动,不仅将儿童引向人与世界本源意义的境域,也是个体直抵审美境界的心灵坦途。因此,无论从人生时间历程来看,还是从个体空间活动而言,游戏应享有最崇高的地位,这种崇高由其在人生历程所占据的真实位置而体现。从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而论,过往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受限于所依据的思想前提,而未能确保童年游戏位置的真实性。前提真实是结论真实的重要条件[5]55,天人之际作为人与世界关系真实本质的准确表达,是确立童年游戏真实位置而必然选择的真实前提。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视角
如果不考虑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不进行人生终极意义的审美追求,童年游戏实践与理论研究确实取得了有效的经验与丰硕的成果,游戏似乎也获得了其应有的位置。然而,当将目光转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这一本体论层次,来审视童年游戏的位置时,游戏无位置的实践困惑与理论拘囿,便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
(一)童年游戏无位置的现实困惑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出了儿童有游戏权,我国各类学前教育文件也强调要保障儿童的游戏权。游戏权虽保障了儿童游戏发生的可能,却难以承诺儿童游戏的质量。在此情况下,高质量游戏近乎缺席的事实,坚定了世人抱持童年游戏无位置的信念,并由此催生了童年游戏无位置的诸多现象。实践中,在“休闲、娱乐”游戏观的指引下,侵占儿童游戏时间与空间、吝啬提供游戏材料、随意投放游戏材料、限制儿童玩法等状况时有发生。有研究者推崇游戏对儿童学习的价值,重视儿童在游戏中展现的自主性[6],产出了“教学游戏化”[7]337和“课程游戏化”[8]的概念,形成了“游戏是一种学习”[9]8的呼声;另有研究者强调游戏对个体成为自由人、理性人的价值[9]9-10,看重游戏对儿童创造力的培养[10],产出了“游戏课程化”[11]的幼儿园课程模式。然而,丰硕的理论成果难以改变游戏无位置的困境。正如“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的不同,只是“从课程到课程”与“从游戏到课程”之间的差异[12],游戏并未脱离手段的命运,实现其在人生历程的真实位置。从教育实践来看,不重视对游戏的理性认识,不突出人的主体性,容易造成侵占儿童游戏时间与空间、游戏质量不高的事实。从理论研究来看,过度关注游戏的价值而非游戏的本质,以“自由、学习”理解游戏,容易造成“游戏极端承载(深度)学习功能”[13]的结果。虽有学者呼吁“要抓住游戏自由、休闲的本质,避免游戏的‘泛化’‘捧杀’游戏本身”[14],却未能突破童年游戏无真实位置的困境。因其所言“自由、休闲”并非游戏的真实本质,只是游戏的价值与特征。
游戏不仅体现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还能将人引向人与世界本源意义的境域,引导个体直抵人生审美境界,超出了“休闲、娱乐”“自由、学习”能定义的范畴。从“休闲、娱乐”理解游戏的本质,缺少对游戏的理性认识,不彰显“有我”的独立人格,落入原始天人合一的思想困境。以“自由、学习”来理解游戏的本质,虽然能认识到游戏对个体发展的价值,但容易将游戏视作个体学习发展、自由追求的手段,从而陷入“主客二分”的思想困境。作为个体精神意识发展的两个阶段,原始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虽属于人与世界关系的范畴,却不是人与世界关系真实本质的准确表达[15]52-57。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思考与行动的大前提,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进行思考与行动,而不思考这“思考与行动”所依据的大前提是否真实[15]158。正如人们理解游戏、支持儿童游戏,虽然会依据理论、经验进行思考与行动,但不考虑理论、经验产生于何种思想前提,亦不思考该前提的真实性。只有前提真实,结论才能保真[5]43。游戏是人与世界关系真实本质的现实表现[16]150-165,以不是人与世界关系真实本质的原始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作为思考童年游戏位置的前提,必然造成童年游戏位置虚幻、虚假的现实。
(二)天人之际作为思想前提的分析框架
确立童年游戏的真实位置,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为前提。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2]40-59,其现实活动有游戏、艺术、诗、节庆[1]11-20。从人类思想史、个体精神意识发展来看,人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原始天人合一、主客二分和高级天人合一这三个阶段[4]19。以原始天人合一为前提,不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不强调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推崇“有我”的独立人格,尚不能清楚区分在场与不在场,故所谓的共同出场无非是主客不分的原始合一[4]19。以主客二分为前提,人将自己置于世界之外,企图通过绝对理性追寻世界“是什么”,进而消除差异达到普遍同一性,实现的只是此在场与彼在场的共同出场[4]20,141。“以高级天人合一为前提,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将想象置于思想工作的首位,清晰区分在场与不在场,突出‘有我’崇尚‘忘我’,真正实现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4]20,143。可见,唯有高级天人合一才是人与世界关系真实本质的准确表达[4]176。高级天人合一可理解为张世英先生所言的“万有相通”,“万有相通”指出审美境界是人生最高境界,论证了“有我”的重要性,但对游戏讨论较少。高级天人合一也可理解为西方哲学所讲的“主客融合”,“主客融合”虽论证游戏,但没有明确讨论人生境界,“有我”也不是其论述的重点。互通“万有相通”“主客融合”的思想,结合心理学有关“有(自)我”独立人格的研究,故本文拟采用“天人之际”作为论证童年游戏位置的思想前提。
天人之际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7]5166。《史记》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指引人在天人古今的时空跨越中思考人该怎样生活在世[18]。人生怎样在世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真实本质的拷问,“天人古今的时空跨越”蕴含着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框架[4]277,“成一家之言”意在彰显独立人格、个体理性,弘扬自我肯定、自觉担当的精神意识[19]。张世英认为,司马迁通过《史记》把个人的思想、品格,提升到崇高的审美境界[20]32。他综观司马迁其人、其志、其著,认为其所言天人之际,具有表述人与世界关系真实本质的广泛容量。作为论证童年游戏位置的真实前提,天人之际具有如下内涵:其一,审美境界是个体精神意识发展的最高境界,它超越并包括欲求、求实、道德境界[21]。其二,“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既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也是把握游戏本质从而论证童年游戏位置的重要依据。其三,把想象置于思想工作的首位,通过想象实现“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22]。在场指当前呈现或当前呈现的东西之意,即出席或出席的东西。不在场指未呈现在当前或缺席之意[23]69-70。其四,实现“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想象包含四个要素,即“有我”与“忘我”共在[4]371,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虚拟[24]19,理性惊异和超理性惊异持续出现[4]136,以及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25]。确立童年游戏在人生历程的真实位置,旨在高扬儿童真实游戏必然发生的思想前提,同时也为儿童的游戏与学习获得各自独立地位,提供些许理论探索。如此,以天人之际为前提,既要证明在原始天人合一、主客二分思想前提下童年游戏位置的虚幻、虚假,也要推理“天人之际”思想前提下童年游戏位置的真实。
二、童年游戏位置的虚幻与原始天人合一
如以休闲、娱乐把握游戏本质,会造成童年游戏位置的虚幻,其根源在于将原始天人合一作为思想前提。原始天人合一只是人类童年期、个体童年期的精神意识水平,它既不是个体精神意识发展的高级阶段,也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部,更谈不上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原始天人合一不注重发挥主体性,不强调人对游戏的理性认识,不推崇“有我”的独立人格,不能清楚区分在场与不在场,所谓共同出场无非是主客不分的原始合一状态。
(一)童年游戏位置虚幻的哲思拘囿
人在原始天人合一阶段,自始就处于与世界沟通的活动中,但这些活动以“行”而不是以“知”为主导[4]19。以“行”为主导的人与世界的相通,缺少明确的主客区分,不重视区分“我”与外在,不张扬个体理性,如此相通感受多而认识少[4]365。从“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来看,以原始天人合一为思想前提,“行”多“知”少,甚至尚“行”弃“知”,将人淹没于自然、人伦,既缺少对在场、不在场的清晰理性认识,也无所谓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26]16-39。“不突出自我存在,笃信首领、巫师沟通天地的权利和能力,缺乏自我沟通天地的信念和意识,不注重探究客观事物规律,将神灵精怪与人生活相互渗透,对广宇长宙时空网络视而不见。”[27]271以原始天人合一为思想前提,不重视个体“我”之理性,把自我湮没于自然、人伦中,造成“无我”1的局面。因此,既不存在“有我”,也无所谓“有我”与“忘我”的共在,这是原始天人合一无法实现“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根本原因。
所谓湮没于自然,指不注重对游戏的理性认识,以感性经验代替理性认知,比如以“休闲娱乐”理解游戏。这为人们敷衍儿童游戏,进而限制儿童“有我”提供了依据。现实中,教师压缩儿童游戏时间、关闭儿童部分游戏空间、吝啬提供游戏材料的现象时有发生。诸如此类现象容易造成一部分儿童漫无目的等待时间,一部分儿童破坏规则以彰显“自我”。漫无目的等待导致“无我”,破坏规则彰显“自我”虽然是儿童对“无我”的抗争,但又会遭遇教师对其游戏时空、游戏材料的进一步剥夺。如此教育经历既不能培养儿童“有我”的意识,也不能培养儿童“忘我”的胸怀,更不存在指引儿童抵达审美境界的可能。教师因不注重对游戏的理性认识,就容易将自己和儿童陷入“无我”的困境。所谓湮没于人伦,指不提倡个体的独立显现,而是以个人所属社会群体之“我们”占优先地位,此种“自我”是互倚型自我,即头脑在什么东西里的思维结构[28]16。无我的价值伦理体系积淀成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大脑进而发展出特殊的机制(如同某些脑区专门负责行走、谈话一样),指引人自觉地选择互倚型自我而放弃独立型自我,以应付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29]。试举儿童反向滑滑梯(沿坡道而上)为例,大多数幼儿园向来禁止儿童反向玩滑梯,理由是容易带来上下冲撞的危险。从儿童发展来看,反向玩滑梯亦有重要价值,教师有责任支持儿童此种非常规玩法。所谓的危险来自游戏方向的不一致,教师只需通过有效机制统一儿童游戏的方向,就可以消除危险。然而事实却是,一旦儿童反向玩滑梯,教师往往立即制止,而非思考如何支持儿童。虽然不乏教师愿意支持儿童非常规玩法,但是当自我理性认知与“园长说”“专家说”“大家说”有分歧时,终因湮没自我的文化心理结构,而放弃支持儿童反向玩滑梯。以原始天人合一为思想前提,不重视人的理性与不彰显独立自我,共同造成童年游戏“无我”的局面。
(二)童年游戏位置虚幻的具体表现
从实现“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想象工作四要素来看,原始天人合一思想观照下的“游戏”,表现出的是无我、虚幻、感性惊异、逻辑偶然性,“游戏”不再是游戏,亦无法实现其在人生历程的真实位置。无我不讲“我”之理性,由于其还未达到“有我”的层次,所以无我不是“忘我”。游戏中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虚拟要靠“有我”与“忘我”的共在来实现,缺少“有我”之理性只能是虚幻,而不是虚拟。“有我”指有自我,自我知觉形成于个体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体验中[28]251。大约从2岁开始,婴儿能够知觉自我,但2~3岁儿童的自我还局限在现在之内[30]439。2岁的婴童会捡心仪的树叶给他人,期待别人参与他的游戏。但他不能同时知觉“过去的捡树叶”与“现在的送树叶”,也做不到把期望他人参与“未来树叶游戏”一起知觉,这是2岁儿童不能清楚表达“我知道我在游戏”的关键原因[28]250。一个尚不能宣告“我知道我在游戏”的儿童,其行为局限于“现在”,他无法构筑起“过去的捡树叶—现在的送树叶—未来的游树叶”之间的虚拟,所能体验到的只是虚幻。其行为所表现的惊异,往往是对材料(树叶)的瞬间感知,类似在某一瞬间意识到某物(树叶)好玩,而瞬间的感性惊异不能让行为持续,也就形不成游戏。诚然,儿童游戏偶尔也会出现符合逻辑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正巧”遇见的行为,其游戏进展的逻辑偶然性远多于必然性。
儿童大约2岁半过后,就具备了虚拟的能力,逐渐能构筑起时间距离较短的事物之间的虚拟,可以实现在场“我”“树叶”,与不在场的动画形象“花园宝宝”“飞飞鱼”的共同出场。他们挥动树叶,向他人或自我宣告“花园宝宝坐着飞飞鱼去旅行”。但游戏很快会随着在场事物的变化而终止,儿童从“有我”对树叶想象之境,瞬间进入新事物的“无我”之境,此种现象常见于2.5~3岁儿童的游戏场景。这意味着,儿童3岁以前的游戏行为,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游戏。这类行为正是人们所说的“休闲娱乐”。也正是这类行为的高频出现,塑造了人们“休闲娱乐”的游戏观,形成将原始天人合一作为前提的思想倾向。相较于主客二分、高级天人合一,学前儿童的精神意识更接近原始天人合一。尽管儿童3岁后的游戏行为飞速发展,“有我”与“忘我”的共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虚拟、理性惊异和超理性惊异以及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逐渐出现在儿童的游戏中,但是由于缺少成人的积极支持,原始天人合一思想观照下的游戏,容易成为儿童游戏的主要组成部分。教师因不重视对游戏的理性认识,随意缩减游戏时间,限制开放游戏区域,造成儿童“无我”境况;在桌面游戏时间提供数量极少的材料,区域游戏时间提供杂乱无序材料,既限制了儿童虚拟的时空跨度,也阻隔了儿童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正是因为教师以原始天人合一为思想前提理解儿童游戏、消极支持儿童游戏,加之学前儿童精神意识的近原始天人合一性,造成儿童游戏呈现出无我、虚幻、感性惊异及逻辑偶然性的事实,进而导致童年游戏位置虚幻的结果。
三、童年游戏位置的虚假与主客二分
如视游戏为突破学习(认知)困境、实现人生自由的手段,则会造成童年游戏位置虚假的事实,其根源在于以主客二分为思想前提。主客二分将“我”置于世界之外,无限推崇人的主体性,只考虑主体、客体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统一,不追求人与世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相通,实现的只是此在场与彼在场的恒常在场,而不是在场与不在场的共同出场[4]102。在主客二分的思想前提下,游戏是通往绝对理性的重要手段[31]483-486。如此,游戏在作为手段的道路上,逐渐迷失自我陷入位置虚假的困境。
(一)童年游戏位置虚假的哲思困境
主客二分属于人与世界关系属性的“主体—客体”结构范畴,它强调人在世界之外,企图通过人的理性消除事物之间的差异性,达到超出时间之外的概念普遍性,实现此在场与彼在场的恒常在场[15]48-53。然而,人生最高意义与价值却是,人在有时间性的现实世界中,通过想象实现“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4]113。主客二分无限推崇理性而贬低想象,追求超出时间之外的概念普遍性,以恒常在场压制不在场,实现的只是此在场与彼在场的恒常在场[4]45。以主客二分为思想前提,极端强调“有我”而丝毫不考虑“忘我”,这是主客二分无法实现“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根本原因。所谓极端强调“有我”指,无限推崇人的理性,将主体与客体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统一,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最高追求[4]58。主客二分认为人的自我实现先后经历感性、知性、理性三个阶段[31]482-483,游戏因其更接近知性而尚未达到理性[32]72-75,所以它不属于人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虽然主客二分宣扬“人首先是游戏者而后是理性者”[33]5,25,211,但其意在表达,游戏是人达到最高层次的必经阶段与重要手段,人只有先成为游戏人,才可能成为超出时间之外的理性人[32]72,256-264。主客二分如此崇尚理性,以至于黑格尔彻底离开“人—世界”结构进入“主体—客体”结构,将人推向绝对主体的地位,最终把人抛出世界之外[26]135,造成人现实生活世界的虚假与苍白。以主客二分为思想前提,视游戏为儿童完善理性的重要手段,追求恒常在场的概念普遍性,容易造成只关注儿童对概念的掌握,而不关心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
不重视游戏的持续推进,不关心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只关注儿童对概念的掌握,是主客二分只讲“有我”不屑“忘我”的具体表现。主客二分不讲“忘我”的根源在于崇尚理性思维贬低想象。在主客二分的思想框架中,想象长期被压制于理性思维之下。旧形而上学认为,想象是意识对原本外在感性元素的模仿,人到达彼岸世界要诉诸理性思维而非想象。康德认为,想象是在直观中再现一个本身并未出场的对象的能力,想象与知性联系产生游戏,与理性联系形成道德,实现了道德自由,人才能达到理性的最高层次[32]72。黑格尔进一步强调,想象力只是介于感性直观和理性思维之间,还不能形成统一的自我关联[34]51。可以看出,以主客二分为思想前提,想象不可能超越理性。而不将想象置于思想工作的首位,便不能让我之理性飞离在场,进而实现将不在场纳入思想工作范畴的可能。也就不存在“忘我”的体验,缺少“忘我”,也无所谓“有我”与“忘我”的共在,最终实现的只是此在场与彼在场的恒常在场,而不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以滑滑梯为例,在主客二分看来,儿童滑滑梯时进行的“金鱼冲浪”“猴子捞月”等想象,仅限于感性知性的经验层次,并未达到理性概念层次。因此,在支持儿童滑滑梯时,应以诸如“速度”“摩擦力”等概念的追求为最高目标。主客二分不能理解,滑滑梯时,痴迷于“金鱼冲浪”“猴子捞月”等想象的儿童,已经超越了“速度”“摩擦力”等概念的理性思维层次。一个在滑滑梯时,能根据想象情节需要来调整摩擦力掌控速度的儿童,不仅拥有对速度、摩擦力的感知经验,而且还形成了关于速度、摩擦力的知识,他缺少的不过是关于“速度”“摩擦力”的词语。将词语概念的掌握作为儿童滑滑梯游戏的最高目标,贬斥儿童滑滑梯时的想象,对儿童“忘我”的体验置若罔闻,视游戏为儿童理性完善的必经路径与重要手段,造成儿童游戏世界的苍白与虚假。
(二)童年游戏位置虚假的现实体现
主客二分崇尚思维贬斥想象,在主客二分的思想前提下,游戏表现出的是,极端强调“有我”,只考虑恒常在场的虚拟,只讲理性惊异与概念逻辑。极端强调“有我”,既是在场与不在场不能共同出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主客二分思想前提下,成人支持儿童游戏的价值诉求。无论在幼儿园还是在家庭,人们要求游戏服务于儿童理性完善的现象并不少见。幼儿园将游戏目标定位于课程构建的起点而非游戏本身的进展,把游戏作为课程实施、儿童学习的手段,与非智育类玩具相比,家庭购买智育类玩具的意愿更强烈,诸如此类均是“有我”理性至上的具体表现。主客二分极端强调“有我”,执着追求超出时间之外的概念普遍性,因此不可能给人留出有时间性的不在场的想象空间[23]71,实现的只是恒常在场的虚拟。虚拟就是超越现实,超越意指从现实出发而又多于现实,虚拟是肯定现实中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的意义和真实性[24]14。人不仅可以虚拟合概念逻辑而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如“绝对的圆”,还可以虚拟不合概念逻辑但在现实中能被领悟的东西,如“方形的圆”[24]17。前者虚拟靠思维,后者虚拟靠想象。在有时间性的现实世界里没有绝对同一性,如没有绝对的圆,这些绝对同一的概念是人们在生活实践基础上所做的理想设定。这种理想设定以时空中具体特殊的东西为基础,但多于和高于时空中具体特殊的东西,这多于和高于之处就在于人的虚拟[25]。以主客二分为思想前提,游戏中的虚拟显然是,由思维实现的合概念逻辑的理想设定,而这虚拟之物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由这种虚拟实现的是此在场与彼在场的恒常在场。
儿童游戏若以恒常在场为最高目标,则会陷入执着概念逻辑的困境。执着于概念逻辑的结果是,滑滑梯时追求对“速度”“摩擦力”等概念的理解,商店角色游戏时努力解决“数量关系”“加减运算”等问题。当儿童游戏被要求感知学习概念时,儿童必须充分发挥理性极端突出“有我”,而不能让“我”之理性飞离在场,进入到同样在有时间性的现实世界中的不在场的境遇。儿童滑滑梯只有苍白无意义的动作体验,而没有从坡顶到坡底的“时间经过”1中,所进行的“金鱼冲浪”“猴子捞月”这“有我”与“忘我”共在的想象体验。商店游戏也只是儿童重复眼前生活时空的购物行为,而不存在越出眼前时空限制的跨时空行为,类似于不存在以“殷人”“唐人”“外星人”等为角色的购物游戏。缺少不在场的境域,只能体验理性惊异。惊异是刚刚惊醒的状态,既包括从不分主客到区分主客这一“中间状态”的惊异,也包括从主客二分到超主客二分“中间状态”激起的惊异。前一阶段的惊异使人见到一个新世界,后一阶段的惊异使人创造一个新世界[35]。见到一个新世界属于理性惊异,创造一个新世界属于超理性惊异。如“绝对的圆”突出的是人从主客不分(未建立起圆的概念),到主客二分(能理解圆概念之下的不同的圆)的理性惊异,属于见到一个新世界。而“方形的圆”突出的是从主客二分(能理解方和圆的概念),到超主客二分(超越方和圆的概念逻辑限制,用以表达人心灵深处最真实的东西)[24]17。只追求理性惊异的游戏,执着于概念逻辑,它属于儿童的学习范畴而非游戏,游戏注定沦为学习的手段。主客二分视游戏为手段,终究造成童年游戏位置虚假的事实。
四、童年游戏位置的真实与天人之际
如突破童年游戏位置虚幻、虚假的困境,则需要以天人之际为思想前提。天人之际将想象放在思想工作的首位,重视“有我”与“忘我”的共在,追求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虚拟,以超理性惊异为目标同时关注理性惊异,超越概念逻辑重视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由此准确展现了“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框架。在天人之际的思想前提下,游戏将人引向人与世界本源意义的境域,见出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从而实现游戏在人生历程的真实位置。
(一)童年游戏位置真实的哲思高扬
天人之际属于人与世界关系属性的“人—世界”结构范畴,是个体精神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强调人在世界之中。“但这并不是教人们盯住在场的东西不要超越,也不是让人从此一具体物转向彼一具体物,而是要人们通过想象,超越到事物所‘隐蔽’于其中的无穷无尽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共在之中。”[4]47天人之际重视在场而突出“有我”,崇尚不在场而需要“忘我”,是“有我”与“忘我”的共在,成就了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并由此彰显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本质[2]121,实现人生的最高意义与价值,达到审美境界。天人之际实现的共同出场,不是主客二分超出时间之外的此在场与彼在场的恒常在场,而是有时间性的现实世界中在场与不在场的共同出场。实现共同出场的心理活动是想象而不是思维,想象能达到思维所达不到的可能,思维的极限正是想象的起点[4]46,是想象使人回到现实,指引人从宇宙整体内部体验到有我与忘我共在的境界,实现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4]176。想象这一心理活动,既要求彰显“有我”的理性思维,也要求我之理性飞离在场达到瞬间的“忘我”。想象如果不包含理性思维,则有回到“无我”的风险;如果不超过理性思维,则无法让“我”之理性飞离在场达到瞬间的“忘我”。正是“有我”与“忘我”的共在,不仅指引人清晰区分在场与不在场,还教人脱离恒常在场的困境,最终实现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
在天人之际的思想前提下,儿童按游戏所隶属的活动秩序,既向自我提出游戏进展任务,又让理性越出自我,像观众那样欣赏任务的推进[16]158。一个乐此不疲玩球的孩子,能够在球落地前后的短暂时间内,实现在场与不在场的共同出场。在球落地之前,手中的球和对球弹跳次数的估计属于在场,而尚未弹跳的球及其弹跳事实次数属于不在场。当球落地后,球的事实弹跳及其次数转变为在场,而之前的估计则成为不在场。当他估计球可以弹25次,如果只弹了10次就滚跑了,他会失望,但倘若弹了30次,他会骄傲得像个国王[1]22。若是球恰好弹了25次,他神气得就像同宇宙一起旋荡的神仙。只不过有了30次的弹跳经历,在之后的游戏中,他会选择估计30次甚至更多,以期待在稍长的时间跨度中,体验这“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可见,一个乐此不疲游戏着的儿童,不仅能够清晰意识到在场、不在场,还可以让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出场。诚然,作为个体精神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天人之际,也讲欲念、功用、声色、理性,但绝不拘囿于此[36]23。但一个以审美境界为主导的人,即便缺少游戏材料,他仍然有办法令自己沉浸在游戏中。对一个“会玩儿”的儿童而言,他不太容易被游戏材料所限制,而一个“不会玩儿”的儿童常常将自己拘囿于游戏材料。以天人之际为思想前提分析儿童游戏,可以发现,沉迷于玩球的儿童,球的美丑、弹力优劣,以及对球弹跳次数的估计,均是其关注和在意之处。但是,儿童游戏的进展并不拘囿于上述因素,这些因素也不是儿童沉迷玩球的重要条件。一颗不好看的球,一颗弹力不好的球,以及不准确的次数估计,丝毫不影响儿童沉迷于游戏,沉浸在这“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中。那些手上有球的儿童,执意要抢他人的球,原因在于他从未脱离眼前在场而进入游戏情境,这类儿童对游戏进展的推进,往往受限于欲念、功用、声色、理性等在场的东西。一个有能力进入游戏情境的孩子,无暇关注他人及其手中的球,除非这个孩子没有球。即便如此,他仍然可以用一颗石头或别的材料,实现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正是天人之际将想象置于思想工作的首位,指引儿童不仅彰显个体理性,而且关注自我体验,进而挣脱恒常在场,让儿童伸展到自身以外,实现了“有我”与“忘我”的共在。并由此展开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的美好画卷,实现游戏在人生历程的真实位置。
(二)童年游戏位置真实的生动写照
以天人之际为思想前提,儿童游戏表现出的是“有我”与“忘我”的共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虚拟,崇尚超理性惊异且包括理性惊异,按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而非概念逻辑推进游戏。这是童年游戏获得真实位置的生动写照。有关“有我”与“忘我”的共在,前述内容已做了较为充分的讨论,本部分内容重点阐释其他三个要素。天人之际思想前提下的虚拟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它旨在肯定现实中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的意义和真实性。游戏者通过虚拟悬置在场事物的概念“之所是”,让无穷多“不在场”的事物,合逻辑必然性地与在场事物共同出场[22]。而这不在场事物的出场,需要在场的东西赋予它形体(embodiment),它要找到自己的“化身”[23]。例如,儿童用木棍玩骑马游戏,木棍既是在场物的概念所是,也是不在场的马之“化身”。此“化身”是人和物交融合一的产物,没有人对木棍的想象,就无所谓马的“化身”。可以说,“化身”即玩具,其本身既有现实性也有虚拟性。当儿童将木棍视作马的“化身”时,木棍飞离在场的概念所是,扑向不在场的马,让马与自己共同出场,由此玩具诞生。在玩具诞生的瞬间,实现了在场与不在场共同出场的超理性惊异。上述骑马游戏中,儿童从“看,这是木棍”到“看,我的小马”,所展现的便是从理性惊异到超理性惊异的变化[35]。理性惊异使儿童看见了木棍之所是,超理性惊异令儿童发现了马的“化身”,并据此拉开游戏的帷幕。在超理性惊异中,最平常的事物通过与游戏者照面进而以新的存在方式崭露[37],如此才有木棍和马这在概念逻辑上不具有同一性的个别物,在不同而相通的唯一世界中的共同出场[36]21。
诚然,游戏不是止步于“看,我的小马”,它要向前持续推进。游戏的持续推进,离不开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包括材料的秩序和朝向一个结果的活动秩序[38]。一些不能持续沉浸在游戏情境中的儿童,或表现为没能把握特定结果的活动秩序,或表现在未能掌握材料的秩序。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不同于现实事件的逻辑必然性。比如,打针游戏中“痛苦的快乐”,如果单从打针这一事件而论,儿童不可能在被打针的过程中,同时有痛苦与快乐两种情绪体验,它不合逻辑。但在打针游戏这一特定情境中,假想的被打针痛苦体验,与真实的游戏快乐体验共同出场,却是合乎逻辑必然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打针游戏呈现的痛苦和快乐,共同指向被打针一事。而平常人们所说“不经历痛苦如何见彩虹”,其中痛苦指向当下之事,快乐指向未来之谋,并非同一事物。打针游戏的痛苦和快乐,是“有我”与“忘我”共在的美好体验,其展现的是虚拟、超理性惊异、游戏进展的逻辑必然性,实现的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持续共同出场。“不经历痛苦如何见彩虹”,是坚持绝对“有我”之理性思维的极端表现,其展现的是恒常在场的虚拟、概念逻辑、理性惊异,实现的仅仅是此在场与彼在场的共同出场。总体来看,在天人之际的思想前提下,游戏生动体现了想象工作的四要素,精准地展现了“在场与不在场持续共同出场”的框架,实现了童年游戏于人生历程的真实位置。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指引人抵达天地境界,一个以天地境界为主导的人,其精神意识发展也达到了天人之际阶段。人不是只在成年后的生活磨砺中领悟天人之际,而是早在童年期的游戏中,就已有天人之际的体验。从儿童立场来看,游戏属于天人之际阶段之事,目标在于,运用想象实现超理性惊异让游戏持续进展;学习属于主客二分阶段之事,目标在于,运用思维消除理性惊异从而结束学习;儿童休闲消遣谈不上有目标,属原始天人合一阶段之事。儿童精神意识接近原始天人合一,他们渴望脱离“无我”,彰显“有我”进而崇尚“忘我”,因此痴迷游戏、乐意学习,却唯独对消遣不甚积极。以主客二分为思想前提研究游戏,既容易造成视游戏为儿童学习手段的事实,也容易导致游戏与学习缺失各自独立地位的结果,从而将儿童陷入既难以真实游戏也不能敞开学习的困境。希望在天人之际思想前提下对童年游戏位置的论证,不仅可以实现游戏在人生历程的真实位置,也能够为儿童游戏与学习各自独立地位的获得,提供些许有意义的理论探索。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艺术作为游戏、象征和节庆[M].郑湧,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 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3] 张世英.希望哲学论要[N].人民日报,2013-07-18(7).
[4]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 陈波.逻辑学十五讲[M].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 刘焱.也谈幼儿园游戏与课程[J].学前教育,2021(10):4-13.
[7] 刘焱.儿童游戏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虞永平.课程游戏化的意义和实施路径[J].早期教育(教师版),2015(3):4-7.
[9] 黄进.体验为本的游戏:再论游戏是一种学习[J].学前教育研究,2003(6):8-11.
[10] 王小英.“无为而为”的游戏活动与幼儿创造力的发展[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49-154.
[11] 王振宇.论游戏课程化[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18(4):3-8.
[12] 黄小莲.“课程游戏化”还是“游戏课程化”:命题背后的价值取向[J].中国教育学刊,2019(12):57-61.
[13] 黄进,贺刚.儿童游戏的理论化及其意义裂变:基于概念史方法的考察[J].学前教育研究,2023(12):1 -13.
[14] 黎勇.幼儿园课程的游戏转向及其实践限度[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23):42-45.
[15] 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7]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孙晓,主持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18] 向晋卫.“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新论[J].兰州学刊,2019(8):30-37.
[19] 郭院林.试论司马迁以道统抗衡政统的精英意识:以《史记》项羽形象为中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09-116.
[20] 张世英.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1] 张世英.美与真善[J].学海,2000(1):12-17.
[22] 张世英.超越在场的东西:兼论想象[J].江海学刊,1996(4):69-74.
[23] 张世英.审美意识:超越有限[J].北京大学学报,2000(1):68-73.
[24] 张世英.现实·真实·虚拟[J].江海学刊,2003(1).
[25] 张世英.相同·相似·相通:关于“共相”本体论地位问题新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47-53.
[26]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7]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8] 朱滢.文化与自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9] HEATHERTON T F,MACRAE C N,KELLEY W M. What the social brain sciences can tell us about the self[J]. Current direction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4(5):190-193.
[30] SHAFFER D R.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M].第6版.邹泓,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3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2]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3] 约翰胡伊青加.人:游戏者[M].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34] 黑格尔.美学: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35] 张世英.谈惊异(Wonder):哲学的开端与目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36-41.
[36] 张世英.审美意识的三重超越:再论美在自由[J].哲学分析,2011(3).
[3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节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98-201.
[38] 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22.
[责任编辑:玉 璐]
1敷衍、限制儿童游戏,即限制儿童通过“我”之主体认识客体,从而将儿童湮没于“无我”状态。
1伽达默尔认为,人在游戏中追寻的是时间经过,在经过的时间里展现“在场与不在场的共同出场”。儿童从坡顶到坡底的瞬间,是充满期待与回忆的时间。起先在场随后不在场的坡顶,与起先不在场随后在场的坡底,共同被儿童回忆与期待。在坡顶到坡底的时间经过中,儿童运用想象,让“我”滑滑梯与“猴子捞鱼”“金鱼冲浪”共同出场,所带来“有我”与“忘我”共在的体验,便是儿童在这瞬间所期待与回忆之事。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广西壮族、侗族家长儿童观的调查与比较研究”(2021KY0373);广西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基地幼儿园课程改革实践样态与质量保障长效机制研究”(2021ZJY602)
[作者简介]任志楠(1981— ),女,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引用格式]任志楠.天人之际:童年游戏的位置[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3):17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