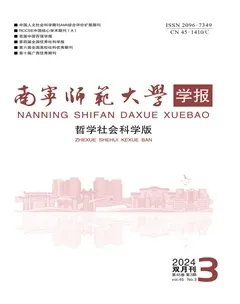防卫不适时的范围界定与限缩
[摘 要]防卫不适时这一概念能够区分防卫行为与单纯的犯罪行为,厘清其范围对于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理论和实务中存在将形式上符合防卫不适时的情形认定为假想防卫或防卫过当的做法,这容易导致防卫不适时与这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因此亟须探寻其背后蕴含的教义学原理,重新廓清防卫不适时的范围。一是结合事实认识错误理论,严格区分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明确假想防卫仅指行为人对不法侵害是否存在产生认识错误而实施“防卫”的情形,而将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时或者已经结束后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而实施“防卫”的情形归入防卫不适时的范围。二是通过完善防卫不适时的内在驱动理念,综观限缩传统通说所认定的防卫不适时范围的必要性,以防卫不适时的特征为对照范本,结合“量的防卫过当”理论,将事中的反击行为与事后的追击行为整体评价为一体化防卫行为的情形排除于事后防卫之外,以限缩防卫不适时的范围。
[关键词]防卫不适时;假想防卫;量的防卫过当;一体化防卫行为;整体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349(2024)03-0130-13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简称“刑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是正当防卫权行使的前提。换言之,只有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使防卫权,方存在减免责任的可能。与之相对,违反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发生在不法侵害开始之前或者不法侵害结束之后的所谓“防卫”行为,刑法理论称其为“防卫不适时”[1]。基于逾越时间限度的行为的产生时间,防卫不适时可分为事前防卫与事后防卫两种形式。刑法学界通说认为,由于防卫前提条件的缺位,行为人不具备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正当动机,因此防卫不适时既不能成立正当防卫,亦不能成立防卫过当;针对防卫不适时,理论通说和实务惯例均以单纯犯罪论处[2]130-132,[3]158-161。由此可见,防卫不适时是行为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一概念能够区分防卫行为与单纯的犯罪行为。
关于防卫不适时的范围界定,除了可从正面定义其概念以划定其范围,还可以通过区分其与假想防卫、防卫过当的关系或界限的方式从侧面明晰其边界。然而,学界对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关系的认定并未达成共识,二者在理论上存在混淆的现象;而且,针对防卫不适时与防卫过当的关系,近年来实务界出现了将形式上符合防卫不适时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行为这一突破惯例的做法,如“涞源反杀案”1、“谭某某故意伤害案”2、“朱邦源故意伤害案”3等。司法机关之所以承认此类情形的防卫性质,是因为考虑到事情的起因是出于防卫,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亢奋、愤怒等可以理解的因素,并且如此认定更能够得到人们在情感上的普遍认同。但是,这与防卫不适时的传统界定范围相抵牾,并且可能导致通说中防卫不适时与防卫过当概念的混淆,由此产生争议。
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层面重新审视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的关系,以明确防卫不适时的边界。面对争议案件,不应仅满足于“就案论案”或“以法说案”,而应进一步从刑法理论的高度进行深入探究。通过研析判例或案例,从中发掘学说讨论的契机,再将讨论成果转化至刑事实务之中,不失为研究范式转变的良策之一[4]。那么,在前述案例中,司法机关将超越防卫时间界限的情形认定为防卫过当的做法,其中所蕴含或者可依据的教义学原理是什么?是否会影响防卫不适时范围的界定?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初,本文先对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防卫过当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
二、防卫不适时与相关概念的混用与辨析
鉴于理论上常通过探究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防卫过当的关系以明晰其边界,本文亦从这两方面来呈现:其一,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需要厘清;其二,防卫不适时与防卫过当之间的界限应如何界定,有待商榷。
(一)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的界线厘定
假想防卫,是指客观上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错误,误认为不法侵害存在,因而实施反击行为的情形[2]129。对防卫不适时和假想防卫关系的认知差别,会影响防卫不适时的范围界定。在界定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的关系上采“交叉重叠说”,是使二者产生混淆的主要原因。此说认为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部分,且此说内部对重叠范围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如有学者认为,防卫不适时存在事前防卫、事后防卫和延长防卫三种表现形式,其中延长防卫是指不法侵害在行为人实施防卫的过程中结束,但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而继续实施防卫的情形,属于假想防卫的一种[5]。另有学者认为,防卫不适时应包括两种情形:其一,“对时的假想防卫”或称“事前、事后的假想防卫”,即行为人将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的不法侵害误认为正在进行,因而实施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其二,事前防卫与事后防卫,即行为人对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均为明知,但仍实施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6]。据此,从“交叉重叠说”的立场出发,至少在行为人于不法侵害结束后,因存在认识错误而实施的“防卫”行为的场合,存在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的混用。
与此相对,“严格区分说”主张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相互独立,应当严格区分,而如何划定二者之间的界线则见解不一。有观点指出:行为人在“明知”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的前提下,仍对对方或原不法侵害人实施损害行为的,属防卫不适时,只能构成故意犯罪;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而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而对对方实施了“防卫”,则属假想防卫,可构成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7]9。可见,这是基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产生认识错误的标准所进行的划分。另有观点认为,防卫不适时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明知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而实施“防卫”的情形;二是不法侵害已经结束,而行为人误以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而实施“防卫”的情形[8]。前者构成故意犯罪,后者可构成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而假想防卫仅指在根本不存在不法侵害的前提下,对不法侵害的存在产生认识错误的情形。简言之,该观点认为,因对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产生认识错误而实施损害他人权益行为的,不是假想防卫,而属防卫不适时的一种[8]180。可见,此观点是以认识错误的具体对象为依据,将假想防卫和因事实认识错误导致的防卫不适时进行了区分。还有观点认为,真正的防卫不适时仅指“事前防卫”,即不法侵害已经存在但未着手实行(预备阶段),行为人提前对不法侵害人采取反击行为的情形,只能构成故意犯罪;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或者误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从而实施损害行为的,可能构成假想防卫[7]10。鉴于此观点认为防卫不适时只能发生在不法侵害已经存在的场合,那么“事后防卫”自然就因丧失了不法侵害存在的前提而被排除在防卫不适时的范围之外。持此观点的学者指出,将防卫不适时限定为“事前防卫”,能够区分防卫不适时与单纯的故意犯罪[7]10。然而基于通说,对防卫不适时本就按照单纯的犯罪进行处理。换言之,此观点中的“事前防卫”实质上也是单纯的故意犯罪,由此便无法做到清晰地区分二者。
纵观前述观点,将行为人对自始不存在的不法侵害产生认识错误而实施“防卫”的情形定为假想防卫,以及将行为人明知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而实施“防卫”的情形定为防卫不适时,在理论上并无太大争议。学界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定性行为人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时因认识错误而实施的“防卫”行为,而这正是廓清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关系的关键所在。解决这一问题,需追溯到正当防卫中的“事实认识错误”。在正当防卫中,是否凡涉及事实认识错误便要归于假想防卫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行为的过程中,其主观上认识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9]。而事实认识错误在正当防卫中表现为对正当防卫前提事实的认识错误。根据产生认识错误的具体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其一,对防卫起因条件,即不法侵害现实存在的认识错误,构成假想防卫;其二,对防卫时间条件,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认识错误,属于防卫不适时;其三,对防卫对象条件,即不法侵害人的认识错误,属于防卫第三人[10]。
实际上,第一种形式构成的假想防卫与第二种形式构成的防卫不适时各自独立,并无重叠。原因在于,假想防卫是在完全不存在不法侵害的前提下产生的,行为人所误认的这一不法侵害过去从未发生,现在也不存在;而对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的认识错误却建立在不法侵害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的基础之上。首先,事前防卫以对方存在不法侵害的预备行为或者某种犯意表示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行为人将不法侵害的预备或犯意表示误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假想防卫。相反,如果对方实质上不存在任何意图加害的举动,行为人以保护法益为由损害对方权益的,无需也不能将其纳入事前防卫的讨论范围;若存在认识错误,则考虑是否成立假想防卫。其次,事后防卫以曾经现实存在不法侵害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而继续实施防卫行为的,也不能成立假想防卫。简言之,“在防卫时间错误中不法侵害并非假想,而是存在的……或者已经过去”[11]。最后,事实认识错误的防卫不适时之所以与假想防卫产生混淆,原因在于部分学者在阐述事实认识错误产生的防卫不适时的处理方式时,往往采用“按照假想防卫的原则处理”[8]145的表述方式。可能他们的意图在于说明对于此类型的防卫不适时也像假想防卫一般,采取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而不是将此类型的防卫不适时等同于假想防卫。
因此,应严格区分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曾现实地存在不法侵害。置言之,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时或者已经结束后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而实施“防卫”的情形,属于防卫不适时;假想防卫则仅指行为人对不法侵害是否存在产生认识错误而实施“防卫”的情形。然而,当前针对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二者关系的厘清往往只是在通说基础上对理论上的混淆作出回应,并未实际影响到通说对防卫不适时存在范围的划定,即只是对通说进行解释,而未改变其实质内涵。若要对通说所划定的防卫不适时进行限缩或者改变,则还需通过理解防卫不适时与防卫过当的关系、划定二者的界线来达成。
(二)防卫不适时与防卫过当的关系界定
防卫过当,是指行为人在实施防卫行为的过程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其成立须以存在与正当防卫同质的防卫行为为前提。由此,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主张,超过防卫时间条件的行为一律不具有防卫性质,不存在成立防卫过当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在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或自动结束侵害的情况下,防卫人的防卫目的已经达到,不再存在现实紧迫的侵害,防卫人就应当停止防卫行为,出于激愤、不满而继续追击原不法侵害人的,构成故意犯罪,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12]。简言之,防卫不适时逾越的是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而防卫过当则是超越了限度条件,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非此即彼的界线。
然而,近年来逐渐活跃的一种见解认为,传统理论为防卫不适时划定的范围过宽,其中一些情形理应构成防卫过当,甚至正当防卫。如有学者主张,当不法侵害结束后的防卫行为与结束前的防卫行为能被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时,不认定为事后防卫,根据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13]266。实务中也存在不少将超过防卫时间条件的情形作为防卫过当处理的实例。如“代某故意伤害案”1:代某行至停车场,见王某站在代父驾驶室外,右手持刀连续两次伸进车窗威逼代父,代父用手抵挡;代某即跑向收费亭,边喊“有人抢劫,快报警”,边捡起一根木棒和半块砖头;代某返回后,将砖块扔在地上,先用木棒朝王某腿部一棒,木棒被打折,紧接着在其胸部一棒;代某捡起砖块,王某后退,代父下车捡起被打折的木棒,二人追打王某;王某边后退边合起手中刀具,此时代某扔砖块击中王某头部,致其后仰倒地死亡。二审法院认定代某在其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后果,其行为属防卫过当。事实上,在代某投掷砖头之前,加害方已经停止攻击行为并在离开现场的途中,其“合起手中刀具”的行为也佐证了这一点。置言之,此时已不存在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因此在这种场合下对原不法侵害人进行追击,按照通说和惯例就不能评价为防卫过当,更不能成立正当防卫,而应认定为防卫不适时。
前已述及,防卫不适时包括事前防卫与事后防卫。其中,事后防卫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第一,不法侵害结束后才实施反击行为;第二,不法侵害持续过程中实施了反击行为,不法侵害结束后继续实施追击行为,即在不法侵害结束前后存在复数的反击行为。学界争议的焦点在于:在第二种情形中,是否存在防卫过当甚至正当防卫的成立空间。第二种情形的性质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是因为通说往往以正当防卫结束的时间为临界点,将事中的正当防卫与事后的不当防卫分离。这其实忽视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在同一案件中并存的事实。笔者认为,在第二种情形中存在成立防卫过当甚至正当防卫的可能,通说所划定的防卫不适时的范围理应被限缩。而在展开限缩防卫不适时范围的路径之前,有必要阐明防卫不适时范围限缩理论建构的必要性。
三、防卫不适时的限缩理念
若要阐明限缩传统防卫不适时范围的必要性,可借助防卫不适时的内在驱动理念。防卫不适时的作用与内在驱动理念之一是为了将防卫行为与单纯的打击报复行为相区别,防止防卫权的滥用和过度扩张。然而,单向度的思考往往会失之偏颇。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有必要对当前只具防止防卫权滥用和过度扩张理念的防卫不适时进行转型,这就需要将适度扩张防卫权的理念纳入考量范围。据此,要达到限缩防卫不适时的目标,就需阐明通说对防卫不适时范围的划定不利于防卫权的适度扩张甚至是正当行使。进言之,需要说明将在不法侵害结束前后实施复数反击行为的情形一律认定为防卫不适时,不当压缩了防卫权的行使空间和行使积极性。
首先,防卫人在面临不法侵害的紧急状态下,容易产生恐惧、紧张等情绪,加之不法侵害的结束经常只在一瞬间,因而在防卫人看来,不法侵害的暂时中断与彻底结束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然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更不能因为遭受了不法侵害就忽视了防卫人可能存在的错误判断”[14]102。换言之,对防卫时间要件的判断应当是客观的,不能受防卫人辨认能力的影响。由此,如果机械地将超越时间界限的部分分割为事后防卫,容易造成“防卫时间的精确性与防卫人难以把握之间的紧张关系”[14]103。虽然理论上认为对此可以考虑被害人存在过错,在量刑时对行为人酌情从轻处理,但这与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律效果有较大区别,可能会严重打击防卫人行使防卫权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然而,在具体案件中必须考虑防卫人动摇的心理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由不法侵害人实施侵害所引起的,并非防卫人自己的选择。面对紧迫的不法侵害,防卫人被动产生的恐惧、激动等情绪和动摇的心理状态很难随着不法侵害的结束就戛然而止,反而会持续影响着防卫人。并且,防卫人所实施的连续性反击行为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时空界限,而是像“河水”一般流畅,加之被动形成的极度恐惧、激动等情绪和动摇的心理状态的影响持续存在,要求防卫人在不法侵害结束的瞬间就立时停止防卫行为,不啻强人所难。
其次,不法侵害结束后的追击行为,既存在完全出于报复、不满等心理,对原不法侵害人进行加害的情形,也存在出于认识错误继续实施“防卫”的情形,还存在为防止受到再度侵害而继续追击的情形[15]。有学者主张事后防卫多为报复性的侵害[3]160,但是现实中误认为侵害人仍在实施不法侵害与防止再度侵害的情形并不在少数,因此不能够以偏概全。例如,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但之前由不法侵害所引起的恐惧、紧张等情绪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平复,很可能为“以防被再度侵害”而继续对原不法侵害人加以攻击。此外,主张行为人实施追击行为时夹杂激愤、恼怒或者报复的情绪就否定存在防卫目的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因为即使是发生在时间界限之内的防卫行为,也存在出于保护法益的防卫意思与出于激愤、报复的攻击意思并存的情形,但均不直接否定行为人的防卫动机[16]。此外,该观点也承认在出于认识错误而继续防卫的场合,行为人具备防卫动机。据此,将具备防卫动机的行为与出于单纯报复的行为一同定性为防卫不适时的做法便难言合理性。
最后,与行为人有意地实施过当的防卫行为相比,存在认识错误或受极端情绪影响而实施的追击行为往往要承受更严厉的诘责。例如在“汤某故意杀人案”1中,汤某与杨某系夫妻,杨某经常酒后无故打骂汤某。某日,杨某醉酒后吵骂着进屋,把几块木板放到同院居住的杨某甲、杨某乙父子家的墙脚外。为此,杨某乙和杨某发生争执、拉扯。汤某上前劝阻,杨某即用手中的木棍追打汤某。汤某随手从柴堆上拿起一块柴击打杨某头部左侧,致其倒地。杨某甲劝阻汤某不要再打,汤某因惧怕杨某站起来后殴打自己,仍继续用柴块击打杨某头部数下,致其因钝器击打头部颅脑损伤死亡。法院认为,汤某持柴块将杨某击倒后,不听旁人劝阻,继续击打杨某头部,造成了杨某死亡的严重后果,但鉴于杨某具有重大过错、汤某认罪态度好等因素,对汤某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汤某有期徒刑十年。而在“张某防卫过当案”[3]143-144中,张某在防卫过程中积极追求过当的防卫后果,出于气愤,在用斧头将侵害人李某砍倒在地后,又朝李某头部、背部、腰部等处连砍十余下,致其死亡,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可见,在前案中尽管法院在量刑时考虑到被害人存在过错,对汤某酌情从轻量刑,但判处的刑罚仍然很重,与后案中张某因成立防卫过当而减轻处罚的结果相比,可谓落差巨大。然而,行为人在不法侵害持续过程中故意实施明显超过行为必要限度一倍强度的反击行为,与行为人在不法侵害结束前后分别实施了与行为必要限度相同强度的反击行为和追击行为相比,在预防不法侵害的刑事政策层面并无区别[17]。置言之,在强度总量同等的前提下,实施两次适度的攻击相较于实施一次明显过度的攻击,至少在评价上不应有太大的区别。由此可见,通说对防卫不适时不合理的划定,容易导致实务中出现罪刑不均衡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实施复数反击行为的场合,将追击行为一律认定为防卫不适时的做法过于机械和严苛,在追究防卫人的刑事责任等方面暴露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简言之,通说对防卫过当的认定过于狭隘,不利于防卫人进行防卫。从保障公民防卫积极性、能动性和适度扩张防卫权行使空间的角度出发,应当给予在不法侵害前后实施复数反击行为的行为人相比于实施单纯事后报复的行为人更加宽松的待遇。因此,传统理论对防卫不适时范围的认定并不合理,存在限缩的必要性。
四、防卫不适时限缩的路径展开
要达到限缩防卫不适时范围的目标,首先需明确其特征,为通说所确定的防卫不适时范围提供对照范本。如果复数反击行为能够突破防卫不适时的本质特征,那么就存在将其排除于防卫不适时范畴之外的可能性。
(一)防卫不适时的特征明确
1.超过防卫时间界限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要件,而防卫不适时发生在不法侵害开始之前或者结束之后,恰恰违反了这一要件,即超越了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前已述及,防卫不适时包含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前者是指行为人在不法侵害尚未实际发生,尚处于预备阶段或犯意表示阶段时就实施损害对方权益的行为;后者是指行为人不法侵害终止后,对原不法侵害人实施的反击或追击行为。可见,“在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中的‘事’就是指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18]。
2.行为缺失防卫性质
是否客观存在正当防卫的前提状况决定了行为人能否实施防卫行为,若不存在防卫前提状况,就不能实施防卫行为;即使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也不具有防卫的性质。换言之,正当防卫的前提状况即紧迫的不法侵害现实存在,决定了行为的防卫性质。显而易见,防卫不适时虽然具备不法侵害存在的前提,但不法侵害尚处于预备阶段或者犯意表示阶段,并非紧迫。因此,防卫不适时的行为不具备正当防卫的前提状况,也就不具备防卫行为性或防卫现象性。
3.行为超过时间界限具有客观性,与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无关
防卫不适时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超出正当防卫的时间界限,行为人主观上对防卫时间的认识不影响防卫不适时的成立。如果加入对防卫人主观认识的考量,容易造成公众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误解,即不法侵害客观上虽已结束,然而只要防卫人主观上合理地认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就仍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由此便容易导致正当防卫的过度扩张[19]。因此,对“超过防卫时间”这一要件的限定,应当遵循客观性判断的基本原则。申言之,防卫不适时不限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实施损害行为的情形,还包括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而实施“防卫”行为的情形[13]266。
在上述各项中,欠缺防卫性质可谓防卫不适时的本质特征。而如果在复数反击行为的场合,借鉴“量的防卫过当”理论,放弃分离式的评价视角,而采用整体性的评价视角,将不法侵害结束前后的复数反击行为评价为“一个行为”或“一连串行为”,那么该行为从整体上看就具备了现实存在紧迫不法侵害的前提状况,从而脱离了防卫不适时的本质特征。
(二)以“量的防卫过当”理论展开具体限缩
“量的防卫过当”理论指出,防卫过当的类型包括质的防卫过当与量的防卫过当,其中:质的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本身的侵害性超过排除侵害所必需的程度的情形;量的防卫过当,则指在对急迫不法的侵害的继续反击中,侵害结束或侵害程度大幅减弱,仍继续实施反击的情形[20]。“量的防卫过当”理论采取整体性的评价方式将复数反击行为认定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从而将其所属情形排除在防卫不适时的范围之外。由此,“量的防卫过当”理论便从反面进一步划清了防卫不适时的范围。
然而我国刑法通说一般仅承认质的防卫过当能够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不认可量的防卫过当属于防卫过当的一种类型,并将其所属情形直接划入防卫不适时的范畴。因此,若要借鉴“量的防卫过当”理论,首先便要证明刑法中的防卫过当涵盖了量的防卫过当。
1.“量的防卫过当”的证立
首先,针对复数反击行为,分离式的评价方式未能考虑前后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由于行为的范围由行为意思的范围所决定,行为人出于一个行为意思实施的数个行为,原则上应看作一个整体行为[21]。因此,应采用整体性的评价方式,将行为人基于一个行为意志所实施的数个在时间、空间上具有持续性的反击行为评价为一系列、一体化的行为[14]103。由此,该行为整体上就具备“紧迫的不法侵害现实存在”的防卫前提状况,应将其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因而便具备了成立防卫过当的首要条件。
其次,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刑法中的防卫过当并不排斥“量的防卫过当”。从形式解释的层面出发,刑法第20条第2款所规定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中的“必要限度”在语义上能够涵盖“时间限度”。尽管传统刑法理论通常从“防卫行为本身的限度”的角度来理解“必要限度”,即将“必要限度”阐释为“防卫强度”或者“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限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刑法条文本身并未明确将“必要限度”限制于强度的过当,也并未规定超过时间界限的防卫行为不能成立防卫过当。换言之,将“必要限度”解释为包含“时间限度”和“行为限度”在文理解释上并无障碍。因此,在我国的刑法语境下,量的防卫过当是指行为人在实施防卫行为的过程中,明显超过时间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
从实质解释的层面出发,量的防卫过当与质的防卫过当并无实质区别,亦应适用防卫过当的相关规定。正如前文所述,在强度总量同等的前提下,行为人有节制地在不法侵害结束前后分别实施两次适度的攻击与行为人在不法侵害持续过程中有意实施一次明显过度的攻击相比,在刑事政策层面并无区别,甚至前者的危害性更小。根据刑法通说理论,后者中的行为人即使造成死亡的损害后果,也能享受减免处罚的待遇,而前者中的行为人即使存在认识错误或受极端情绪影响,也只能承受更严厉的诘责。这明显不符合罪刑相均衡的原则。可见,对量的防卫过当适用防卫过当的条款能够得到实质解释的支持,亦能体现罪刑相均衡的要求。
最后,量的防卫过当契合防卫过当的减免处罚根据。在防卫过当的减免处罚根据上采取违法与责任减少重叠并用说更契合刑法的规定。防卫人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被允许在防卫限度内进行反击,而在超过限度到达防卫过当时,虽然整体上具备违法性,但在防卫限度内造成的这部分损害为法律所允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结果非价,因此防卫过当必然存在不法程度的减轻[22]。也正是因为防卫过当的不法程度必然减轻,因此刑法规定对防卫过当至少应当减轻处罚;而在此基础上,当防卫人存在恐惧、惊慌等动摇的心理状态时,期待其实施适度行为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责任就会减少至微弱状态,所以规定针对此类情形免除其处罚[23]。
以防卫过当的减免处罚根据为基准,考察量的防卫过当场合下是否同样存在违法与责任的减少。第一,整体的防卫行为,面对紧迫“不正”的行为维护了正当的利益,与单纯的不法行为存在区别,因此违法性有所减少;第二,防卫人在遭到侵害的紧急状态下,存在极度恐惧、激动、慌乱等情绪和动摇的心理状态,并且一直延续到其实施追击行为的场合,难以期待行为人对不法侵害是否结束平静、准确地作出判断,要求其在不法侵害结束时立即停止防卫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大幅降低,因而导致责任的减少[24]。据此,量的防卫过当既存在不法的减轻,又存在责任的减少,契合我国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实质根据。
综上所述,量的防卫过当与质的防卫过当应该一起成为我国刑法上防卫过当的类型。因而,当事中的反击行为与事后的追击行为被评价为一体化防卫行为时,不属于防卫不适时。申言之,只需明确一体化防卫行为的范围即可得出真正的防卫不适时的范围。
2.以整体性评价方式界定一体化防卫行为的范围
前已述及,一体化的防卫行为由不法侵害结束前后的复数反击行为,通过整体性的评价而得来,因此一体化防卫行为范围的问题就转化为整体性评价标准的问题。整体性评价的标准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
(1)主观层面:行为人防卫意思的持续性
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是在同一、继续的意思决定支配下实施的行为。此处的“防卫意思”并非完全等同于正当防卫成立条件中的“防卫意图”所指的防卫认识与防卫意志的总和,而是更侧重于防卫意志,即防卫合法权益的动机或目的。换言之,在判断一体化的防卫行为时,前后行为基于针对同一不法侵害、保护同一法益的意思决定或动机即可认定存在连续的防卫意思,并不涉及对具体事实的认识[25]。因此,可以承认以下两种情形中防卫意思的持续性:第一,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而在原本的防卫意思的持续支配下继续实施反击行为(实际上为追击行为)的情形;第二,行为人明知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但由于恐惧、激动等心理上的动摇,为了防止原不法侵害人再度攻击而继续实施追击行为的情形。
如果行为人已经意识到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在与心理上的动摇毫无关系的情形下继续实施追击行为[26-27],即行为人在实施追击行为时主观上完全转变为出于报复、泄愤等目的或者出于强烈仇恨、不满而攻击的意图占据完全的压倒性地位的,其行为就由防卫行为转变为彻底的攻击行为[28],防卫意思的持续性即告中断,那么追击行为与反击行为就无法被整体评价为一体化防卫行为,而是应当分别进行评价。例如,在“刘某故意伤害案”1中,刘某在夜宵摊吃夜宵时,碰到韩某酒后骑助力车过来。韩某下车后拿一把三棱刮刀边骂边走到刘某身旁,一手抓住刘某衣领,一手拿刀把顶了刘某下巴一下。刘某摆脱韩某的纠缠,但韩某仍持刮刀谩骂、威胁,数次纠缠未果后,韩某骑车离开。刘某心感不满,便跑了十多米追上正骑车的韩某,从后面用双手推了一下韩某左侧肩部,韩某连人带车仰面摔倒头部着地,助力车压在韩某身上,刘某也因惯性摔在助力车上。韩某因重度颅脑损伤抢救无效后死亡。最后,法院判决刘某推倒韩某的行为构成防卫不适时。在本案中,刘某在不法侵害进行时实施了反击行为,不法侵害结束后又实施了追击行为,但其追击行为是出于“心感不满”的报复行为,并不是出于防卫法益的意思或动机,因此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之间发生断裂,不能被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即成立防卫不适时。
(2)客观层面: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的紧密性、连续性
第一,前后行为具有时间上的紧密性,追击行为是反击行为的“顺势而为”,间隔时间之短暂能够“自然而然地将防卫行为及其后续部分自然地看成一个整体的事实发生过程”[29];第二,前后行为在空间上具有同一性或延续性,行为人当场接连实施了反击行为和追击行为,抑或行为人实施反击行为致使不法侵害人退缩,在其逃离现场的过程中继续实施追击;第三,前后行为处于同一不法侵害所形成的紧急状态,且均针对同一不法侵害事实和相同的不法侵害人进行。例如,甲在面临乙持刀行凶时,拿起木棍反击,在击倒乙后,继续使用木棍击打乙,此时可以肯定前后行为的侵害对象和侵害法益相同,且对法益的具体危险具有持续性。然而,若在侵害结束后,甲未继续使用木棍击打乙,而是趁乙倒地丧失攻击能力将乙身上的财物取走,那么此时就不能再认定前后行为具有法益侵害的同一性和持续性。
综合客观层面与主观层面的要件,将同时满足两方面要件的复数反击行为评价为“一个实行行为”,进而可以确定该实行行为整体具备防卫的前提状况,因此可以认定其整体具有防卫性质,即其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例如在前述的“汤某故意杀人案”2中,汤某在不法侵害结束之后又对原侵害人杨某进行了击打,并且由于汤某后续的击打行为(追击行为)与之前的击倒行为(反击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且发生在同一空间;汤某出于防止被杨某继续殴打的动机,反击行为与追击行为基于同一意思决定,所以应当将汤某的击倒行为与后续的击打行为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25]129-130。因此,汤某的行为不属于防卫不适时。
总之,根据量的防卫过当理论,当追击行为与反击行为被整体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时,不应认定其为防卫不适时。换言之,需将符合整体性评价标准的复数反击行为从传统的防卫不适时范围中剔除。据此,防卫不适时应当具体限定于以下情形:一是事前防卫,包括故意的事前防卫与存在事实认识错误的事前防卫。前者是指行为人明知不法侵害尚未开始,而提前实施损害行为的情形,后者是指不法侵害尚未开始,但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而实施所谓“防卫”行为的情形。二是事后防卫,包括故意的事后防卫和存在事实认识错误的事后防卫。前者是指行为人明知不法侵害已经结束,而仍然实施损害行为,且不法侵害结束后的追击行为不能与结束前的反击行为作整体性评价的情形;后者是指行为人误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而实施所谓“防卫”行为,且不法侵害实际结束后的追击行为不能与结束前的反击行为作整体性评价的情形。
结" 语
防卫不适时将不具有防卫性质的行为排除在正当防卫之外,具有防止防卫权不当扩大的作用,因而对其存在范围的确定有助于正确区分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正当防卫与单纯犯罪以及防卫过当与单纯犯罪。因此,在理论上厘定防卫不适时的范围就具有必要性。首先,通过廓清防卫不适时与假想防卫的关系,明确因事实认识错误导致的超越防卫时间界限实施“防卫”的行为属于防卫不适时,而非假想防卫。其次,通过梳理关于防卫过当与防卫不适时二者关系的理论分野,借助对存在正当防卫前提的事后防卫的定性争议,探讨现行通说所划定的防卫不适时范围的合理性,进一步丰富防卫不适时的内在驱动理念,将适度扩张防卫权的考量纳入其中。最后,明确防卫不适时的本质特征,并结合借鉴“量的防卫过当”理论,通过整体性评价将复数反击行为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由此将部分存在正当防卫前提状况的事后防卫纳入防卫过当甚至正当防卫的范畴,从而达到限缩防卫不适时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张洪成.正当防卫时间限度的实证分析[J].北方法学,2020(6):96-103.
[2]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3] 陈兴良.正当防卫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4] 曾文科.论复数防卫行为中的评价视角问题:以日本判例为素材的分析[J].中国案例法评论,2015(1):75-99.
[5] 梁喜伟.浅议防卫不适时[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2(4):80-81.
[6] 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8.
[7] 王剑波.防卫不适时之界限分析[J].法治研究,2008(2):8-11.
[8] 王政勋.正当行为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9] 李森,陈烨.假想防卫的错误类型再探[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70-75.
[10] 陈兴良.教义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492.
[11] 彭卫东.正当防卫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69-72.
[12] 林亚刚.刑法学教义: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94-295.
[13] 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14] 孙国祥.防卫行为的整体性判断与时间过当概念之倡导[J].清华法学,2021(1):98-115.
[15] 张明楷.防卫过当:判断标准与过当类型[J].法学,2019(1):3-21.
[16] 山口厚.刑法总论[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28-130.
[17] 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62.
[18] 陈兴良.正当防卫教义学的评析与展开[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2):3-29.
[19] 王志祥.论正当防卫制度司法适用的纠偏[J].法学论坛,2019(6):135-141.
[20] 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M].曾文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79.
[21] 赵宗涛.整体评价视角下量的防卫过当的理论建构[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97-103.
[22] 许恒达.屋主的逆袭:再论延展型过当防卫[J].月旦裁判时报,2015(41):49-59.
[23] 曲新久,陈新良,张明楷,等.刑法学[M].5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46-49.
[24] 赵金伟.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及适用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17(3):134-140.
[25] 曾文科.论量的防卫过当[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4):122-136.
[26] 尹子文.论量的防卫过当与《刑法》第20条第2款的扩展适用[J].刑事法评论,2017(1):495-513.
[27] 段宇衡.事后的防卫过当的教义学阐释:以量的防卫过当之否定为切入点[J].江汉论坛,2024(3):139-144.
[28] 刘夏.一体化防卫行为的法教义学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1(7):87-93.
[29] 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M].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38.
[责任编辑:翟香丽]
1参见河北省涞源县人民检察院涞检公刑不诉〔2019〕第1、2号不起诉决定书。
2参见贵州省平塘县人民法院(2004)平刑初字第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3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刑终14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1参见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青01刑终12号刑事判决书。
1详见2014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起涉家庭暴力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1详见北大法宝网《江西公布五起涉正当防卫典型案例之四:不法侵害结束后仍防卫 防卫行为属于故意伤害》,https://www.pkulaw.com/pfnl/a6bdb3332ec0adc4f68b2ba31e8d4468ed1853e37a9732fdbdfb.html。
2详见2014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起涉家庭暴力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基金项目]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科研项目“市域社会治理视域下西部基层公共安全法律体系研究”(20SFB4021);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不追究刑事责任制度研究”(XSP2023FXC172)
[作者简介]辛有仪(1997— ),女,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刘抒婷(2000— ),女,中南大学教育立法研究基地研究助理,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引用格式]辛有仪,刘抒婷.防卫不适时的范围界定与限缩[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3):13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