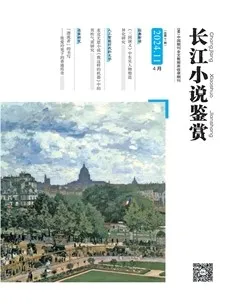“漂流者”的书写
[摘要]张爱玲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她曾三次赴港,香港的都市传奇、人世悲欢也成为她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张爱玲对香港的书写态度与当时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通过细读张爱玲早期有关香港的小说与散文,可以发现,张爱玲并非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香港进行审视,而是以“漂流者”的身份,站在中西文化交界的边缘位置上,书写生活在殖民统治背景下的一个个独特个体。本文认为,张爱玲早期的香港传奇呈现出了香港社会“混杂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香港中西混杂的文化元素上,更表现在港人的情爱追寻与身份认同上,在此基础上张爱玲对香港的殖民主义权威进行了深入的质疑和一定程度上的解构。
[关键词]张爱玲 香港传奇 香港形象 后殖民主义 混杂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1-0088-05
一、绪论
张爱玲于1939年—1942年在香港求学,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中断学业并返回上海。在张爱玲作为一名“上海作家”的岁月里,她曾写下数篇关于香港或以香港为故事发生背景的散文及小说,包括《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1943年)和《烬余录》《连环套》(1944年),其中1943年创作的四篇小说都被收入其作品集《传奇》(1944年)中。在《第一炉香》的开篇,张爱玲即借葛薇龙的视角书写下自己对于港岛最为直观的感受:
薇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她到姑母家里来。……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1]
“搀揉”与“奇幻”是张爱玲赋予香港的最为贴切的形容词。当时的香港虽然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并没有完全割舍同中国的血脉联系;与此同时香港的地域位置也让它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冒险家游乐园”——各方角力下,香港成为一个复杂的旋涡,一个繁复的空间,一个华洋杂处的都市,一片幽深的思想丛林[2]。学者李欧梵认为,香港文化以其“杂糅性”而闻名:在历史的进程中香港融合了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等不同文化元素,并将上述的文化元素以非常规性的方式进行拼凑与融合,从而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景观[3]。李欧梵在作品《上海摩登》《张爱玲在香港》中均有论述到香港和上海的双城关系,在他看来,张爱玲小说中的香港承受着来自英国殖民者和来自中国上海人的双重注视,与“带有异域气息但全然是中国的”上海相比,香港是张爱玲笔下被殖民化的“她者”,正如张爱玲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称自己笔下的香港实则是来自“上海人”视角的观察与体悟[4]。但学者倪文尖则指出,对张爱玲这一自白不能高估,因为《到底是上海人》其实是刊登于上海的卖书广告上,因此可能有讨好上海读者之嫌[5]。学者黄心村认为,张爱玲对于香港的看法受到了她的历史讲师弗朗士的影响,她或许正是从弗朗士的近代历史课上开始了对殖民和后殖民的思考。弗朗士生前自称是“Hong Kong Stayer”(港居者),他是英国殖民历史中暂居他乡的漂流者,而他的学生张爱玲既是上海回不去的“主人”,又是香港受欢迎的“过客”,他们“同是二十世纪殖民、再殖民、反殖民、后殖民的大背景下的一对师生”[6]。
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说张爱玲是从一个上海人的视角来审视香港,倒不如说张爱玲是以一个“漂流者”的身份来观察带有异国色彩的“香港”,张爱玲以游离在传统中国人和殖民者的边界上的视角,来描绘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社会的“混杂性”,并通过这种混杂性的呈现对香港的殖民主义权威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质疑与解构。“混杂性”(Hybridity)是后殖民评论家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的核心思想之一,巴巴认为,“混杂化(Hybridization)”即意味着“不同民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相互混合的过程”[7]。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文化教化体现了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同时也呈现出一个充满矛盾(ambivalence)的过程:一方面,殖民话语鼓励被殖民主体接受其先进文化,走向优雅文明;另一方面,却通过种族差异和劣等性观念否定和阻挠这种文化接近,形成了被殖民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戏拟(mimicry)。根据文化混杂性理论,文化并非单一、纯粹的实体,而是通过不同文化元素的交流、碰撞和混合产生。这种混杂性不仅存在于文化本身的层面,也反映在个体和群体的身份认同中。巴巴消解了殖民关系中二元对立的“自我-他者”关系,他认为“从一开始,自我就有赖于他者而存在,这些他者与自我相互混杂、不可分割,且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这种变迁将一直持续下去,人的身份就成了一个变动不居的异源集合体”[8],即自我是所属种族内部与外部的“双重他者”。尽管张爱玲的创作时期与“后殖民”研究兴起的时间有一定的差距,但笔者旨在以这一理论为研究切入点,阐述张爱玲的“香港传奇”中展现的香港社会文化混杂性特征,及其对殖民主义的深刻思考。
二、文化混杂的香港社会
香港的混杂性首先表现在东西方文化元素的交融上。香港是包容性很强的一个海滨城市,是一个“杂色”场所;左与右,中与西,土与洋,就那么看似“犯冲”却也兼容并存[2]。然而,看似多元的文化元素并非“平等”地出现在香港社会之中,其所反映的正是英国统治时期香港社会背后西方对东方的权力话语。例如,在《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写梁太太的园会:
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灯笼丛里却又歪歪斜斜插了几把海滩上用的遮阳伞,洋气十足,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丫头老妈子们,一律拖着油松大辫,用银盘子颤巍巍托着鸡尾酒,果汁,茶点,弯着腰在伞柄林中穿来穿去。[1]
梁太太的园会是与西方人交际的场所,在装饰风格上,却分明是在中国文化元素的基础上混杂对西方“洋气”文化符号的戏拟,最后呈现出的也是“不伦不类”的效果。同样,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讽刺香港的英国式舞厅古板无趣——那些西洋侍者“仿着北方人穿着扎脚裤”,只为滑稽地追求一种“中国式”情调[1]。在张爱玲看来,不光是香港的中国人在戏拟殖民者的文化,殖民者为了达到“异域色彩”的奇幻效果也在模拟中国的文化元素,以塑造西方人幻想中的“东方想象”。由此可见,香港到处都是殖民化、混杂性,香港这座城市既是位于中国的“异邦”,也是与异域文化混杂后产生变异效果的“东方”。
除了这些物质文化符号,香港社会也呈现出许多殖民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与冲突。香港社会新旧教育观念的混杂共存状态是张爱玲笔下香港的突出特点之一,例如在《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姑妈讽刺葛薇龙爸爸“古董式”的家教不如香港通行的“英国大户人家小姐交际”的规矩,《茉莉香片》中饱受旧式封建教育思想折磨的聂传庆对从外国归来、奉行西式开明家教的言子夜无比倾慕。同时,张爱玲笔下那些外表光鲜、深受西方发达物质文化影响的角色背后所体现的更是殖民者的“拜物教”文化和虚无苍凉的传统美学之间的对照。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弥散着一种浓厚的西方“拜物教”文化,张爱玲在《第一炉香》中写道:
睨儿道:“呵哟!就像我眼里没见过钱似的!你看这位姑娘也不像是使大钱的人,只怕还买不动我呢!”[1]
梁太太家中下人的话反映出了香港社会崇尚“金钱”的社会风气,殖民者带来先进物质文明的同时,“拜物教”的文化观念也根植在了香港人的心中。与此同时,张爱玲又敏锐地觉察到因为政治变动和日本的侵略战争,生活在香港的人们流露出“万般虚空”的价值观念。正如其在散文《烬余录》中所述:
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9]
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深受中国传统宗教哲学思想影响的张爱玲敏感地体悟到了香港“华丽”外表下隐藏着的“悲哀”①,殖民文化的先进物质在炮火的洗礼下最终依旧会走向“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可见,不论是表层的物质文化,还是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张爱玲笔下的香港社会最突出特点就是“混杂性”。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下,张爱玲也将观察的视角投射到了个体在情爱关系中对身份的追寻之上。
三、情爱书写与身份认同
香港的殖民文化特性给了张爱玲爱情书写极大的发挥空间,其笔下人物的情爱故事集中反映了殖民关系中“自我”心理的不确定性。在张爱玲的香港书写中,从不同地方来到香港的这些人物角色本身便包括不同地域文化特性相混杂的特征,他们对爱情的追寻过程也象征着其徘徊在多种文化之间,又对认同哪一种文化感到无所适从,最终造成了一种身份上的悬置,成为了被任意一方建构的“他者”。
在《连环套》中,从广东乡下被卖到香港的霓喜一直渴求一个正式的“妻子”身份,为此她先后同印度商人雅赫雅、药铺老板窦尧芳、英国工程师汤姆生“结婚”,然而正如张爱玲所言,“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来,赛姆生太太曾经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看来,她始终未曾出嫁”[10]。霓喜在不同时期辗转并依附于不同的男性,取悦他们并为其生儿育女,而这些男性却无一不是利用霓喜的心态来满足一己私欲。因此,在他人的眼中霓喜自始至终都是在扮演“姘头”“姨太太”的角色,其身份从未获得香港社会的正式认可。即便最后如愿获得了“英国式”的名字,但在本质上霓喜却依旧无法获得确切的自我身份认同——她既对自己原生的中国人身份嗤之以鼻,却又无法被自己所“向往”的殖民者主体所接受,最终成了被西方殖民者抛弃,被迫游离在自我种族内部与外部的“双重他者”。
在《倾城之恋》中,离婚后被家人榨干财产的白流苏为躲避家人的冷眼无奈从上海漂泊到了香港。不被范家人承认的私生子范柳原自幼辗转海外多国,来到香港之后也依旧无法找到归属感。白流苏与范柳原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对于“婚恋”的态度集中反映了其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状态:
流苏沉思了半晌,不由得恼了起来道:“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还得绕着大弯子!什么做不了主?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哩!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谁替你做主?”柳原冷冷地道:“你不爱我,你有什么办法,你做得了主么?”流苏道:“你若真爱我的话,你还顾得了这些?”柳原道:“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1]
在香港社会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都渴求得到一个能被自我与他者认同的“身份”,虽然被认为“不像上海人”,但白流苏依旧秉持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试图通过一份安稳的婚姻、一个正式的“妻子”身份来获得社会的认可;而范柳原虽然喜欢“真正中国化的”女性,但同时他又被“中国人”所表现出的虚伪自私所伤害,本质上向往自由的天性又让他不愿意被无爱的婚姻束缚。虽然香港的沦陷成就了两人圆满的婚姻结局,但实质上二者依旧是香港社会殖民背景下的漂流者,是在身份认同上充满混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双重他者”。
四、对殖民主义的审视与反思
张爱玲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中抽离出来,对香港社会进行了“有距离感”的审视与书写[11],而这样带有足够距离的观察视角也让张爱玲对于香港的书写没有停留在表现“洋场”异域色彩的表象上,而是对香港社会的殖民主义现实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在《烬余录》中,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张爱玲直观感受到了殖民主义权威的脆弱性与虚假性,她在文中写道:
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9]
战争的到来打破了西方优越文明的叙事神话,比战争更加残酷无情的是西方殖民者冷漠自私的精神底色。在张爱玲笔下,从香港招募的中国大学生只能沦为英国殖民者自保的作战工具,英国的殖民政策只不过是以巧言令色来美化其对被殖民者的压迫:在殖民者眼中,被殖民者始终是劣等的,是可以被无条件牺牲的。张爱玲曾是上述现实的亲历者,而这也使得她在书写“香港传奇”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殖民主义的权威性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
张爱玲在作品中采取了西方殖民文学中“殖民者的凝视”方式对香港进行了刻画,却把殖民者的生活转变为观察对象,而把被殖民者放到观察的位置,这种置换动摇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构成了霍米·巴巴提及的混杂性[12]。《第二炉香》最为突出地体现了这种“置换”。罗杰虽然是英国殖民者中的一员,但他的命运一直处于“被观察”的状态之中,他最终的自戕结局也是出于殖民者内部对他的观看与议论:
昨天晚上两点钟,你太太跑到男生宿舍里,看样子是……受了些惊吓。她对他们讲得不多,但是……很够作他们胡思乱想的资料了。今天早上,她来看我,叫我出来替她作主。……下午,你的岳母带了女儿四下里去拜访朋友,尤其是你的同事们。现在差不多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人家,全都知道了这件事。[1]
罗杰的悲剧揭示了西方殖民者所谓的进步和开明只是对中国的一种预设特征,而实际上“先进的”殖民者也承担着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同样可能会变成愚昧和封建的化身。罗杰的困境来自同为西方殖民者的“自己人”,而这样的处境又让他陷入“异邦”与“家乡”的茫然之中——英国是其无法返回的家乡,而充满“混杂性”特征的香港社会更是他走不出去的牢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爱玲看到了香港殖民色彩的讽刺性与荒诞性,但她没有采用历史宏大叙事的方式对其进行严厉批判,而是站在中西文化的边界上将其视为全新的创作资源。在《第一炉香》中,张爱玲以叙述者的口吻写道,“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1],以被物化了的“女性”为喻点明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在《连环套》中,张爱玲对殖民地官员米耳先生的“丑陋”外貌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刻画,同样将殖民者放置于被读者审视的视角之下,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殖民者所谓的“文化霸权”。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张爱玲早期有关香港的作品为切入点,论述了其站在传统中国人和殖民者的边界上,将香港视作充满着异国色彩的混杂性殖民社会。张爱玲对于香港形象的独特创作视角与其在香港求学的所见所闻及其亲身经历的战争状况息息相关。王德威教授曾对20世纪中国作家的香港经验进行概括:“租借的时空,转手的历史,现实的无明状态让作家感同身受;现实可以细微琐碎到完全没有意义,但这种对生活底色的专注使他们发展出不同的视界。”[13]在文学创作中,张爱玲以既非局内人又非局外人的独特“港漂”身份,对香港社会的混杂性现实以及生活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微小个体进行观察与叙写,其笔下有关香港的殖民记忆与浮世悲欢也为人们理解文学与文化上的“香港形象”提供了别样的思考路径。
注释
① 张爱玲出生于官宦之家,不自觉地受到家庭与社会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同时,张爱玲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如《红楼梦》《金瓶梅》等)的熏陶,并且其前半生均生活在五四后佛学传播的思潮之中,故佛教“色空观”的生命哲学对张爱玲的创作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参见苏天宇.试论佛教文化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D].浙江大学,2017.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传奇(增订本)[M].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
[2] 鹿义霞.文化场域与创作转型——海派作家的香港时期[J].文艺争鸣,2018(7).
[3] 李欧梵.寻回香港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 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J].文学评论,2001(1).
[6] 黄心村.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
[7] 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J].中国翻译,2002(2).
[8] 翟晶.后殖民视域下的当代艺术——霍米·巴巴对艺术批评的介入[J].文艺研究,2018(2).
[9] 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10] 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11] 黄心村,黄子平,王风,等.张爱玲与世界主义的人文视野[J].文艺争鸣,2022(10).
[12] 梁慕灵.想像中国的另一种方法:论刘呐鸥、穆时英和张爱玲小说的“视觉性”[J].政大中文学报,2013(19).
[13] 王德威.悬崖边的树[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谭嘉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