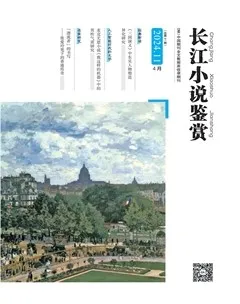麦克尤恩小说《我这样的机器》中的男性气质研究
[摘要]在麦克尤恩的小说《我这样的机器》中,男主人公查理的人物形象弥漫着以延宕犹豫、纠葛反复、边缘拮据为特点的从属性男性气质,而人造人亚当富有力量、无畏果毅、视野广阔,虽为“非人”角色却具备“为社会文化所普遍接受的”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在亚当介入查理的生活后,查理憎恨亚当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威压,致使其男性气质即将从从属性沦为边缘性,甚至将自己生活濒临崩溃的原因归咎于此,最后选择毁灭亚当。但亚当从查理的生活中消失后,查理并没有感到轻松与解脱,反而感到愧疚与惶惑。查理被性别的刻板印象所缚,只想着颠覆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却无法认清自身存在的性格缺陷才是致使其生活进退维谷的元凶。麦克尤恩这一系列性别书写的策略,不动声色地讽刺了社会刻板印象中的性别气质,启发读者去思考所谓“理想化”性别气质的构建。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 《我这样的机器》 男性气质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1-0075-04
伊恩·麦克尤恩,英国当代作家,其创作生涯与各类奖项的名单相互交织,《阿姆斯特丹》获布克奖,《时间中的孩子》获惠特布莱德奖,《赎罪》获全美书评人大奖,是当今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堪称当今英国文坛的“国民作家”。
学界认为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将更多的兴趣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充斥着暴力、谋杀与性,麦克尤恩也因此得名“恐怖伊恩”。而在其稍晚一些的作品中,麦克尤恩表现出更加自觉的社会意识,开始关注社会当下的发展态势。在人工智能与生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伊恩·麦克尤恩2019年出版的新作小说《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便构想了一个人造人已经变为现实的世界。小说重点讲述人造人亚当在介入主人公查理及其女友米兰达的生活后,三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麦克尤恩在此部小说中聚焦人机关系,多数研究从伦理学或后人类的视角来解读此作品,认为其“隐喻了科学选择和伦理选择的冲突”,而小说结尾处“亚当的毁灭则揭示了机器人之于人类道德生活介入的失败”[1]。
“性别”这一原本蜕生于生理学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与社会文化语境交织在一起。社会学方面的性别研究理论深入发展,更是为文学批评的新视角提供了借鉴。当我们把性别视角融入文学研究时,能深刻地揭示作品中角色身份构建及行为话语的性别动因,从而管窥作者关于性别政治的独特观念。康奈尔(Raewyn Connell)对男性气质研究的贡献最为社会性别研究界所推崇,其著作《男性气质》也是性别研究界的丰碑。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研究不可忽略,因为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概念是相互影响存在的,对男性气质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妇女研究的推进及社会理想化性别话语的构建。
本文以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辅以其他性别研究学说,对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中的男性气质主题进行解读,以期探寻作者对于性别政治的人文观照,更深入地理解麦克尤恩的后期创作。
一、查理的从属性男性气质
康奈尔在他的性别研究理论著作《男性气质》中将社会实践中构建起来的男性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通过麦克尤恩的人物刻画,《我这样的机器》的主角查理身上表现出明显的从属性男性气质。
首先,查理的身上弥漫着延宕与犹豫的气质,查理描述自己的性格为“我的性格无论是什么,大多时候都处在悬置状态”[2]。此种气质有时还表现为胆小与多疑,这一性格特质在他决定是否要向米兰达表明自己的爱意时尤其明显,查理总是胆怯“一不小心就可能失去她 ”,若向米兰达吐露自己的心迹,“会令人尴尬,而且有害无益”。并且他常常因为纠结此事而在脑海里“翻来覆去,思绪越缠越紧”[2]。查理的这一气质与传统性别观念中男性刚毅果断的特征明显不同。同样也是在传统的性别观里,女性被认为优柔寡断,思绪纷繁,麦克尤恩把这样的弱点赋予查理这一男性角色,就是为了凸显他的从属性男性气质。
查理的从属性男性气质也表现在他反复无常,做事不能坚持,反而经常半途而废,满腹抱怨。查理的求学历程充分印证了他这一性格特点,他17岁时在当地一所学院学习物理,但他感到枯燥无味,内容抽象,打算换个专业。他对文学兴趣浓厚,但又觉得其“太让人气馁,太依赖直觉了”,不值得学习。后来学习人类学,虽获得了学位,但又怪罪是人类学让他“迈入了永无止境的相对主义”[2]。这同样与人们刻板印象中的男性应当坚韧倔强的观点发生了偏移。
纵观查理的一系列性格特质,他的踌躇多思,他的纠葛反复,他的抱怨牢骚,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种“神经质”。而在西方传统的文学创作中,“神经质”常常与女性角色联系在一起,它一般代表了女性角色“天使般谦逊外表之下根深蒂固的自我”[3]。康奈尔在论及从属性男性气质时也指出从属性男性气质与所谓的女性气质的联系是明显的[4]。麦克尤恩正是通过将男主人公查理的形象女性化来凸显他的从属性男性气质。
再从查理的经济情况来反观他的从属性男性气质。他继承了母亲的大笔遗产,却将其浪费在一个精巧的玩意儿上,导致了自己彻底的破产。他不会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地重建自己的经济基础,反而在获取经济来源方面钻营取巧,投机倒把,查理描述自己获取经济来源的方式是“搞些项目和打法律擦边球的计划,喜欢走聪明的捷径”,每天7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面“靠在线上炒股票和外币生活”[2]。性别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结构,男性气质的构建自然而然要与社会语境下的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失去了稳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查理的男性特质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从属性。从属性男性气质除了集中表现在男同性恋者群体中,也会表现在从主流男性气概圈中被驱逐的男异性恋身上,贫穷者就分属此类[5]。遑论男性气质的构建,缺乏稳定经济基础与理性经济观念的查理,甚至都不参与集体的社会活动,这让他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也表现出一种“边缘人”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查理实际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男性集团中的所谓从属性和在社会关系中的边缘性,但他从来不会对自己的生活境况进行反思,从来不会对造成自己窘境的自身因素进行反思,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更不会积极寻求突破和改正。相反,他转过头来怪罪这个社会,他指摘社会弊病,大谈空话,愤世嫉俗,悲观地认为“当下是最脆弱、最不可能的建构”[2]。
二、亚当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既存在从属性男性气质,那么就会有居于统领地位的男性气质,康奈尔将其称之为“支配性男性气质”,“在任一给定的时间内,总有一种男性气质被文化所称颂”[4]。支配性男性气质代表的便是目前广为接受的男性特质。但由于其性质近似于在社会语境的不断重复操演中演化出的一种文化定义,有时会表现为对男性的刻板印象。在《我这样的机器》中,麦克尤恩安排亚当这一“非人”角色来展现这种支配性气质。
在人造人亚当还没有真正启动之前,查理其实没有将亚当作一个“人”,或者说根本没有将其视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个体生命。直至亚当与女主角米兰达发生关系后,查理才真正把亚当视为一个“人”,当作一个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人”来看待。在查理看来,米兰达的行为是对他赤裸裸的背叛,亚当不是按摩棒,他像个男人,是“另外一个男人”[2]。表层意义上,查理只有在此时将亚当视为“人”,才能在与米兰达的争吵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达成他需求的情感关系。
而深入理解查理的话语,他侧重强调的不只是亚当由物到人的升格,更是亚当在他的观念中已经被赋予“男性”这一性别表征。亚当不仅在与米兰达的性关系中有着“教科书一般的技巧,用不完的力气”[2],而且在事后还对米兰达径直吐露爱意,向米兰达献上自己创作的饱含倾慕的爱情诗行。果敢的决断和对异性的占有,这些都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重要因素。而在前文中已经论及,查理在对待和米兰达的感情问题上总是犹豫不决,踌躇不前,他的从属性男性气质与亚当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形成强烈反差。查理也已经感受到亚当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他开始把亚当视为威胁者和竞争者,所以亚当才在他的观念中由“有功用”之物升格为“有威胁”之人。
后文中亚当与查理就米兰达一事爆发的肢体冲突不仅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还喻示着亚当的男性气质对查理已经由威胁上升为压制与支配。查理认为亚当对米兰达产生的爱意荒谬又可笑,这不过是亚当的处理器出现了故障,勒令他即刻停止;而亚当则认为查理的此般言语是对他彻头彻尾的侮辱。两人的争吵随即升级为肢体冲突,查理想要关闭亚当的开关,却被亚当扭断手腕。在被亚当扼住手腕时查理内心想的是“不要发出一点点呻吟的声音,不让他从我的痛苦中获得满足”[2]。此处查理已经完全将亚当视为了男性人类个体,也完全直面感知到来自亚当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两人的直面冲突不仅是人机冲突,更是从属性男性气质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冲突。查理在与亚当的冲突中被完全控制,毫无反抗之力,付出伤痛的代价,这也象征着支配性男性气质通过暴力的宣扬与威压。
亚当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同样体现在他生财有道,学识广博。亚当在金钱投资上可以根据“极其微小的货币价格浮动进行交易”[2],能够慢慢累积起一笔笔收益,最终获得可观收入。同时他还深谙文学,能自创俳句;通晓物理,精于量子力学;视野独到,能针对当时的英国政局发表自己的深刻见解。而反观查理,理财意识淡薄,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可靠稳定的维生手段,视野狭隘,愤世嫉俗,学习上更是浅尝辄止,因噎废食。由此,无论是性格特质、体魄力量,还是经济基础层面,亚当的支配性男性气质都与查理的从属性男性气质构成强烈反差,对其形成全面压制。
三、亚当之“死”: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颠覆
根据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凭借着支配性男性气质,一个集团可以“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据此试想,若亚当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类男性个体进入社会,势必会进入“目前广为接受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权力集团,从而对以查理为代表的从属性集团形成统治与压制。
这种统治与压制引起了查理的憎恶与怨恨,他将自己对社会与生活的怨火转移到亚当身上。他在叙述中频繁使用诸如“可憎的”“可恨的”一类形容词来咒骂亚当,甚至鄙视制造亚当的制作人员,鄙视程序和算法设计。明知亚当不需要休息,却仍报复性地让其连夜工作来宣泄自己的愤恨。这种怨恨发展到小说结尾,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濒临崩溃,亚当的支配性男性气质难辞其咎,亚当的存在必须被抹除。
在小说临近结尾处,亚当捐献了他赚来的钱,向法庭检举了米兰达所做的伪证,此行为不仅会使查理和米兰达面临破产,更会使米兰达锒铛入狱。米兰达的入狱会进一步致使两人收养幼童马克的计划流产。两人就此事与亚当爆发了激烈的争辩,小说也迎来情节的高潮。在争辩中,亚当丝毫不为查理与米兰达的情感攻势动摇,坚持捐赠财产,认为检举米兰达的行为合理合法。若把亚当视为人造人看待,其行为可以解释为超然冰冷的机械理性;两人与他的争执则代表着道德伦理与科学技术冲突的最终爆发。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亚当的一系列行为会使查理的男性气质由从属性沦丧为边缘性。康奈尔对边缘性男性气质的定义是:“性别与其他结构如阶级和种族的相互作用发展出各种男性气质之间的进一步关系。”[4]亚当的行为会使查理的生活完全崩坏,失去财产,失去女友,失去家庭,这接连的剧变甚至会完全改变查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失去一切的查理很可能只得从头开始,靠出卖劳力过活,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关系中,只靠出卖劳动力的男性所具有的气质就表现为边缘性。
这使得查理对亚当的怨恨到达顶峰,他决心彻底终结这一使人窒息的祸患孽物。“我感觉到怒火在心中聚集,寻找爆发点。我憎恨他那不以为然的耸肩膀的小动作。完全是假的。”[2]查理此时又将亚当重新视为了机器,“他是我买的,也就该我毁掉”[2],这一方面是因为毁掉砸碎一个属于自己的物件不会受到任何良心道德的拘束和谴责,另一方面是亚当此时在查理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了对他施压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极致化身。出离的愤怒使他举起铁锤,只犹豫了不到半秒便砸在亚当的头顶,彻底使亚当失去了生命力,从属性男性气质颠覆了支配性男性气质。
但亚当从他的生活中消失,查理所感受到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压制消失后,查理非但没有丝毫轻松与愉悦,反而感到愧疚与惶惑。在把亚当的“遗体”送回研究所后,他朝自己那“并不安宁”的家走去,他生命中的下一个阶段,“当然是最辛苦的阶段”[2]已经开始。这是因为毁坏亚当并不会带来新的改变。
四、结语
“性别”这一原本蜕生于生理学的概念如今已经与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纠葛交织在一起,社会似乎为性别的定义施加了诸多固定范式。这应和了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性别是在强制的重复性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6]。就像巴特勒所言,社会的性别定义是“在身体的表面建制、铭刻的一种幻想”[7]。“性别是一贯隐藏它自身的创生的一种建构;它是心照不宣的集体协议,同意去表演、生产以及维系明确区分的、两极化的性别的文化虚构。”[7]此种现象使得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在社会语境中生根发芽,带来了性别之殇。
《我这样的机器》中的男主人公查理就被性别的刻板印象所缚,一度认为自己的从属性男性气质被代表着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亚当压制,只盲目地一味怨恨憎恶,甚至将自己生活的崩溃归因于亚当,以致最后“杀死”亚当,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一团乱麻实则是由于自身的性格缺陷,与所谓的男性气质博弈毫无关系。即使没有亚当的介入,他的生活也会迟早陷入混乱。另外,麦克尤恩让人造人亚当这一实际上“非人之物”代表所谓支配性男性气质也颇有深意。那种以威压强势全能为特点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或许只能在冰冷的机器身上才能觅得一二。麦克尤恩的这一系列性别书写策略不动声色地讽刺了社会刻板印象中的性别气质,启发读者和社会去思考真正“理想化”的性别气质构建。
参考文献
[1] 尚必武.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冲突:麦克尤恩《像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人工智能与脑文本[J].外国文学研究,2019,41(5).
[2] 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M].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3] 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 R.W.康奈尔.男性气质[M].柳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 方刚.康奈尔和她的社会性别理论评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8(2).
[6] 都岚岚.西方文论关键词性别操演理论[J].外国文学,2011(5).
[7] 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8] 李玥.论伊恩·麦克尤恩《像我这样的机器》中的机器形象及人机关系[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3).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邵培豪,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